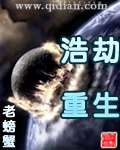上海生死劫-第5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当老李进来时,我站起来对他表示敬意。他请我坐下,另外拿了只椅子柱对面隔着桌子坐下。
〃我是住在太原路一号的。〃我自我介绍。
〃我知道你是谁。〃老李望了望时钟,不耐烦地说,〃你找我有什么事?〃〃我来向你汇报,昨晚有个小偷越墙进了我们那幢房子。〃〃有什么东西遗失吗?〃〃楼下朱家遗失了两件衬衫,我们家只是把这块通告牌撕碎了。〃我将那些纸牌的碎片放在桌子上。老李将那些碎片拼在一起,看上面写着的字。他额上的眉头皱紧了。
〃这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要写这些?〃看样子他真的有些糊涂。这样我就明白他不了解我那些络绎不绝的客人。公安部门作为一个机构来说,没有参与袭击我的活动。但我没有排除个别干部,多数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新提升的造反派,在幕后指使的可能。
整个一九七零年,造反派和新结合进来的老干部,在甲匾每个政府部门中相互共存。相互敌视和不合作的气氛中,没有什么工作可做。原来那一套不恰当的官僚制度,实在已难以使用了。假如在文化革命中新提升的造反派实施一项新的计划措施,那些新结合进来的老干部大多不了解这些情况。同时,造反派肯定不让新结合的老干部恢复他们在文化革命中所失去的全部权力。在许多情况下,新结合的老干部发现自己的职务和地位虽然恢复了,但实际上仅是个傀儡而已。造反派在行使各项权力时只当他们不在场一样。
〃许多自称是我女儿朋友的人来看望我,老是谈论我女儿的死亡。我对他们感到厌烦。我是个老太婆,又动过大手术,我需要休息。〃我告诉他。他点点头表示关心。
〃为什么小偷要撕碎这纸牌?〃老李指着桌上的碎片问我,〃这不像是小偷干的。〃〃朱家告诉我说是小偷干的。〃我告诉他。
〃好的,今天下午我到朱家去和他们谈谈。〃我对他表示感谢后就回家了。
看样子老李并不了解有关我那一串客人的情况,因而我尚不能调查清楚谁在幕后指使打击我的计划。但我从老李没有反对我悬挂那张纸牌通告的事实中得到了一些鼓励。我决定另制一块同样的,再挂在门口。
我回到家里,阿姨已经来了。我告诉她去了派出所,并把纸牌的碎纸片给她看。她说,〃这肯定是朱家的人撕碎的。没有小偷从墙上进来,都是些谎话而已。〃〃朱家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做?〃我问她。
〃谁知道?〃她说。但我想她是知道的。
那天下午我过得很清静。第二块纸牌通告,没有被人打扰,也没有人敲锁着的大门。
第二天阿姨走后,我的决定要经受考验了。席的母亲来到我家门口。我以为她看了通告会回去的,但她没有走,反而敲门叫我。我虽然难以不理睬我的好朋友,但我必须这样做。接着她又日叫我,然后她就走了。
那天之后,我的外甥女带了她的小儿来了。她是我已故妹妹的女儿。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她还是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因为她的家庭出身问题,曾遭受到很多不幸,结果使她变得神经过敏而胆怯,她害怕得罪造反派。因为我进过看守所,她迟迟不敢来看望我,农历新年我叫阿姨去请她来我家的。所以我听到她在门外叫我,感到很奇怪。然而我仍没有去理她。过了一会,她也走了。
我怀疑席的母亲和我的外甥女两人,都是受人指使来试探我那张通告的。但我不能完全肯定。为此我决定去看望我的好友。
在我向席的母亲解释清楚为何我不能开门的理由后,就问她:〃你有没有读过我的通告?〃〃是的,我看过了。但是……〃她凝视着我,吞吞吐吐地没有说下去,好像她心里有话不能说出口来。
她不能自己说她是有人指使她来看我的。可能是因她感到有些羞愧,也可能是她怕我脱口而出随便告诉别人。她低着头看样子非常准为情。
过了一会,她说,〃你对那些客人,各忍一下不是更好?晚上睡不着,你可长期服安眠药。为什么要和人争论?你不害怕他们吗?〃〃不,怎么这样说,我可不怕。我要向他们反击。否则我会被气死或折磨死的。〃我告诉她。那时我即使这么说,我仍感觉怒气在从胸口喷出来。由于我女儿的死亡,使我比在看守时对造反派的仇恨更深一万倍。向他们进行反击,至少能使我得到一些安慰。
席的母亲对我说:〃我们是这么多年的老朋友了,我很爱慕你。假如我说过一些话或做过一些事,是我平时不会说的或做,我希望你能理解我。生活在我们目前的环境里,我们不能永远显露自己的面目。〃〃喔,是的。别担心!我完全明白。〃我说完就告别了。
她陪我走到马路上:〃你同意我对人说因为我身体健康情况而不来看你吗?你知道我有严重的心脏病。〃〃当然。我会因为见不到你而挂念你的。但这是最好的办法,我不愿使你为难。〃我说。
〃你能理解我,那太好了。我希望这种时间不会太长。你己要保重。〃看样子她似乎放心了。
每天下午,我继续坚决对没有事先预约好的来访客人拒绝开大门。大德从未向我提出有关门口纸牌的事。要是他在下午来我家,他总是事先小心地和我联系好。这样,两星期之后,就再也不见这些客人来访了。
但是这些人要打击、陷害我的行动仍未停止,不过从我家里转到马路上就是了。有一夭,我从外面散步回家,忽然一大群小学生围着我大叫:〃特务!帝国主义的特务!帝国主义的走狗!〃我自顾自地走着,没有去理他们。但有两个大胆的学生拦住我的去路,继续对我大叫。我不能随便将这些孩子推开。所以就停下来,轻声对他们说:〃跟我来,让我们好好谈淡。〃他们都逃走了。我到居民委员会去诉苦,但他们说除非我能说出孩子们的名字,否则他们便没有办法进行调查。
这种反常的情况天天发生,好像那些孩子在那里准备对我进行侮辱。我把每天外出散步时间更动,有迟有早,但结果仍然一样。这些孩子总是等在那里,而远处也总是立着那个推自行车的人。每当这些孩子开始高声大叫时,那人便骑上自行车离开了。
虽然这些孩子使人讨厌,也会引起马路上的行人向我盯着看,但我仍没有放弃每天外出散步的习惯。我只是不理睬这些孩子,好像没有见到或听到他们一样向前走着。
两星期后,阿姨又发现有人用粉笔在大门上写着:〃一个狂妄自大的帝国主义特务住在这里。〃她很恼火,要想用一块湿抹布揩掉。
〃阿姨,让它留着。〃我对她说。
〃这太欺人了,〃她说,〃我们门口的过路人看了会怎么想呢?〃〃他们爱怎么想就让他们怎么想好了。不管怎样,他们现在已习惯于看到这种讯息了。文化大革命初期,不是有许多这样的大字报贴在人家大门口吗?〃我按照我经常外出的时间上街,也看到那个推自行车的人立在对面马路的人行道上。他离开我不太远,我能看清他是个三十来岁留着一头乱蓬蓬黑发的青年。我也看到他自行车上有一个发亮的黄色鞍座套子。当他看见我出来,便骑上车离开了。我没有对那门上用粉笔写上的讯息看上一眼,就关上门出去散步了。
过了几天,一场大雨把门上用粉笔写着的字洗刷掉了。不久那些孩子也对他们的把戏感到厌倦。最使我感觉有趣的是虽然大德每天来时必然看到大门口用粉笔写着的字,但他却从未向我谈起此事。
我安静地度过了几天。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七日,是我从看守所释放回家的两周年。那天在初春温和的阳光下,我坐在凉台上打毛线,读唐诗。到了下午,我想起在牢房里度过的日子。回忆起每个看守及审问员,就再次使我感到在看守所里所遭受的寒冷、饥饿、以及痛苦的刑罚。我看着那将终身留在我手腕上的伤痕,使我感到好像我虽然已不是被禁闭在监狱的牢房里,但是我面对着被迫害的斗争尚未结束。我的对手仍徘徊在四周,我得继续加强警惕。
我心绪不佳,不愿外出,因而也打消了下午外出散步的习惯。以后两天,连续细雨。当天气转晴,太阳高升时,我急着想外出活动。
〃你想出去散步吗?今天天气很好。〃阿姨离开时这样问我。
〃喔,当然我今天要出去的。〃我告诉她。
〃我想你把那旧的拖地木柄'4'带去,到合作社去做个新的。〃〃需要将那旧木柄带出去吗?〃〃是啊,外面缺少木柄。你不把旧的带去,他们不肯给你新的。〃下午三时是我外出散步的固定时间。我带了那根旧的拖地的木柄,出发到一家合作社去。那里有几个附近的家庭妇女在打零工,赚些额外的收入。开始我未发觉是否有人跟踪。但当我走下人行道准备过马路时,突然感觉有东西在我背后重重地将我打倒在地。我背部着地,平躺在马路上。这时对面有一辆公共汽车开过来,接着当刹车尖声响时,有一个人把我拉向一边。那辆公共汽车慢慢地从我的拖地柄上滚过,将它压碎了。那位售票员从窗口对我大嚷:〃你为什么走路时不向前看看?你要自杀?〃然后那辆公共汽车便加快速度开走了。
接连发生了几件出乎意料的事情,我真感到眼花缭乱,心猛跳得厉害,膝部也在颤抖。
〃一辆自行车将你撞倒在地,那人没有停车。〃营救我的人说。
〃你救了我的命,我将怎样谢你?〃我的声音发抖,听起来好像另一个人在说话。
〃不,不,是那辆公共汽车及时刹车了。你最好到医院里去检查一下,是否有骨折?〃那位好心的人说。
〃我想我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感觉有些发抖。请你和我一同回去,我要送你一些礼物表示感谢。可能你愿陪我到附近派出所去汇报这件事故。〃我说。
〃你没有把那骑自行车的人抓住,派出所不会负责的。我还得去参加一个会议。〃〃你有没有看清那撞我的人?〃〃真的没有,不过我看见他自行车座位上有闪烁发光的东西。〃〃是不是黄色有光的座套?〃〃他坐在座位上,但好像有光在我眼前一闪。〃〃他是不是长了一头乱莲蓬的黑头发?〃〃是的。你认识他?〃那人问我。〃他是你的仇敌?〃〃不,我不认识他。但过去我曾见到过他。〃〃好,我要去开会了。你自己要当心,他是有意撞你的。马路上很空,他不应该撞你。而且他离开时,把车踏得很快。〃我再次向他表示感谢后,他在人群中消失了。
我回到家里,吃了两片阿斯匹灵就睡觉了。那时还只刚过四时。我睡了约有一小时就醒来,觉得全身僵得像块木板,而且又痛得难受,几乎不能行动。好不容易从床上下来,到浴室里。我想洗个热水澡会好一些,但是阿姨不在,我无法准备热水。
那一夜好像过得很慢,我全身又感觉很不舒服。后来阿姨侍候我在床上进早餐。她听了我谈发生的事故很感担心。她可能在私下猜测我是被人有意撞倒的,对她来说也负有部分责任。因为她曾向人提过我去什么地方的。整个上午,她似乎在淌眼泪。
当她为我准备热水洗澡时,我在床上读唐诗。忽然我想起胡先生和我约好今天下午来看我。虽然我很想躺在床上,但我还是起来整理了房间,因为我没法通知胡先生今天不要来。自从红卫兵采取革命行动后,在中国没有人被准许装私人电话。要打电话须到公共电话旁。那里的负责人把我们打的电话号码记下来,并能听到电话中的全部谈话内容。那负责人经常守在那里,以便把电话机锁上。
胡先生于下午四时来到。我将阿姨在厨房里准备好的茶和饼干拿出来请他吃。然后我告诉他我被一辆自行车撞倒,差一点给一辆驶来昀公共汽车从身上压过。我预测他会大吃一惊而对我表示同情或仅是对我表示担心。但是他却认真地对我看着说:〃让我来保护你!假如你同意我来照顾你,我将会多么高兴!〃他似乎控制不了感情,说话的声音有点激动。
这意思是否在求婚?我还不能肯定。同时因为我一直把思想集中在考虑我四周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他对我感到有些意外,好像我的沉默不言使他感觉不好意思。很快他接着说:〃你认为只有年轻人才能结婚?可能我对你直率求婚使你大吃一惊,是吗?〃〃咳,不,不是这意思。我认为老年人结婚是完全应该的。我想有许多女人能和你结婚会感到自豪和幸福的。我对你深表感谢。你向我求婚也使我感到很得意。但我已向我已故丈夫起过誓,我将终身保持陈太太的身份。〃他默然微笑着握住我韵手勉强地说:〃我不认识其他任何女人。我曾等着……但你别介意。我对你这种忠于你丈夫的决心表示尊敬。我对他非常尊敬也很爱慕,他是个好人。〃他轻轻地将我的手捏了一下,就放开了。
这使人难堪的时刻过去了。我坦率地回绝了胡先生,但没有使他失面子。这可不是中国人习惯上的做法。
自从那天下午以后,胡先生仍一次次地来看我。他总是显得很高兴,对我也很关心。但他每次来访之间相隔时间渐渐地加长了,直至恢复到他的老习惯,每逢中国农历新年来望我一次。一九七八年他专程来告诉我他已平反,恢复原来工厂里副厂长和总工程师的职务。他在繁忙地处理文化大革命中遗留下来的种种问题,并试行全面恢复生产。
〃我每天工作十六小时。我真想自己能再年轻些,可以多做些工作。要学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可惜我自己己不中用了。〃他说着。看样子他很高兴,似乎忽然年轻了十年。
一九八0年,我取得护照要离开中国时,我写信去向他告别。他立即来看我,并对我说他始终认为我是希望离开中国的。但我认为胡先生从未了解为何像我这么大年龄会选择到国外去开始前途不明的新生活,而不愿安静地在祖国的现成家庭里定居下来。
在六十岁的年纪能得到一位富有男人的求婚,即使不是太兴奋也是愉快的。虽然我的四肢酸痛,但第二天早晨当大德来上课时,我精神仍很好。
我刚吃完早餐,把前门打开,就听到他从楼梯上跳上来。我看了看钟,发现他早到了二十分钟。
〃你今天来得早。〃他出现在门口时,我就对他说。
〃我有件使人兴奋的消息告诉你。〃他大笑着进了房间,〃我可能不久就要去北京了。〃〃真的?你找到工作了吗?〃我问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