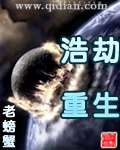上海生死劫-第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李菁和我到花园去。老赵在花园里准备了两把柳条藤椅,上面置着靠垫,一盘蚊香,置在两把椅子当中。然后再送上两杯菊花茶。从窗口飘来一阵时隐时显的小提琴声,我把自己整个身子埋在藤椅之中,仰头凝视着布满星斗的苍穹。
〃你过得真舒服,〃李菁感慨地说:〃你的生活不仅在中国,就是以西方的标准来说,也是第一流的。我怕,这是否会引起他们的不满?〃〃完全可能。那些审查我的人,看上去十分仇恨我。你是否相信,中国工农群众的贫困,是因为因们的过失?〃〃他们不过是妒忌而已。人们不可能过着一样的生活。我有一套大公寓,是学校分配给我的。那表示他们也是不愿搞平均主义的。〃李菁说,她现在似乎显得轻松点了。
〃自然,你情况不同。你为国家做了许多事情,你亲手培养了几百个学生,他们都从你那里学到许多东西,那不是很美好吗?〃我从心里羡慕我的朋友李菁。
〃但在学院里,从来没人对我说过这种话。他们总是说,我把腐朽的西方音乐拿来腐蚀青年。他们从来不曾想刭,如果国家真的如此明文禁止西方音乐,我就不会这样做了。我们的教材在给学生讲授前,都事先经过党委审批的。他们好像已忘记了,在五十年代与苏联友好时,还鼓励我们教授西方音乐呢。〃她越讲越气恼,到后来,都发起怒来。我就不在提及她的工作了。为了让她高兴,我问起她孩子的近况。
〃对我来讲,他们离我那么远,特别现在,他们都各自成家了。〃她说。
〃你不想去看看他们?〃〃喔,当然想。但想又有什么用?他们不会签给我去澳大翻亚的护照。当然,我的孩子们,也不会到这儿来。〃〃其实,你真不该从香港回来。〃〃那时,我认为这是最好的决策。你知道,我对音乐学院感情很深。我在这里受教育,又在这里执教,它真正是我一生中,除我孩子之外最最重要的一部分。我的许多同事都是我在音专的老同学。我在香港时,他们粕写信给我,我的学生和党委书记,也写信给我。他们都说音乐需要我,我就回来了。〃〃那苏雷的家属对你返沪是怎么想的?〃〃苏雷故世后,他们很关心我。他们家多数成员都已在澳大利亚定居了。他们是个很团结的家庭。那些叔伯们都认为苏雷的孩子,就是属于苏家的人,但他们不认为我与苏雷的孩子一样重要。当然,假如我无法谋生的话,他们会照顾我的。但我不喜欢自己处于这种状况下,寄人篱下,仰人鼻息。〃李菁话里最后几个字,被一阵激烈的锣鼓声淹没了,老赵到花园里告知:〃屋前,正好有一支学生游行队伍走过。〃那正在欣赏音乐的年青人也涌到凉台上来,孔那个青年演员说:〃那好像是红卫兵。几天前,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过他们的代表。这意味着,毛主席已承认了他们这个组织。〃〃这是谁组织的?〃我间他,〃我从未听到过有'红卫兵'这个组织。〃〃我听说,这是江青支持的文化大革命中所产生的新生事物。人家告诉我,事实上,她暗中组织了一批清华附中的学生,然后假说是学生自发组织的。因为她是毛主席的妻子,'红卫兵'这个称呼,便更受人欢迎。现在,她代表毛主席公开批准红卫兵这个组织了。〃孔说着就笑了,〃我爸说她过去不过是个普通演员罢了。现在似乎身价百倍了。〃(后来当江青在清理电影界的〃敌人〃时,孔的父亲经历了一个可怕的遭遇,总算保全了一条命。孔本人也因父亲牵连,几年来没有在任何片中任过主角。)次日,我在报上看到八月十八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消息。在第一版上,载着毛穿着卡其布军装,手臂上戴着写有〃红卫兵〃三字的红袖章的大幅照片。〃红卫兵〃三字是他亲笔题的。在天安门检阅台上,他接受了台下聚集着的青年们的热烈欢呼,微笑着对他们招手。他对红卫兵指出的特殊任务是:在全国各地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当时全国青年,把他们自幼就崇拜的对象的指示,作为自己的武器。在文化革命初期,上面布置的斗争对象,仍是〃资产阶级〃。红卫兵的矛头,也仅针对他们。
八月十八那晚,成群结队的红卫兵在我们屋前走过,敲锣打鼓,大声呼着口号。曼萍和她的朋友们都上街去看游行了,李菁和我回到书房去。外面的声音震耳欲聋,我们都无法讲话。口号声中似有〃保卫毛主席〃,当曼萍独自一人回来时,她告诉我们,那些学生高举着毛的画像高呼:〃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谁会攻击他加害他呢?〃我问。我们都没法回答。像他这样拥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受人崇拜的人物,似乎已经不是凡人了,还有谁会攻击他呢?
略等片刻以后,李菁说:〃我该回去了。以后总会把情况弄明白的。〃〃我送李阿姨回家吧,路上都是游行队伍,已没有公共汽车了。〃曼萍说。
我把他们送到大门口,看到游行队伍,都由十几岁的青年组成。他们高举着口号标语和旗子,捧着毛主席的画像,走过我们屋前马路。前排有人敲锣打鼓,每隔几米,就有个领呼口号者,口号写在纸上。其余的随着高呼。每个游行者臂上都挂了红袖章,上面仿着毛的字体写着〃红卫兵〃。看来,这个队伍组织得有条不紊,统一领导,似不像是青年人自己组织的。我想,幕后一定有当权派在操纵。
李菁和我互相道别了,曼萍推着自行车与她并肩而行。我目送着她们,直至李菁的满头银发,在游行队伍中融化消失了。
那是我对亲爱的朋友最后的一瞥了。一个月后,当我在隔离时,她自杀了。在一次对她极端侮辱的批判会上,红卫兵们把一根离地不到四尺高的竹竿横在音乐学院门口,要地从下面爬进去,以示她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因为她在英国受过教育。后来又开了斗争会,强迫她承认她〃热爱西方音乐〃。次日,她被发现,坐在钢琴边打开了煤气开关。她留下一张纸条,上面仅仅留着一句话:〃我为我的学生尽力了。〃我的佣人们都休息了,我在楼下等女儿回家。她回来后,我俩默默无言地上了楼。在楼梯口,她用手臂环抱着紧搂了我一下,表示着向我道晚安。我似有很多话要对她说,我想告诉她,我是多么爱她!她对我是如何珍贵,是我的安慰。但一团凄迷愁人的情绪堵住我喉咙。我怕我什么也说不清,于是,我什么也没说。
〃我永远也忘不了今天的生日。〃我女儿幽幽地说。
当她回自己房后,我把窗关上,以隔绝马路上的喧嘈声。这样,声音似乎轻了点,但因为凉风吹不进屋,室内很是阿熟。马路上的游行队伍络绎不断。男女青年们怀着火热的革命热情,高呼口号,迈着革命步伐的声音,依旧阵阵传入室内。
我走进书房,从书架上抽下一本书,但却一个字也读不进,我放下书本,毫无目的地在房里徘徊着。我把花瓶里的花重新插过,清理掉已凋落的,再往瓶里添点清水,又把墙上的油画扶扶正,轻抚一下牙雕上精工细刻的花纹,外边的游行队伍还在持续着,即使他们不打我大门前走过,依然听得到阵阵震耳的锣鼓声。我在房里漫无目的地荡了一圈,就踱到曼萍房里。她没听见我轻轻的敲门声,我轻轻推开门,发现她已睡着了。她一头乌黑的秀发散放在洁白的枕头上,甜甜的脸庞显褥那么平静、安宁。门外透入的一抹柔光,照在她床头边柜上置着的,嵌在银质相架里的我丈夫脸上,我轻轻把门关上。
我心中唯有两个亲人,一个已死了,另一个还活着,但将来等着她的是什么呢?命运,是无法预测的。
〃你要自己保重,照顾好曼萍,我为这样早就要离开你俩而难过。〃我又记起我丈夫临终弥留之际,以微弱的声音对我所说的。那已是九年前的事了。他要求我好好照顾好曼萍,我已遵照他的嘱咐做了。我看着女儿渐渐地长大成人,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安慰,她很聪敏,漂亮又热情活泼,我对她十分放心。但现在,自文化革命开始以来,一团乌云始终笼罩着我们。当我想到将来时,我只感到一切都毫无把握。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感到无法把握自己生活中的方向盘,也无法引导我的女儿。这些念头让我恐惧不已。
从前,我就凭借着不断地排除困难,迎接新挑战,适应新情况及享受乐趣而过活。自一九五七年丈夫逝世后,我的心已碎了,一时几乎觉得已没有活下去的信心了。我认为,唯有采取积极的态度,把困难一一解决排除,才能治疗我的创伤,恢复我的勇气。
在中国,自古以来,当一个女人失却了丈夫后,也同时失却了她自个的人生价值。实际上她们已不是〃人〃了,只能受邻里耻笑,还有〃寡妇门前是非多〃的说法。虽然一九五二年人民政府制订了新婚姻法,保护妇女权利,反对重男轻女,但对寡妇和老处女,依然存在某种偏见。中国社会,似乎对能自强自立韵女性,并不欢迎或不以此为荣。
我刚刚开始在亚缨亚公司就职时,那些高级中国职员,看到一个没有经营经验的女人来领导他们工作,觉得很是意外。我就得反复表现出我自己的能力,以此赢得他们的尊敬和信任。对我来说,没有比接受新挑战和克服困难更使我感兴趣了。我为我能在丈夫逝世后仍可维持原来的生活水准而感到高兴和自豪。但在我一生中,我从未有过像在文化革命中那样迷茫怅然。据我所知,每当一个中国人被派往外资公司担任高级职务时,必须先经工商联及上海市公安局审核。因为公安局储有每个人的档案,政府理应对我作过全面了解。似乎不存在对我进行审查的理由。而薇妮、李菁及胡先生,都认定我在劫难逃,将成为这次运动的对象。除了坚决拒绝写假交代外,我真不知道我该如何是好。但真这样做,必定会使我与他们对立,这种对抗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呢?会对我女儿有啥影响呢?我伫立在女儿的卧室外,陷入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望之中,我唯有祈祷,恳求上帝的保护。
自毛主席在北京接见了第一批红卫兵,并表扬了他们后,几天中,上海马路上成了红卫兵的世界。报上又宣布了,红卫兵的任务是扫四旧旧文化、旧风俗、旧思想、旧习惯。对〃旧〃字并没有明确的概念,全部由红卫兵来决定。首先,他们将上海的马路改了名。沿黄浦江外滩一带最大的马路改为革命大道。另一条主要马路为纪念〃八·一〃建军节也改了名。苏联领事馆所在的马路,改名为反修路。而英国领事馆前的马路,则改为反帝路。我又发现,我家所在的马路,改为欧阳海路。这是为了纪念一个士兵欧阳海,他为了拉走一匹因受惊窜上铁轨的马而献出自己的生命。红卫兵还在讨论,是否要把红绿交通灯也改革一下,因为,他们想,红色应标志着革命前进.而不是停下。此时,交通灯也已停止开放。
他们砸掉了鲜花店和,工艺品商店,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富人才有钱买这些无聊的东西。他们对其他的商店都一一进行检查,凡他们看不入眼的,或他们认为不适宜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便进行毁坏或没收。他们的要求极严格。因为他们认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不应该坐沙发,因此,所有的沙发,一下都有如洪水猛兽,不可接近。另外如席梦思床垫、丝绒绸缎、化妆品,西方流行式样构衣服,都扔在马路上,等着拉出去烧毁。
按中国惯例,商店在命名时,常取吉祥之兆,如〃富丽〃绸布店,〃美昧思〃饮食店,〃天禄〃鞋帽店专门经营老年人的帽子,〃康福〃皮鞋店及〃全家福〃家具店等,即使在一九五六年政府把商店合营时,都未改变店名。现在,红卫兵命令它们必须把店名改为革命化的名字。许多商店经理不知怎样来选择新的店名,但最热门的名字,就是〃东方红〃,它是一首歌颂毛泽东的歌名,在文化大革命中,它几乎代替了中国国歌。陈列在橱窗里的商品都搬走了,取面代之的是毛的画像。因此当人们在商业区行走时,马路两边同名的商店,使人们弄不清它们究竟经营什么商品,与此同时又让人有一种极紧张的感觉,似乎有成百双毛的眼睛在盯着他们。
每天,我的佣人们总给我带来有关红卫兵的可怕行动,我对此很好奇,我想自己冒脸出去看看。
我有两张商业区银行的定期存单,适逢到期。我决定兑现一张以备家常开支,因为经验告诉我,凡一场政治运动之后,必然会带来食品供应缺少及紧张。有时为了活命,只得去黑市场购买所需的食品,但那里的价格却是惊人的。记得在大跃进失败后的困难时期,我的厨师花了五十元钱买了一块猪肉,而平时的正常价格,不道二、三元。
老赵和陈妈,都要我在出门时注意一下穿着,因我们一位邻居太太在出门看朋友时,碰上了红卫兵,他们没收了她的皮鞋,剪破了她的长裤,弄得她狼狈不堪。因此我在去银行时,穿上一件旧衬衫,并向陈妈借了条大腰身的长裤,一双胶鞋。因为八月的日头,仍然是热辣辣的,陈妈又给找来一顶阔边草帽,那是我女儿在农村巡回演出时用的。
马路上人声喧闹,处处都能见到红卫兵,也有看热闹的。在文化革命初期,〃敌人〃只是指资产阶级分子,因此大多数老百姓,都有一种安全感。他们对待红卫兵的所作所为,持隔岸观火的态度。许多人在马路上闲荡着,看看热闹。
东一簇西一堆的红卫兵,给看热闹的人们宣传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意义。有几个红卫兵的宣传,令我很不理解。他们对群众说:文化大革命将把他们解放出来。广大人民不是在一九四九年就解放出来了?是否那次的解放还不彻底,因此还要进行第二次解放?在我看来,似乎共产党在做自我批评,但那是极其不可思议的。因此,我认为我一定听错了,也可能那是小青年的口误。事实上,不久,〃重新解放无产阶级〃已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宗旨。官方舆论公开指出:共产党党内的敌人,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司令部,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只是这些论点直至年底方才明朗起来。
有些红卫兵干扰公共汽车的行驶,他们散发传单,向行人作宣传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