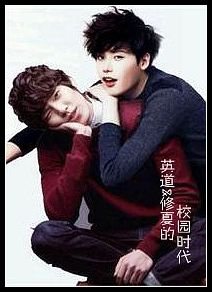走过错过-第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就不跟她玩了,我说:我不就在你前面吗?可可就在我的腰间拧了一下。我说我可没有骗过你,是你自己想得太多了,哈哈。
夜很静,因为听不到人的说话声。夜同样热闹非凡,对于昆虫来说,夜晚是虫子的天下,他们在开晚会,唧唧咕咕的。我说:可可,你听过吗?
可可说:听什么啊?
我说,你真的没听到吗?
可可低声说:你听到了么?是什么声音?
我说:你真的没听见?
可可说:没。
我问:那你在做什么啊?
可可说:我在注意旁边的动静啊。
我说:有我在你就别怕了嘛。你说这山沟里能有什么东西啊?用得着你怕吗?其实啊,夜晚和白天一样,你想夜晚就是白天把眼睛闭上这么简单。晚上还不会像白天那样一走神就撞到人了呢。
可可说:我现在不怕那些鬼啊什么的东西了,我现在担心受到野兽的袭击。
可可的话提醒了我,我怎么没主意到这个问题呢?可可的话并非没有道理,这深山老林的,难不会有野兽出现,这苗寨的木楼建造的结构本身就为了防止野兽袭击。我说:不怕,有我在,这山里不会有什么猛兽的,最多也只是个黄鼠狼或野猫之类的小动物,不会有危险的。但我也是有点心虚,不断把脚碰到鞋帮里的匕首的触觉传给大脑,让我知道它还在。
可可说:你听到什么声音了?
我说:虫子叫啊。
可可静静听了一阵子,说:满好听的啊,就是我从来没有同时听过这么多虫子一起在叫。
突然我的手机响亮,铃声就像一枚炸弹划破夜的宁静,并带来了莫名的恐惧。我和可可都被吓了一大跳。但它也仅仅是响了不到两秒钟,我打开看到一个陌生的号码,我不理它了。可可问:你怎么不回电啊。我说:这都习惯了,十有九是六合彩的。
几只萤火虫在不远处飞舞着。我就知道要带可可去看什么了。我往后看了看可可,她背后的山寨,零星亮着煤油灯的昏黄的灯光,远远望去,就像一只停在叶子上的萤火虫。也许是孩子们在用功吧。我也只能在煤油灯下才能安心做功课,就因为小时候家乡建设落后经常停电,我才得以常常在昏暗的灯光下做功课,那时候的成绩好的原因就是得益于这煤油灯。后来,就很少停电了,日光灯太亮照到的地方太宽,空荡荡的,总是安不下心了,就只是看电视。开始在家就不做功课了。
我把可可带到小河边上的水车旁,在磨坊伸向水里的木板架上并排坐着。可可刚到的那几天,天天和喜妹来这里坐,她们把嫩白小腿吊在水里,不停地踢着从她们脚上哗哗流过的水。她们指挥我要我帮他们摘野花,我就在河边的草地上乱跑,把各种各样的花一束束送到他们的手上,黄的白的粉红的。她们抓在手里闻闻,可可更是大鼻子大鼻子地吸着花儿淡淡的清香,不幸花粉吸得太多,不停地打喷嚏。她们把花一朵一朵摘下来扔到水里去,花儿随水向下悠悠飘去,一朵一朵,黄的白的,粉红的。很美。我说:两位仙女在散花啊。很快她们又让我去摘花了,我很快活,做了护花使者,把一束束花护送到两位花仙子手中。
身旁的水车像位老人,在推动磨石的同时也把清清的河水送往菜地里去,它以独特的方式为周围的虫鸣作伴奏,吱吱的木架的转动声,哗啦哗啦竹筒的倒水声。可可不敢把小腿放下去,下面黑黑的,偶尔闪着反射的星光。
我指着小河对面,用肩膀碰了碰可可柔柔的肩,说:你看。
可可顺着我的手看去,惊喜地说:萤火虫!好多萤火虫啊!好漂亮啊!她的兴奋无法随着声音发泄,两只手紧紧抓住我的手臂摇。说:这就是书中说的萤火虫啊!
我问:你没见过萤火虫吗?
可可望着飞舞着的萤火虫,说:没见过。
我们都不说话了,萤火虫我见过多了,但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萤火虫聚集在一起,有几十只萤火虫飞舞在不到一张桌子大的空间里。它们的队伍还在不断扩大,附近的萤火虫慢慢向这里靠拢。我和可可都默不作声,生怕我们的声音把它们吓走了。几次我以为可可睡着了,她的目光专注得一眨不眨。不到半个小时,我们的河的对面聚集了有一百多只萤火虫,它们围在一个很小的地方飞舞着。像一个巨大的夜明珠,把下边的河水都照得一片透亮,倒映在水中的萤火虫更能展现它们优美而神秘的姿态。不时有几只飞到我们们身边,我们的眼珠子就跟着它们飞行的轨迹转。
良久,可可才说话,她说:我现在才发现其实很多美好的东西都不是能用笔所能描述的。我读小学的时候,就听说过萤火虫,一闪一闪的美极了,忽悠飞在空中,像星星却是星星无法比拟的,它们是活生生的生命。长大了点,我接触到了一些写萤火虫的文章,我更是对它们无比神往,书里的描述那么生动。流萤啊,多好的名词。我在伤心的时候看到这些写萤火虫的文字,心就会舒服点。现在看到活生生的萤火虫,这么美,不是一个美字所能形容的。现在回想起那些文字,觉得是那么的拙劣啊,这眼前的景物怎么可能用文字表述啊。这都是有生命有灵魂的,你再怎么妙笔生花,你的笔尖也是无法描绘得到生命的。和爱情一样,没有亲身去感受又怎么能体会到其中的酸甜苦辣悲欢离愁呢?
我想女人的情感真是微妙,我说:是啊,你说得对,有灵魂的才是真的。
我说:听你这么说,你是经历了爱情的种种酸甜苦辣悲欢离愁咯?
可可说:那倒没有。但还是经历了那么一点的,就是没有生命大起大落,平平淡淡的,好像也没什么意思。
我说:你这么漂亮难道没有男孩子追求你?
可可说:有是有。我一听心里就是另一种滋味,涩涩的那种。
可可说:他们都是些乱糟糟的家伙,不是流里流气的就是假正经。
我说:那你喜欢他们吗?
可可说:我想没有吧。我在过去的感情上没有什么是让我觉得伤心的,也没有什么是值得我去留恋的。那你呢?
我本想挖挖她爱情方面的一些想法和经历的,不想被问回头。我支吾说:这……不知道怎么说。脑里搜索着可以应对的话。我说:这个好像有过又好像没有,我也不知道算不算,也许不能算吧,就是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看待的,我也不了解她是怎么想的,也许是没有吧,我也想是没有吧。我在自己不知道说什么的时侯还要说,就是说了等于没说的那种。
可可说:唉,我也不知道怎么说这些事。
可可问:哎,你说这些萤火虫都聚集在一块,它们做什么啊?不是说萤火虫都是单个单个的吗?
我说:是啊,可现在它们在繁衍后代啊。
可可顿了一阵,说:那它们不是很多兄弟姐妹?
我笑笑说:那当然啦,它们是昆虫啊,一生就不是一只两只了,是一窝一窝或者一群一群。几十几十的生的啊。
可可说:这么多啊!那你有几兄妹啊?
我以为可可在开玩笑,把我当昆虫了。可可说,我是独生女,我多希望可以像你们一样有兄弟姐妹啊。记得读幼儿园的时候,一次我和一个同学为了抢一样东西玩打起来了。你知道吗?我胜利了,可没有想到的是,她有个哥哥,她哭着叫哥哥来,用手指这我说:她打我。于是我就被她哥哥揍了一顿,他们两兄妹一起打我啊。我当时是多么的无助啊。
可可说到这里,如果是平时,我肯定会说,你不也以大欺小打人家妹妹吗?活该。但可可说话的口气很沉闷,像一个虞城的教徒向上帝忏悔。
可可说,我当时哭了,我不是因为被他们打哭的,我哭为什么我没有个哥哥帮我打他们呢。我怎么没有哥哥保护我呢?唉,我多想有个哥哥疼我爱我帮我呵护我,不开心的时候有哥哥陪着,可以向哥哥撒娇。或者有个姐姐也好,和我去逛街买东西,帮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有弟弟妹妹也好,我就保护他们,帮他们打扮得漂漂亮亮,和他们玩游戏,教他们学习。
我说:兄弟姐妹啊,小时候是好,大家懂事。都相互帮忙。长大一点知道了一些东西就渐渐地发生冲突了,经常打骂。长大了,就没有这回事了,出门在外,总是挂念着他们,想他们过得好不好,工作顺不顺利。
夜幕散落在身边,空气变得清凉。可可双手抱膝,继续说着。她说,我的父母都是做生意,一天到晚都不见人影,小时候就是早上送我到幼儿园,放学把我接回家。家总是冷冷清清的,没有人和我玩,没有人和我说话,他们总有忙不完的事,就是我生日了,他们也很少能陪我一起度过。我小时的记忆就是在四面墙的房子里,从窗子张望着外边玩乐的同龄人,我希望自己是只小鸟,飞去自己想去的地方,不要困在笼子里。我不到八岁就能自理生活了,我可以自己洗衣服,自己煮方便面吃。我很小就懂事了,父母不在家我也能把自己照顾得好好的,他们请来的保姆都被我赶走了。看到爸爸妈妈都那么陌生,我有怎么能让一个更陌生的让在面前晃来晃去呢。我就喜欢一个人,习惯了。
可可说,我怕黑,睡觉我就把屋子的灯都开着,半夜醒来也不会觉得害怕,可以睁开眼就看到身边的布娃娃,它们是我陪伴我的朋友。屋子很静,白天也一样,灯亮着,就没有白天和夜晚之分了。越是长大,他们在家的时候就越少,我习惯了。当我来到这里,去到学校,看见这里的孩子,上学放学都成群结队的,有说有笑,多开心啊。而我的世界总是一个人,我对玩具熊说话聊天,跟电视里的人物交流,对着镜子说心事流泪。
我问:那你没有朋友吗?
可可说:没有。上大学之前没有。我总是自己一个人,连个要好点的同学都没有。你不会想到吧,我很内向的,我不喜欢和人说话,可能是小时候沉默惯了。也不知道能和同学们说些什么。上大学后,很多同学多觉得我古怪,就来研究我,这么我才有了些朋友,但不多,可能是因为我不能玩的缘故吧。总是很郁闷。不过我发觉我来这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看我现在,你觉得我挺开朗的吧。我啊其实不知道是怎么了,就是想说话,想玩玩,很新鲜,这里。
可可这点和我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我很快就会随着时间而慢慢改变,改来变去也只是个轮回,我始终没有改变,是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性格而已。我告诉可可,你也会像我这样的。
可可说:也许吧,但总会发生点变异的。
我说:这么多年来,我倒没有觉得自己有变异。
可可说:当局者迷啊,一个人的变化自己很难知道的。
我说:那倒可能是吧,不过你发现了哦。
可可抿嘴一笑,把头枕在我的肩上,夜风吹过,一阵淡淡的洗发水的清香。第一次有女孩把我的肩膀作依靠。感觉很好,就是有点紧张。我很瘦,想可可她会不会靠在我的肩上不舒服。我想我能不能让身边这位美丽的女孩觉得有安全感,和她会不会发生一些诸如电视爱情片那样有缠缠绵绵曲折动人的故事呢?可是喜妹她又怎么办,这是我异想天开,自作多情吧。我们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我心里十分之三是喜妹,十分之三是可可,十分之一是一些与我素未谋面的年轻美丽的姑娘。还有未来占十分之二,家人十分之一。当然只是现在而已,以后会怎样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喜妹不是不理我了么?我又想。
我们回去时,东南方的夜空升起了一弯新月,夜变得有些凉了,雾水一点点地渗在皮肤里,凉涩涩的,头顶像对着空调,冷气比空调来得慢,无意之中把头发沾得湿湿的凉凉的。相信已是凌晨时分,可可略显疲惫。
可可还是不肯回自己的房里睡,我说:难道不睡?明天还要上课啊。可可躺在我床上,斜斜地靠在墙的一侧。不住地打啊欠,说,睡啊,我就在你这睡了。
我觉得可可此刻的神态非常搞笑,就说:你睡我床上,这孤男寡女的,等下发生什么事怎么办啊?
可可说:能发生什么事啊?
我笑说:你就不怕我把持不住?
可可说:什么怎么了?你敢!
我当然不敢。可可说了这句话不到一分钟就睡着了。我就挨在椅子上合眼。毕竟椅子是用来坐而不是用来睡的,三五分钟就醒来一次。每醒一次就偷偷看可可一次。实在睡不着就更加明目张胆了,移近煤油灯,手肘顶着大腿,手掌托着下巴打量着沉睡中的可可。梦中的可可嘴角微微翘起,几条发丝沾在嘴唇上,闭着的双眼有薄薄的光波在荡漾。我听得见她均匀轻快的呼吸,胸脯一起一伏,我就把注意力全放在她起伏的胸脯上,一种欲望有喉咙往上升起,我不停地吐口水。我控制住自己,不能这么做。就把目光转向可可的嘴唇,可可的嘴唇很美,丰满欲滴,红润有光又让人不觉得肥腻,我轻轻地拨去嘴角的发丝,样子更显抚媚动人。我想我要是再这样看下去会犯罪的。可可身子略略翻动,额头上渗出湿湿的汗,我就拿了本书帮她扇风。不知多久,我就屁股坐在椅子上,上身趴在床上可可的旁边睡着了。并做了个梦:
几天来,我都在为等一个女孩子的来信而枕食难安,上一封信已让我等得十分不耐烦了,
这次不至于要更久吧,我就准备在写一封去问个究竟。
我走在冷清的街道上,我思索着该写些什么,要有等得不耐烦的语气,也不能让她感觉
我是一个没有耐心的人。双手插在裤袋里,低着头。在街边的一块空地上,有个桌子罢在那
我就坐在桌子旁的椅子上,桌子很乱,和我的一模一样,都放着喜欢看的书还有散落的稿纸。
我拿起笔就写。
手机响了,它可以放MP3和放电影电视了,我激动得放下笔欣赏着搞笑的动画片。而它
只是一台我用了两年的波导S…788。
对面的女孩很捣蛋,她把双方的十多支笔搞混,满桌子都是,威胁我不要拿错她的笔。
一连三天,我们都在桌子那里相见,斗气。这三天,和电视里的镜头的切换一样让人
毫无觉察。
她说她经常到这儿打羽毛球,和她的丫环一起打,很无聊。想和我聊天。
我告诉她,我的名字里就有一个“球”。
就这样,我们并列同行在这海边小城冷清的街道上。扫兴的是,她总有一个随从跟着,
是个男的,




![[重生]幸而我们不曾错过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19/19310.jpg)

![(全职同人)[全职高手同人]错过了春天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23/2340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