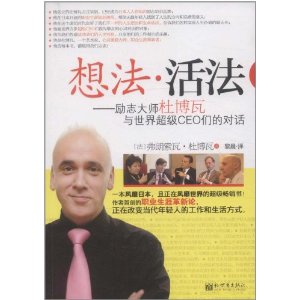与神对话-第10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是生命能本身,这你称为悲喜交集的流。
在任何时候这能量都能以你称为喜悦的方式表达。那是因为生命能可以受控制。就像将一个自动调温器由冷转到热一样,你能加速生命能的振动,从悲伤到喜悦。而我要告诉你这点:如果你心里带着喜悦,任何时刻你都能治愈。
但你怎么在心里带着喜悦呢?如果它不在那儿,你怎能将它弄到那儿?
它就在那儿。
有些人并没经验到那点。
他们不知道喜悦的秘密。
是什么秘密?
除非你让它出来,否则你无法觉得喜悦。
但如果你没感受到它,你如何能让它出来?
帮别人感觉它。
释放在别人心内的喜悦,你便释放了在你心内的喜悦。
在些人不知道怎么办得到。那是个如此巨大的声明,他们不知那长得是什么样子。
它可以用像微笑这么简单的事办到。或是一句赞美。或挚爱的一瞥。而它也可以用像(**)那么高贵的事办到。用这些方法以及许多其他的,你都能释放别人的喜悦。
以一首歌,一支舞,书笔的一挥,或黏土的塑形,文字的韵律。以手握着手,或心智的相会,或灵魂的合作。以共同创造任何好的、美的与有用的东西。以所有这些方法以及其他的行为,你都能释放别人的喜悦。
以分享一个感受、说出一个真理、结束愤怒、治愈批判。以倾听的意愿,说话的意愿。以宽怒的决定和释放的选择。以给予的承诺,和接受的优雅。
我告诉你,有一千种方法去释放别人心中的喜悦。不对,一千乘以一千。而在你决定去那样做的一刹那,你就会知道如何做。
你说得对。我知道你说得对。甚至在一个人临终之际也办得到。
我曾派给你一位伟大的教师,以阐明这一点。
对的。是伊莉莎白·库布勒·罗斯博士。我无法相信。我无法相信我真的有缘见到她,更别说成为她的雇员了。多了不起的女人啊!
我离开了安妮阿仑尔郡政府后,(在乔·阿尔顿的麻烦开始之前。咻!)在那儿的学校体系里担任了一个工作。他们有一个长期新闻助理退休了,而我去应征那职位。再次的,我在正确的时间位于正确的地方。我得到了更多不可置信的人生训练,从危机处理小组到课程发展委员会,样样都做过。不论是为议会的附属委员会准备一篇谈学校废止种族隔离的两百五十页的报告(再一次触及到黑人经验),或由一个学校到另一个学校,举行首创式的那种与老师、父母、学生、学校行政人员及支持职员之间的家庭会议。我都深深的投入其间。
我花了整个七○年代在那儿——我工作最久的一个地方——并且极享受前三分之二的时间。但终究,荣景不再,而我的任务开始变得重复又无趣了。我也开始瞥见越看越像一个死供堂的远景——我可以看见自己做着同样的工作三十多年。没有一张大学文凭,我晋升的机会不多(事实上,有这种高层次的工作我已很幸运了),而我的精力已开始衰退。
然后,在一九七九年,我被伊莉莎白·库布勒罗斯博士绑了票。可别搞错哦,那真的是绑票。
我那年开始帮伊莉莎白做义工,与一位朋友们——比尔葛里斯华德——合作,协调支持伊莉莎白的非常营利组织香提·尼拉亚在东岸的筹款演讲。比尔几个月前介绍我让识罗斯博士,那时他设法说服了罗斯博士在安那波里斯登台,也请我帮忙准备一些公开资料。
当然,我听说过伊莉莎白·库布勒罗斯博士。一位有不朽成就的女性,她一九六九年突破性的书《论死亡与垂危》(0nDeathandDying)改变了世界对死亡过程的观点,消除了研究死亡学的禁忌,孵出了美国安宁照顾运动的建立,并永远改变了上百万人的生命。
(此后她又写了许多书,包括《死亡:生长的最后阶段》及《生命:生与死的回忆录》。)
我立刻对伊莉莎白着迷——就如几乎每个见过她的人一样。她有特别具磁性和深具影响力的性格,凡我所看过被她触及的人,都真的与之前再也不相同了。在我与她相处了六十分钟后,我便知道我想要协助她的工作,并且自愿那样做,甚至不需任何人要求我。
在那首次会面之后约一年,比尔和我在波土顿筹备另一场演讲。在她讲完后,我们几个人在一家餐厅的安静角落,享受与伊莉莎白少有的片刻私人对谈。之前我和她会有两、三次这种对谈,所以她已听过我那晚再告诉她的话:我会竭尽全力的加入她的工作。
当时伊莉莎白正在全国举办“生命、死亡与转换工作坊”,与绝症患者及其家人和其他做她所谓的“悲伤工作”(griefwork)的人互动。我从末见过任何像那样的事。(她后来写了一本书《活下去,直到我们说再见》以了不起的情感力量描写在这些避静中进行的事。)这位女士以具意义且奥妙的方式触及人们的生命,而我可以看出她的工作使她自己的人生具有意义。
我的工作则否。我只是做我认为为了存活(或让别人也能存活)所必须做的。我从伊莉莎白那儿学到的事情之一便是:没有一个人必须那样做。伊莉莎白会以最简单的方式教这种非常大教训:给你单单一句话的观察,不许你争辨。那晚在波士顿的餐馆,我便被赠予了其中之一。
“我真的不知道”我耍赖地说,“我的工作再也没有什么令人兴奋的了,感觉上好像我的人生都消耗了。但我猜我会在那儿工作直到六十五岁,直到我领到退休金为止。”
伊莉莎白看看我,好像我疯了似的。“你不必那样做。”她非常安静的说,“你为什么要那样做?”
“如果只是我自己,相信我,我不会。我会明天就离开那儿。但我现在有个家得养。”
“那你告诉我,如果你明天死了,你的这个家庭,他们会怎么做?”伊莉莎白问道。
“话不能那么说”我争辨道,“我没死,我还活着。”
“你称这为活着?”她这样回答后,就转过身去与别人谈起来了,好像非常显而易见的,我俩已没有更多可说的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在她的旅馆与她的波士顿助手们喝咖啡时,她突然转向我。“你和我一起去机场。”她说。
“哦,好的。”我同意。比尔和我是由安那波里斯开车上来的,我的车就在门外。
在路上,伊莉莎白告诉我,她将往纽约州的卜吉普西去主持另一个五天的密集工作坊。“跟我一齐进机场里去,”她说,“别只送我到入口处。我需要人帮我拿行李。”
“没问题。”我说。于是我们便开进停车场去。
在售票柜台处,伊莉莎白出示了她自己的机票。然后放下一张信用卡。“我还需要这班机上的另一张票。”她告诉办事人。
“让我看看还有没有空位。”那妇人回答,“啊,有的,只有一个空位了。”
“果然。”伊莉莎白展开笑颜,好像她知道什么内部机密似的。
“请问另一位旅客是谁?”办事人问道。
伊莉莎白指教着我,“这一位。”她低声说。
“啊——对不起——?”我说不出话来。
“你要去卡吉普西的,不是吗?”伊莉莎白问道,像我们已讨论过这整件事似的。
“不是啊!明天我必须上班。我只请了三天假。”
“那工作没你也会做好。”她实事求事的说。
“但我的车留在波士顿了,”我抗议道,“我不能就这样将它留在停车场里。”
“比尔能来将它开走。”
“但……我没衣服穿。我没计划要离开这么久。”
“在卡吉普西有商店。”
“伊莉莎白,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就搭上一架飞机,而飞往什么地方。”我的心在砰砰跳,因为其实那正是我想做的。
“这位妇士需要你的驾照。”她边说边拼命眨眼。
“但,伊莉莎白……”
“你会让我赶不上班机的。”
于是我给了那女人我的驾照。而她递给了我一张机票。
当伊莉莎白大踏步走进机门时,我的声音尾随着她。“我必须打电话给办公室,告诉他们我无法到那儿……”
在机上时,伊莉莎白专心的在看一些杂志,只对我说了十个字的话。但是当我们抵达了在卡吉普西的工作坊地点时,她对聚集那里的参与者介绍我:“我的新公关。”
我打电话回家告诉太太我被“绑架”了,周五会回家。接下来的两天,我看着伊莉莎白工作。我看到人们的生命在我眼前改变。我看到旧伤治愈、老的议题解决、旧的怒气释放、旧的信念克服。
记得一天的某个时刻,过程室里坐得离我非常近的一位妇人“爆炸了”。(工作坊职员的用语,指某人开始哭泣不止,或以其他方式在当刻失去了控制。)只见伊莉莎白用头轻轻做了个姿势,打信号叫我去处理。
我温和的引导那哭泣的女人离开房间,陪她走到走廊那端布置好的一个别小角落。我以前从来没做过这种事,但伊莉莎白会给过每一个职员(她能常带着三或四位)非常明确的指导。她讲得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是:“别试着修好它。”只是倾听。如果你需要帮助,叫我来,但是倾听几乎总是够了。
她是对的。我现在能以一种专业的方式“在那儿”陪那个工作坊的参与者了。我能替她保住安全空间,给她一个地方,让他可以全发泄出来,释放她随身携带着而在那个更大房间里触发的东西。她大哭大叫,吼出她的愤怒,然后才安静的说话,再经历整个循环。我一辈子从没觉得自己如此有用途。
那天下午;我打电话给在马利兰的学校董事办公室。
“请接人事室。”我跟接线生说。而当我被接通到正确的部门时,我深深吸一口气。
“请问一个人能不能用电话辞职?”我问。
我替伊莉莎白工作时,是我一生最伟大的礼物。我很靠近的看到一位女性以圣人的方式工作,一小时复一小时,一周复一周,一月复一月。在演讲庭里,在工作坊的记房间里,并在垂危病人的床侧,我都站在她身边。我看见她和老年人及小朋友在一起。我看着她和害怕的人及勇敢的人、喜悦的人及悲伤的人、开放的人及封闭的人、激愤的人及温和的人在一起。
我看着一位大师。
我看着她治愈能施之于人类心灵上的最深伤痛。
我看,我听,而我非常努力的试着去学。
并且,是的,我真的开始了解你说得没错。
有上千种方法可以去释放别人心中的喜悦,而在你决定去这样做的那一刻,你就会知道如何做。
甚至在某人临终的床边也能做到。
谢谢你的规教悔及大师级的老师。
不客气,我的朋友。而现在,你知道如何喜悦的生活了吗?
伊莉莎白忠告我们所有的人要无条件的去爱,快快的宽恕,永远不为过去的痛苦后悔。“如果你保护山谷不受风吹雨打,”她说,“你就再也看不到它们侵蚀的美。
她也力权我们现在要充分的活着,偶尔停下来品尝品尝草莓,并且去做她所谓的“你未完结的事”所需做的任何事。因为生命可以无畏的活,而死亡也可以无憾的拥抱。“当你不怕死时,你便不怕活了。”并且,当然,她最大的信息是:“死亡并不存在。”
由一个人那里收到那些,是很多了。
伊莉莎白有很多东西可以给人。
那么,去吧,去实践这些真理,以及我透过其他来源带给你的那些,以使你能延展在你灵魂里的喜悦,在你心里感觉它,并且在你头脑里明白它。
神是全然喜悦的,而当你表达了神的这第一项态度时,你就会移转到你自己对神性的表达去。
14、你在我的后院玩得已够久了
我从没遇见过任何比泰莉·柯尔韦提克更充满喜悦的人。她总是带着一副眩目的笑容,一种绝对具感染性的奇妙、爆发性和令人解放的笑声,以及以她对人类善的了解而能深深触及人之无可比拟的能力。这个令人激动的女子在一九八○年初轰动了南加州。她以她那招牌的乐观性灵主义,将千百人带回到与他们自己及与神的一个快乐关系里。
我第一次听到泰莉,是当我住在艾丝康迪多,并在香提尼拉亚为库布勒罗斯博士做事时。在职业上我从没有这么的更有成就过,并且与一位有如此慈悲和灵性智慧的人密切的接触,将我又带回到我多年来不曾回去的地方:一个渴望与神有个人关系:在我的人生中以直接的经验认识神的地方。
自从我二十多岁以后,就没再上过教堂了。那时是我人生中的第二次,我几乎曾变成了一名神职人员。我十九岁离开米尔瓦基时第一次错失了当神父的机会。之后,当我继续了我多年的神学上的研究后,我又回到了想当神职的圣望。
为了寻找一位我不必害怕的神,当我年满二十之后,我便放弃了罗马天主教。我开始搜寻谈神学的书,并且去拜访安妮阿仑戴尔郡的一些教会和犹太教会堂,最后决定以安那波里斯的第一长老会堂为我要参加的地方。
我几乎立刻加入了他们的合唱团,而在一年内,我就变成了教会里的俗人读经者。当我星期日站在读经台读那周的圣经单节时,我再一次觉察到了我的儿时渴望:要将我的人生花在与神的密切关系中,教给全世界它的爱。
长老会在他们的信仰上似乎远不及天主教那样的建立在恐惧上(他们有较少的规则和仪式,因此陷阱也少得多),所以我对他们的神学也有较高的舒适度。事实上,我变得很舒适,我开始放一些真正的热情在我主日早晨的读经上,由于放得这么多,以致教众开始期盼我的轮值。这不但对我变得明显起来,并且教会的领导人也察觉到了。不久我便被牧师约谈,他是我所曾认得的最善良的人之一。
“告诉我,”温斯妻·萧牧师在和我交换了些客套话后,说,“你有没想过进入神职这一行?”
“我当然想过,”我回答,“当我十三岁时,我以为我一定会上神学院,然后变成一位神父,但那却没发生。”
“为什么没有?”
“我爸爸制止了我。他说我还不够大到去做这决定。”
“你觉得你现在够大了吗?”
在那一刻,不知为什么,我几乎忍不住要哭出来。
“我一直是够大的。”我悄声说,并努力恢复镇静。
“那么,你为什么仍然没呆在天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