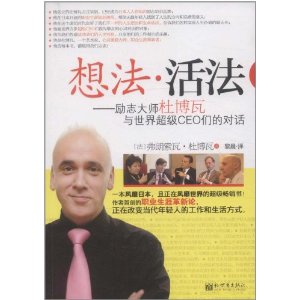与神对话-第11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彼此相爱,并且爱你自己。天哪(forGod’ssake),爱你自己吧!我是真的按字面的意思。爱你自己,为了神的缘故。
有时候非常难那样做。尤其是当我想到我过去是什么德性时。在我一生大部分时间里,我并非一个非常好的人。我花了三十年,我的二十多岁时、三十多岁和四十多岁做一个绝顶的
——别说了。别以那方式判你自己罪。你并非曾走过地球表面的最糟的人。你并非魔鬼再生。你曾是,并且是,一个人类,会犯错,试着找到回家的路。你很迷惑。你由于迷惑才做了你所做的。你迷失了。你曾迷失,而如今又被寻回(译注:著名圣歌AmazingGrace歌词。)
别再失去你自己,这回在你自己自怜的迷宫里,在你自己罪恶感的迷惘里。不如召唤你自己上前,以你对你是谁所曾抱持过的下一个最伟大憧憬之最恢宏版本的样子。
把你的故事说出来,但却不要只是你的故事。你的故事就像每个人的人生故事一样。它只是你以为你是谁而已。它并非你真正是谁。如果你用它来忆起你的真正是谁,你曾是很聪明的用了它。你将是完全如它本该被用的方式利用它。
所以,说出你的故事,并且让我们看见,因为其结果你还忆起了什么,以及还有什么样可让所有的人记得的东西。
嗯,也许我并非一个绝顶的——不论什么……但我显然不擅于使人们感觉安全。纵使在八零年代早期,当我以为我已学到了一点有关个人成长的事时,我却没应用我所学的。
我又结婚了,离开了泰莉柯尔韦提克牧师团,还离开嘈杂的圣地牙哥,到了华盛顿州的一个很小的镇克里契台,但在那生活也没处理得很好,大部分是因为与我相处根本不是很安全。我很自私,总是操纵我能操纵的每一刻和每一个,以便得到我所要的。
当我搬去奥立冈的波特兰想有个新的开始时,也没多大改变。我生活不但没改进,反而从复杂到更复杂。决定性的打击是我们的公寓发生了大火,几乎毁掉了我们拥有的每样东西。但我还没跌到最底呢。那时,我打散了我的婚姻,形成了其他的关系,又把它们打散。我像是个溺水的男人,挣扎着想保持浮着,而几乎将我四周的每个人都跟我一同拖下去。
到此时,我知道事情不可能更糟了。只不过它们真的变得更糟。一位八旬老翁开着一辆老爷车迎面撞上我的车,使我颈骨破裂。结果我戴着费城领圈(译注:车祸颈部受伤之人固定颈子用之白色软领圈。)超过一年,好几个月每天需做密集的物理治疗,更多的月份则是每隔一天,终于渐渐减为一周两次,然后,到最后,它结束了——但我人生中每件其他的事也一样结束。我失去了谋取生力量,失去了我最近的亲密关系,而有天走到外面,发现我的车子也被偷了。
真的个“祸不单行”的典型例子,我一辈子都会记得那一瞬间。仍然因每件其他出了毛病的事而摇摇欲坠,我在路上走来走去,徒然希望我只是忘了把车子停在哪里。然后,怀着绝对的放弃和深深的怨苦,我跌跪在人行道上,大声号哭泄愤,一个过路的女人惊讶的瞪我一眼,急忙窜到街的另一边去了。
两天后,我拿我最后的几块钱买了张巴士车票去南奥立冈,我的三个孩子跟他们的母亲住在那里,我问她可否给我一些帮助,或许让我在她房子里的一间空房间住几个礼拜,直到我能站起来,可以了解的,她拒绝了我——并赶我到外头。我告诉她我已走投无路,她才说:“你可以拿走账蓬和露营用具。”
那就是我结果怎么会在杰克森温泉的中央草坪上的原因。它刚好在奥立冈州艾许兰外围,营区空地的租金是每周二十五元,但我没有钱。我恳求营地管理员通融我几天去弄到一些钱,而他翻起白眼。公园里已挤满了过客,他最不需要的是再多一名,但他还是听了我的故事。他听到有关火、车祸、颈子断裂,车子被偷,以及不可置信的无穷尽的恶运,而我猜他动了怜悯之心。“好吧,”他说,“就给你几天,看看你能怎么解决。将你的账蓬架在那边吧!”
我四十五岁了,而我觉得我的人生已到了结尾。我由在广播界薪水很好的专业人员、报纸的编辑部主任、全国最大的学校体系的公共资讯官、伊莉莎白库布勒罗斯博士的个人助手,到在街上和公园里拣拾啤洒罐的汽水瓶去换五分钱的回收费。(二十个罐头换一块钱,一百个换一张五元券,而一周五张五元券让我留在了那营地。)
我在温泉区消磨了大半年,在那段期间,我对街头生活学到好几件事。当然,我并不是真的在街上,但是与之非常接近了。我发现,在户外、在街上、在桥下及在公园里,有一个密码,如果地球上其余的人也都遵循它,就会改变世界:彼此互相帮助。
如果你在“外面”待上不止几周之久,你会认识其他与你一同在那儿的人,他们也会认识你。但并没有任何涉及个人的事,请注意,没有人会问你你怎么来到了这儿。但如果他们看见你有麻烦,他们不会像这么多有屋子住的人那样置之不理,他们会停下来,问:“你还好吗?”如果你需要什么他们能帮上忙的,你就会得到。
在街上,我曾遇到过一些家伙,有的给了我他们的最后一双干被子,或当我看起来达不到我的“定额”时,他们会把他们平日拣罐子的分给所得。而如果某人得到了大利(从一位过路行人得到一张五元或十元),他就会带食物回来营地分享给每个人。
我记得那第一晚试着札营的事。当我到了营地,已经是黄昏时分了。我知道我得赶快做,但我实在并没什么札营的经验。风渐渐大了,看起来要下雨。
“将它绑在那树上,”无中生有来了个粗嘎的声音。“然后送一条绳子到后方的电线杆上。在那绳子上绑个记号,如此在半夜去厕所时,你才不会弄死你自己。”
开始下起了毛毛雨。突然,我的这位无名朋友不说废话地,和我一起将帐蓬架起。他的评论只限于“在这儿需要一根椿,”及“最好将帐蓬门帘拉起,不然你会睡在一个湖里”。
当我们弄完了(实际上他做了大半的工作),他将我的锤头丢在地上。“那应该撑得住了。”就自言自语的走开。
“嘿,谢谢你,”我在他身后叫道,“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不用介意。”他说,没有回头看。
我再没见过他。
我在公园里的生活变得非常简单。我最大的挑战(和我最大的欲望)是如何让自己保持温暖和干燥。我没有什么晋升的渴望、担心关于追到女孩“的事、为电话帐单烦躁,或自问我的余生要干什么。常常下雨,三月的寒风在吹,而我只不过试着保持温暖和干燥。
偶尔我会自忖,我如何能离开那儿,但大部分时间,我自忖我如何能留在那儿。一周二十五元是很大的一笔得无中生有的钱。当然,我有意找工作。但这是现在最迫切的事。这是有关今夜、明天和后天。而我正在等着一个受伤的颈子恢复,没车,没钱,食物很少,也没地方住。但是现在已春天,正要迈向夏天,这是值得庆幸的一面。
每一天我都去乱翻垃圾筒,希望找到一张报纸、有人没吃完的半个苹果,或午餐袋里小朋友不肯吃的一个三明治。报纸是为了在帐蓬下的额外纸垫,保持温暖,防止水渗进来,并且比凹凸不平的土地要柔软且平整些。不过,最重要的是,这是有关工作资讯的一个来源。每回我拿到一份报,就急急的掠过分类广告找工作。以我的颈伤,我无法做任何非常依靠劳力的事,而大半男人可立刻有的工作都是劳力的。不是需要日间劳工就是这个或那个工作团队的助手。搜录了两个月,我终于挖到了矿脉。
电台播报员/周末替手,必须有先前经验。
电××××。
我的心大大跳了一下。在奥立冈的麦德弗,有多少男人可能在广播上有经验,而不是已有工作的呢?我快步跑到电话亭,迅速翻阅感谢上帝它在那儿的电话簿黄页,找广播电台,丢下我可贵的一个二十五分钱,拨了那号码。要征人的节目部主任不在。“他回你电话好吗?”一个女性的声音说道。
“没问题,”我随意的说——以我最好的广播声音——提到我打电话来是与征求助的广告有关。“我会在这儿一直到下午四点。”我给了她公共电话的号码就挂上了,然后坐在靠近话亭的地方三个小时之久,等待那根本没来的回电。
第二天早上,我在垃圾筒里找到一本平装版的爱情小说,将它抓起来,走回到电话亭去。如果必要的话,我准备在这坐上一整天。在九点时我坐下来,打开我的书,告诉自己,如果在中午之前没有电话,我会再投资另一个两毛五,在午餐后打到电台去。电话铃在九点三十五分响了。
“抱歉我昨天没法回你电话。”节目部主任说。“我分不开身。有人转告我你来应征周末DJ的广告。你有经验吗?”
再次的,我用我较低沉的胸腔音说。“嗯,我不时的做过些播音工作,”我满不在乎的说,然后补充,“在过去二十年里。”当这对谈在发生之际,我祈祷着当我站在那儿说话时,不要有一部大的RV车辆隆隆开进公园。我不希望我必须解释,为什么一部大车正开过我的客厅。
“你能不能过来一下?”节目部主任提议道。“你没有什么播音的查核带?”
播音的查核带是消掉背景音乐后的DJ工作的录音带。我显然令他深感兴趣。
“没有,我所有的东西都留在波特兰了。”我撒了个小谎。“但我可以用你给我的任何稿子做一个‘现场阅读’,我想你会对我留下印象的。”“好吧,”他同意道,“你三点在右过来。我四点要上节目,所以别迟到。”
“知道了”
当我走出电话亭时,我真的高兴得跳了起来,并且大叫一声。两个家伙正好走过。“那么棒,啊?”其中这一慢吞吞的说。
“我想我找到了一个工作!”我得意洋洋的说。
他们真心的为我感到高兴。“做什么?”其中之一想知道。
“周末的DJ!我三点要去面谈。”
“你看来像那个德性?”
我没想到我的外表。我已几星期没理发了,但那也许可以过得了关。在美国,半数的DJ有马尾。但我必须对我的衣服动点手脚。在营地里有一间洗衣间,但我没钱买肥皂,将某些东西洗好、弄干,并准备好可以穿,再加上付往返麦德弗的公车费。
直到那时,我才惊觉我有多穷。如果没有某种奇迹的发生,我甚至无法做什么基本的动作,好比跑到城里去做一个迅速的工作面谈。当时当地,我经验到了在街上的浪人试图重新站起来,再度过一个正常生活所会碰到的阻碍。
他们两个看着我,好像他们完全知道我在想什么。
“你没钱,对不对?”其中一人半喷着鼻息,蔑视的问。
“也许有两块钱吧。”我猜,很可能估量过高。
“OK,来吧!小子。”
我跟着他们到了一圈帐蓬,那儿有些其他的男人札了营。“他有个去做工以离开这儿的机会,”他们向他们的朋友解释,并且低声说了一些我听不到的话。然后,转向我,两人中较老的那位大声的说,“你有像样的衣服可穿吗?”
“有,在我的行李袋里,但没有干净的,没有现成的。”
“把它带回到这儿来。”
到我回来的时候,有一位我在温泉附近看过的妇人也加入了那些男人。她住院在点缀着公园的几个小拖车之一里。“你去把这些东西洗好,弄干,我会帮你烫平,亲爱的。”她宣布。
一个男人走上前来,给了我一个小的棕色纸袋,里面硬币叮当作响。“伙计们全丢了些钱进去,一齐合作,”他解释道,“去洗你的衣服吧。”
五小时之后,我光光鲜鲜的出现在广播电台,看起来好像我是从我的上城公寓里走出来似的。(译注:Uptown上城通常是有钱的住宅区。)
我得到了那工作!
“我们能付你的是一个小时六块两毛五,八小时一天,一周做两天。”节目部主任说。“我很抱歉我无法付你更多。你条件太好了,所以如果你决定不做,我会了解的。”
一周一百元!我将赚到一周一百元!那就是一个月四百元——在我人生的那个时候,是笔财富!“不,不,它正是我现在在找的东西。”我假装不经意的说,“我喜欢我以前在广播电台的事业,但现在我转了业。我只是想找个方法让我保持熟悉。这对我会是很有趣的。”
我并没撒谎,它是真的有趣。幸存下去的趣味。我在营帐里又住了两个月,省下足够钱,花了三百元买了一辆六十三年的车。我感觉像个百万富翁。在营区我们那个团体里,我是唯一的有车阶级,并且是唯一有固定收入的人,而这两者我都随意的与所有其他人分享,从没忘记他们为我所做的事。
对下降的气温感到紧张,在十一月,我搬到公园里一间小小的只有一个房间的小木屋里,租金一周七十五元。将我的朋友们留在外面,我觉得很内疚——他们没人有那么多钱——所以在真的很冷或下场的夜晚,我会邀他们中一或二人与我分享我的房间。我轮流邀他们,所以每个人都有机会避开坏天气。
正当看起来我会永远做这兼差工作时,我收到了城里另一家广播电台来的一个意外提案,要我过去做他们下午交通尖峰时间的节目。他们是无意中收听到我的周末表演,而喜欢上他们所听到的——但麦德弗并非一个很大的广播市场,所以一开始他们只给我一个月九百无。不过,我又终于在做全职的工作,并且能够离开营地了。我在那儿住了九个月以上,那是我永不会忘怀的一段时间。
我祝福我拖着露营用具跋涉到那公园的那一天,因为它根本不是我生命的结束,却是开始。在那公园里我学到有关忠心、诚实、真实和信任,还有关于简朴、分享和存活。我学到永远不向失败投降,而接受此时此地真实的东西,并且感恩。
所以,我不止是从电影明星和名作家学习。也从与我为友的无家游民、从我每天见到的人,当我走过人生时接触到的人:邮差、小店店员,以及干洗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