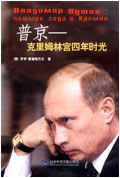克里姆林宫的红衣主教-第3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表明,两个孩子都是苏联青年的典型。瓦吐丁心想,一切的希望和梦想都随着他们
死去了,接着又丧失了妻子。
太糟糕了,米沙。我猜是你在对付德国人时花光了你们家的好运气,该他们三
个来替你还债了……太可悲了,一个贡献那么大的人,应当……
应当由此得到背叛祖国的理由?瓦吐丁抬起头,从办公室窗户望出去。他能看
见外边的广场,车辆围着菲力克斯·捷尔任斯基的塑像在开行,“钢铁的菲力克斯”,
“契卡”的创建人。在血统上是一个波兰人和犹太人,蓄一撮古怪的小胡子,有着
无情的智力,捷尔任斯基曾经击溃早期西方想攻入并颠覆苏联的企图。他背对着大
楼,爱说笑话的人说菲力克斯被判定要永远孤立在那里,象斯维也特拉娜被孤立起
来那样……
啊!菲力克斯,现在您能向我提出什么建议?瓦吐丁知道,答案太容易了。菲
力克斯会把米沙·费利托夫抓起来严刑拷问。只需有嫌疑的可能就足够了,谁知道
有多少男人和女人毫无理由就被弄得致残致死呢?现在的事情不一样了。现在,即
使克格勃也要守法了。你不能任意在街上抓人,滥施刑讯。瓦吐丁心想,那好多了。
克格勃是一个专业机构。现在他们必须更艰苦地工作,那样有利于造就有良好训练
的人员和更好地完成任务……他的电话铃响了。
“我是瓦吐丁上校。”
“上这儿来。十分钟内我们要去向主席作简要汇报。”电话挂上了。
克格勃总部是一座老建筑,兴建于世纪交替的前后,原先是俄国保险公司的总
公司。外墙是赭色花岗石,内部反映了修建时的年代,高高的天花板,特别宽大的
门。房子里那些长长的铺着地毯的走廊却没有很好的照明,因为谁也不应该有兴趣
去注意在那里定的人是什么长相。穿军服的人随处可见。这些军官是第三局的人,
该局是负责监视军事部门活动的。这房子与众不同的就是安静。在里面走路的人都
躺着脸,闭着嘴,生怕一不小心把这里数以百万计的机密泄漏了一件出去。
主席的办公室也面向广场,不过比瓦吐丁上校的办公室视野耍大一些。一个男
秘书从他的桌子边站起来,领着这两个人走过两个保安警卫(他们总是站在接待室
的角落里)。瓦吐丁走过敞开的门时深深吸了一口气。
尼古拉伊·格拉西莫夫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即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俄文
字首缩略。——译者〕主席已经四年了。他不是一个职业间谍,而是一个在苏共中
央工作了十五年的党务工作者,后来被派到克格勃第五局担任一个中级职务,其任
务是镇压国内不同政见者。由于工作得力,逐步提升,十年前终于被任命为第一副
主席。在那里他从行政工作中学习了国外情报业务,表现出色,他的天赋受到职业
外勤人员的尊重。然而他首先是一个党的工作者,他能当主席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他才五十三岁,对这个工作来说相当年轻,他看起来比岁数还更年轻。他那张年轻
的脸上从来没有留下失败的痕迹,他那自信的眼神还渴望进一步高升。对于一个已
经得到政治局和国防委员会席位的人来说,进一步提升意味着他在考虑竟争最高地
位: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由于掌握着党的“剑与盾”(这正是克格勃正式的格言),
他知道别的竟争者的一切情况。他的野心虽然从来没有表露过,但这个大楼里已经
在切切私语,许多年轻能干的克格勃官员每天都在努力把自己的命运系在这颗升起
的星星上。这是一个会迷人的人,瓦吐丁看出来了。即使现在他还是从桌子后面站
起来,向客人挥手示意,要他们坐在大橡木桌子对面的椅子上。瓦吐丁是一个能控
制思想感情的人,他很正直,不会被迷住。
格拉西莫夫拿起一个卷宗,“瓦吐丁上校,我读过了你正在进行中的调查报告。
工作得好极了。你能把到今天为止的情况说一说吗?”
“好的,主席同志。我们正在迫寻一个叫爱德华·华西里也维奇·阿尔土宁的
人。他是桑杜诺甫斯基澡堂的服务员。我们从对干洗店经理的审讯中得知,他是情
报交换链上的下一站。不幸的是,他在三十六小时之前失踪了,我们在这个周末一
定得抓住他。”
“我自己就去过那家澡堂。”格拉西莫夫带讽刺意味地说。瓦吐丁加上了他自
己的经历。
“我也去过,主席同志。我亲眼见过那年轻人。我们放进档案中的那张照片上
的人我认识。他曾在阿富汗的一个军械连里当下士。他的服役档案里说他反对在那
里使用某种武器——我们用来阻止老百姓帮助土匪的那一种。”瓦吐丁提到了那种
伪装成玩具、故意让孩子们去捡的炸弹,“连指导员写了一个报告,但第一次口头
警告就让他封住嘴了,他直到服役期满都没有再出其它事故。那份报告使他找不到
一个工厂的工作,只能从一个单位到另一个干些下贱活。同事都说他为人很普通,
就是不爱说话。当然,一个特务正是这样子的。他从来没有提到过他在阿富汗遇到
的‘麻烦’,连喝酒的时候也不说。他的住处和家庭成员、亲戚朋友都已在监视之
下。如果我们不能很快抓住他,我们就知道他是个特务。不过我们会抓住他的,我
要亲自同他谈话。”
格拉西莫夫深思地点头,“我看见你们在瓦涅也娃这个女人身上使用了新的审
讯技术。你觉得这个东西怎么样?”
“很有趣。在这个案子上它很管用,不过我要说,我对放她回街上去有疑虑。”
“那是我的决定,可能没人告诉你。”格拉西莫夫说得随随便便,“鉴于案情
微妙,加上医生的建议,我认为这个赌博目前值得一赌。我们不要让这个案子招惹
太多的注意,你同意吗?对她起诉的门还是开着的。”
啊,你能用它来反对她的父亲吗?她丢脸也是他的不光采,什么样的父亲愿意
看见他的独生孩子去西伯利亚劳改营呢?这不是有点敲诈勒索吗,主席同志?“案
子肯定是微妙的,还很可能更加微妙。”瓦吐丁回答得很小心。
“说下去。”
“那一次我看见阿尔土宁这家伙,他站在米哈伊尔·谢米扬诺维奇·费利托夫
上校旁边。”
“米沙·费利托夫,雅佐夫的助手?”
“就是他,主席同志。今天早上我看了他的档案。”
“结果呢?”这个问题出自瓦吐丁的头头之口。
“我挑不出什么问题。我不知他还卷进了彭可夫斯基案件……”瓦吐丁住嘴不
往下说,这回脸上露出某种表情。
“有事情使你为难,上校。”格拉西莫夫看出来了,“是什么事呢?”
“费利托夫卷入彭可夫斯基案件,是在他的第二个儿子和妻子死后不久。”瓦
吐丁停一会,耸耸肩,“一个古怪的巧合。”
“费利托夫不是告发他的第一个证人吗?”第二管理局的这个头头问道。他确
实曾在这案子的边缘上做过一些工作。
瓦吐丁点点头,“那是不错,不过那是发生在我们已经把这个间谍监视起来之
后。”他又停顿了一会儿,“正如我所说的,一个奇怪的巧合。恰在我们在追查一
个传递国防情报的可疑的交通员,我看见他站在一个国防部高级军官身旁,而这个
军官三十年前和类似的案件有牵连。从另一方面来说,费利托夫是首先告发彭可夫
斯基的人,他又是一个杰出的战争英雄……他在不幸的情况下失去了他的家人……”
他。第一次把这些想法都拧成了一股绳。
“难道有什么暗示可以怀疑费利托夫吗?”主席问道。
“没有。他的工作给人以深刻印象,无与伦比。费利托夫是前部长乌斯季诺夫
整个任内的唯一助理,从那以后一直在那个位置上,担任部长的私人视察长的工作。”
“我清楚。”格拉西莫夫说:“我这里有一份有雅佐夫签名的,要我们关于美
国战略防御计划工作的申请。我打电话给他时,这位部长说费利托夫上校和邦达连
科上校正在为政治局的一份全面报告汇集材料。你找回来的那张照片图象,上的代
号是‘明星’,对吗?”
“正是,主席同志。”
“瓦吐丁,我们现在有了三个巧合。”格拉西莫夫注意到了,“您的建议?”
那是很简单的,“我们应当将费利托夫置于监视之下。可能也得包括这个邦达
连科。”
“非常小心地,但也要最彻底地。”格拉西莫夫合上卷宗,“这是一次很好的
汇报,看来您的侦察才能时刻都很敏锐,上校。你要让我随时了解本案情况。在案
子结束前,我希望每星期和你见面三次,将军。”他向“二”局的头头说:“这个
人可以得到他所需要的一切支持。您可以征用本委员会任何部分的人力物力。您要
是遇到障碍,请告诉我。我们可以肯定,在国防部最高层里有一个漏洞。其次,这
个案件只有我和你们才能知情。没有人——我重复一遍,没有人将与闻此事。谁能
说美国人把他们的特务安排在什么地方?瓦吐丁,把本案交个水落石出,夏天你就
能得到将军的星徽。但是……”——他竖起一个指头——“我觉得你应该停止喝酒,
直到本案结束为止。我们需要你保持头脑的清醒。”
“是,主席同志。”
瓦吐丁和他的上司离开时,主席办公室外的走廊几乎已经空无一人,“对瓦涅
也娃怎么办?”上校低声问道。
“当然是为了她的父亲。总书记纳尔莫诺夫在下周将宣布他选入政治局。”将
军用一种中立的、不积极的声音回答。
在朝中有个克格勃的朋友没有什么坏处,瓦吐丁心想。格拉西莫夫可能采取某
种行动吗?
“记住他说的喝酒的事。”将军接着说:“听说您近来酗酒很厉害。这可是主
席和总书记之间达成一致的领域,可能没有人告诉你。”
“遵命,将军同志。”瓦吐丁答道。当然,这可能是唯一取得协议的领域吧。
象任何真正的俄国人一样,瓦吐丁把伏待加看成跟空气一样是生命的一部分。他想
起来,那天早上,正是这个坏毛病鼓励他去洗澡,才注意到那个事关紧要的巧合的
;但他抑制住没有说出这个反话来。几分钟后回到他的办公桌,瓦吐丁拿出一个本
子,开始筹划起对这两个苏军上校的监视方察来。
格雷戈里搭乘普通商用飞机回来,在堪萨斯城换飞机,停留了两小时、整个飞
行时间他都在睡觉。他不用取行李,径直走进候机室。他的未婚妻正在那里等他。
“华盛顿怎么样?”在通常欢迎归来的接吻之后,她问道。
“没有变化。他们开车让我到处转圈。我猜想他们以为搞科学的人是不睡觉的。”
他牵住她的手出门上车。
“那么,究竟出了什么事?”走出候机室后她问道。
“俄国人搞了一个大试验。”他住口环顾四周。这在技术上是违犯保密制度的
——可是坎蒂是小组里的人,不是吗?“他们在杜尚别用地面激光烧毁了一个卫星
;剩下来的象放在灶里烧过的一个塑料模型一样。”
“那太糟糕了。”朗博士说。
“的确。”格雷戈里博士同意,“但他们在光学上还有问题。热晕和不稳定。
肯定是他们没有象你这样制造反射镜的人。然而他们在激光那一头一定有些能人。”
“能到什么程度?”
“能到他们正在作的我们还没有想到的一些东西。”阿尔咕哝着。他们已走到
他的“雪菲”车,“你开吧,我还有点迷糊糊的。”
“我们会搞出来吗?”坎蒂打开车门时问道。
“早晚的事。”不管是不是未婚妻,他不能说得再多了。
坎蒂坐上车,伸手去开右边的车门。他一坐上椅子,系好安全带,就打开存物
箱,拿出一包鸳鸯蛋糕来。他总是有积蓄。蛋糕有点不新鲜了,但他不在乎。有时
候她怀疑,是不是她的外号〔朗原名坎黛丝( Candace),坎蒂( Candi)是爱称,
坎蒂的音又和甜食( Candy)相同,所以“坎蒂”含有外号的意思。——译者〕提
醒他吃甜点心,他才爱上了她的。
“新反射镜进行得怎么样?”鸳鸯蛋糕吞下一半之后,他问道。
“马尔夫有个新设想,我们正在做模型。他认为我们应当减薄镀层而不是加厚
它。我们下周就要试一试。”
“马尔夫这老家伙尽出新点子。”阿尔说。马尔夫·格林博士四十二岁了。
坎蒂笑了,“他的秘书也认为,他的鬼名堂是很多的。”
“他应该知道得很清楚,不该在工作中跟人乱搞。”格雷戈里一本正经地说,
然后好一会儿不说话。
“说得对,亲爱的。”她转脸看着他,两人都大笑起来,“你有多困?”
“我在飞机上睡过了。”
“那好。”
在伸手去搂抱她之前,格雷戈里团了鸳鸯蛋糕的包装纸,扔在地板上,那里已
有大约三十个纸团。他经常坐飞机来往,但坎蒂可有一付治时差病的灵丹妙药。
“还好吗,杰克?”格里尔海军上将问他。
“我担心,”瑞安承认,“我们看见试验完全是瞎猫碰死耗子,撞上的。时间
安排得凑巧。我们的侦察卫星都在光学地平线以下。本来不让我们看——这不用惊
奇,因为它是违犯反弹道导弹条约规定的。呃,也许不是。”杰克耸耸肩,“全在
你对条文怎么看,是‘严格的’解释还是‘宽松的’解释。我们要是放肆干这种违
法勾当,参议院就会闹开锅了。”
“你们看见的那个试验他们是不会喜欢的。”很少人知道“茶叶快船”到了什
么样的程度。这项计划是“黑色”的,比绝密还要绝密,“黑色”计划简直是不存
在的。
“也许是的。但是我们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