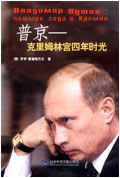克里姆林宫的红衣主教-第3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个他们自己的人员来作传递——没错,尽管作案技术高明,这是一个绝望的行动。
我想同时让弗利暴露。他们这一对儿把我们骗得那么久,一定自鸣得意。在行动中
抓住他们,将摧毁这种骄傲自大,对整个中央情报局也是一次重大的心理打击。”
“同意。”格拉西莫夫点点头,“这是你办的案子,上校。你要用多少时间都
可以。”两人都知道他是说不超过一个星期。
“谢谢您,主席同志。”瓦吐丁立即回到办公室,向各科的负责人布置任务。
扩音器非常灵敏。跟大多数睡觉的人一样,费利托夫辗转反侧好一阵子,入梦
时才安静下来,以后一盘又一盘的带子都是亚麻布的甥串声和刚刚可以听清的梦呓
声。最后一个新的声音出现了,裁耳机的那个人向他的同志作了一个手势。它听起
来象一面鼓满风的帆,那就是说,这个对象把被子扔下床了。
接着是咳嗽声。这老人肺有问题,他的医疗档案有记载。他特别容易得感冒和
呼吸道传染病。显然他是患上什么病了。接着他擤鼻梯。两个克格勃人员相视而笑,
因为那声音听起来象火车头的汽笛。
“跟着他,”负责电视摄像的人说:“向洗澡间去了。”接下去的一系列声音
是预料到的。有两架电视摄像机的强有力的镜头对准那公寓的两个窗户,特殊装置
使它们透过耀眼的晨光也能看得清楚。
“您知道,看人家上厕所已经够呛了,”一个技术人员说:“要是把咱们两人
之一的起床后的录像带拿给任何人看,一定会窘得要死。”
“一将功成万骨枯嘛。”那个上级军官冷冷地说。那是这些调查的一个问题。
你开始同对象太接近了,你必须常常提醒自己叛国者是多么可恶可恨。那个少校怀
疑:你是哪个地方出了毛病?象你这样一个有战功的人!他已经在怀疑这个案子究
竟怎么处理。一次公开审判?他们敢于把这么有名的一个战斗英雄拿去公诸于众吗?
他对自己说:那是一个政治问题。
房门开了又关了,说明费利托夫已经拿到了《红星报》,那是国防部的一个信
差每天送来的。他们听见了他那咖啡壶的汩汩响声,大伙儿一看——原来这个狗杂
种卖国贼每天早晨都吗这么好的咖啡呢!
现在完全可以看清他了,坐在厨房小桌子上,读着报纸。他们看见,他是一个
爱记笔记的人,在一个拍纸簿上记,或者在报纸上划符号。咖啡烧好了,他起来去
小电冰箱里取牛奶。在倒进杯子之前,先嗅一嗅,肯定它没有变坏。他把足够的奶
油抹在黑面包上。他们知道,这是他的日常早点。
“还是吃得跟士兵一样。”那摄像的人说道。
“他曾经是个好士兵,”另一个人员说:“你这个傻老头,你怎么能干这种事
情?”
之后,早餐很快就用完了,他们看着费利托夫走向洗澡间,在那里洗脸、刮胡
子。他又回来照镜子穿衣服。在电视屏幕上,他们看见他拿出一把刷子来刷靴子。
他们知道,他一向穿靴子,这在国防部军官中是不寻常的。然而他军服上别着的三
颗金星也不寻常。他站在衣柜镜子前端详自己。那张报纸放进了他的文件夹,费利
托夫走出房门。他们听到的最后声音是钥匙把公寓房门锁上。少校拿起电话说:
“对象出动了。今天早晨没有异常。跟踪小组就位。”
“很好。”瓦吐丁回答,挂上了电话。
一个摄像人员把机子对好,录下费利托夫在大楼外出现的情景。他接受了司机
的敬礼,钻进汽车,顺着衔开下去,消失了。他们都认为,这是一个完整无缺的、
平平常常的一天早晨,他们现在可以安静下来了。
新
西边的群山包裹在云雾中,天下起毛毛雨来。神箭手还没有动身。还有祷告文
要念,还有些人要去安慰。奥蒂兹出去找法国医生治脸去了,他的朋友在急速翻阅
他的文件。
这使他感到罪过,但神箭手告诉自己,他只不过是看看自己交给这个情报局官
员的东西。神箭手知道,奥蒂兹爱记笔记,又是一个地图迷。他在料想的地方找到
了地图,上面还夹着一些图解。他用手把它们描下来,迅速而准确,然后把它们放
回原处。
“你们两人这样古板。”碧·陶塞格大声笑着说。
“弄脏这种形象太可惜了。”阿尔回答,一个微笑掩盖着他对这客人的厌恶。
他完全不理解为什么坎蒂会喜欢这……不管她是她妈的什么玩意儿。格雷戈里不知
道为什么她在他脑子里引起了警觉感。那不是由于她不喜欢他——阿尔根本不在乎
这一点。他的家里人和他的未婚妻爱他,他的同事们尊敬他。那就够了。要是他不
合谁的意,说他不象一个陆军军官理想的样子,操他们的蛋。可是碧有点什么使—
—“好,咱们谈正事。”客人打趣地说:“华盛顿有人问我要多久……”
“这些人该去告诉那些官僚,你不能把事情看得象这样,一开一关,那么简单。”
坎蒂大声说道。
“六个星期,最多。”阿尔咧嘴一笑,“也可能更少些。”
“什么时候?”坎蒂问。
“快了。我们还没有机会做模拟试验,但觉得它是正确的。这是鲍勃的主意。
他快要搞完了,它使软件包大为精简,比我想做的还要好。它不必象我原来没想的
用那么多的AI。”
“哦?”用AI——人工智能——原来被认为是反射镜性能和目标分辨力的关键。
“是呀,我们把问题搞繁琐了,想用推理云代替直觉。我们不必告诉计算机对
每件事情该怎么想。我们把预先设定的选择编入程序,这样就可以使指令寄存减少
百分之二十。它证明,这样比让计算机从一个选择单中作出大部分判断要快些,而
且好些。”
“有反常情况怎么办呢?”陶塞格问。
“那正是全部问题所在。人工智能程序实际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碍事。我们想把
这东西弄得灵活应变,结果它什么事情也干不好。设想中的激光性能很好,使其能
够在人工智能程序能决定是否要瞄准之前更快地作出射击选择—工那为什么不试它
一下?如果它不符合要求,我们不管怎样也打它一下。”
“你那激光规格性能也改变了。”碧发表看法。
“噢,我不能谈那个。”
这个小小丑八怪又咧嘴一笑。陶塞格努力报以微笑。我知道某些你不知道的事!
是吗?光是看他一眼,她身上就觉得象有虫子在爬一样难受,可是更难受的却是坎
蒂看着他的那个样子,好象他是保罗·纽曼〔Paul Newman ,美国著名电影演员。
——译者〕什么似的!病黄色的脸,还长着粉刺,而她却爱这东西。碧觉得简直啼
笑皆非……
“恰恰是在行政那帮令人作呕的人不得不作超前计划的时候。”陶塞格说道。
“对不起,碧。你是知道保密原则的。”
“你怀疑我们怎么能干任何事情。”坎蒂摇摇她的头,“如果事情变得更糟,
我和阿尔就不能相互交谈,一边……”她对着爱人含蓄地笑道。
阿尔笑了,“我头疼。”
“碧,你信不信这家伙?”坎蒂问道。
陶塞格往后一仰,“我从来没信过。”
“你什么时候才让拉勃博士带你约会去?你知道他六个多月来一直为你神魂颠
倒。”
“我从他那儿唯一所指望的神魂颠倒,是一辆车的。天啊,那是个可怕的想法。”
她朝坎蒂一看,天衣无缝地掩盖’了她的感情。她也意识到她已弄出的程序方面的
情报也没用了,该诅咒的小丑八怪改变了程序。
“那是个什么东西。问题是,究竟是什么?”琼斯调了一下他的话筒,“驾驶
台,声纳,我们发现一目标,方位0 -9 -8 。标示这个目标为S -4 号。”
“你肯定那是目标?”年轻的军士问道。
“看见这个啦?”琼斯的手指划过屏幕。这台“瀑布”显示器上充满了杂乱的
环境噪声,“记住你在寻找非随机数据。这条线就不是随机的。”他敲进一条指令,
改变了整个显示屏。计算机开始处理一系列离散的频率带。不到一分钟,图象就清
晰了。至少琼斯先生是这样想的,年轻的声纳兵注意到。屏幕上的光点形状不规则,
向外成弓形,向下变窄,覆盖了五度方位角。这个“技术代表”盯着屏幕又看了几
秒钟,然后又开口说话。
“驾驶台,声纳,S -4 号目标为‘克里瓦克’级护卫舰,方位 0-9 -6 。
看样子他的转数约为十五节。”琼斯转向那小伙子。他还记得自己的第一次巡航。
这个十九岁的小伙子甚至连“海豚”微章还没得到呢,“看见啦?那是从他的汽轮
机发出的高频特征,十足的漏洞,你通常大老远就能听见,因为‘克里瓦克’没有
很好的隔声装置。”
曼寇索来到声纳舱,“达拉斯”是首批六八八艇,不象后续的潜艇,有控制舱
到声纳舱的直接通路。因而,你得往前走,绕过一个舱板上通向下面的一个洞。也
许大修会改装那地方。艇长对着屏幕舞动着他的咖啡缸子。
“‘克里瓦克’在哪儿?”
“就在这儿,方位仍然不变。我们周围水情很好。他大概挺老远的。”
艇长笑了。琼斯总是企图猜测距离。鬼事情是,在曼寇索有他在艇上当兵的两
年里,他是对的时候多,错的时候少。在后面的控制舱里,火控跟踪小组在绘制目
标相对“达拉斯”已知航迹的位置,来确定苏联护卫舰的距离和航向。
水面上没有多少活动。另外三个绘出的声纳目标都是单螺桨的商船。虽然今天
的天气还不错,波罗的海——依曼寇索的思维方式,一个大号的湖——在冬天绝大
部分时候都很糟。情报指明大部分对手舰只都泊系在港修理。那是好消息。更好的
是,没有太多的冰。一个寒冷十足的季节能把东西都冻僵,艇长心想,那会给他们
的任务作梗。
迄今为止,只有他们的另一位客人,克拉克才知道那个任务的内容。
“艇长,我们得到S -4 号的位置,”一个尉官从控制舱里叫出来。
琼斯卷起一片纸,递给了曼寇索。
“讲吧。”
“距离三万六千,航向大约 2-9 -0 。”
曼寇索打开条子,大笑,“琼斯,你他妈还是个巫师!”他把它递回去,然后
往回去改变潜艇的航向,以避免“克里瓦克”。
琼斯身旁的声纳兵抓过那张条子,大声读了出来,“你怎么知道?你不应该能
够作到这步。”
“熟能生巧,小伙子,”琼斯用他装得最象W ·C ·菲尔兹的声调回答说。他
注意到潜艇的航向变了。这不象是他记忆中的曼寇索。那时节,艇长会迫近目标,
利用潜望镜拍照,执行几套鱼雷方案,总的说来,象在实战中对真正目标那样来对
待苏联舰只。而这一次,他们在增大到俄国护卫舰的距离,悄悄的溜走了。琼斯认
为曼寇索不会变得那么多,开始盘算起这项新任务究竟是怎么回事来。
他没怎么见到克拉克先生。他在后面轮机舱里度过了不少时光,那儿有一个艇
上保健中心——塞在两台机床之间的跑步机。艇上官兵已在窃窃私语,说他不怎么
说话。他只是笑笑,点点头,就自顾干他的。有一个军士长注意到了克拉克前臂上
的纹身图案,轻声传送着一些关于那个红色海豹意义的事情,具体地说,它代表的
是真格的SEAL〔英语海豹之意;而此缩语表示“海-陆-空”美国海军特种部队。
——译者〕,“达拉斯”上从来没上过那样的一个人,然而其他的艇有过,这些故
事,讲的时候除了偶尔几声“不是吹牛吧!”之外都是轻声细语,传遍了整个潜艇
界的人,但是没有外传。如果潜艇兵会做什么事情的话,保守秘密可得算上。
琼斯站起身,向后走去。他想这一天上的课够多了,而他以文职技术代表的身
分可以任意闲逛。他注意到“达拉斯”自己也是逍遥自在,向东以九节速度开行,
度着她的美妙时光。往海图上一瞧告诉他现在他们所处的地点,而领航员在上敲打
铅笔的神气说明他们还要走多远。琼斯往下去找一个“可口可乐”时开始认真思考
起来。他终究是回来参与一项紧张十足的行动。
“是我,总统先生?”穆尔法官拿起电话,带着他自己的紧张神色。决定的时
刻?
“我们那天在这里谈的那件事……”
“是的,阁下。”穆尔看着他的电话。除了他手里握着的手机之外,这套“保
密”电话系统是一个三呎见方的东西,巧妙地藏在他的办公桌内。它接收文字,把
它们分成数字信息单位,把它们搅乱得无法识别,再把它们送到另一个类似的盒子
里,这才把它们复原。这过程的一个有趣的间接作用是它有助于极清晰的谈话,因
为这套加码系统消除了电话线上所有的随机噪音。
“你可以执行。我们不能——噢,我昨晚决定我们不能就丢下他不管。”这肯
定是他早晨第一个电话,情感色彩也在其中。穆尔思付着他是否因这个不知名、不
知面的代理人的生命而失眠了。大概是的,总统是那样的人。穆尔了解;他也是那
种一旦作出决定就坚持到底的人。佩尔特整天都会试图改变这决定,然而总统早上
八点就通知这项决定,必然会坚持不变。
“谢谢您,总统先生。我将让事情动起来。”穆尔通知鲍勃·里塔,他两分钟
后就进了法官的办公室。
“红衣主教转移行动是‘执行’!”
“真使我为投了这人一票感到高兴,”里塔双手一拍,说道:“十天之后我们
就能把他送到一座很好的‘安全房’〔这指情报机构用来庇护、集结特工人员的特
加保安的地方。——译者〕里。我主耶稣,投诚盘问要花好几年!”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