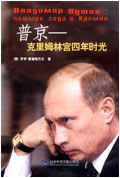克里姆林宫的红衣主教-第5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们前一天听到过两艘潜艇的声音。
“咖啡,长官?”餐室服务员问道。他点头作答,服务员便端出一壶和几个杯
子。
“你肯定这就够近了?”曼寇索问克拉克。
“是咧,我能进去再出来。”
“那不会有多好玩的,”艇长说道。
克拉克发出傻笑,“那就是为什么他们给我这么多钱。我……”
谈话停了片刻。当潜艇沉落到底时,它的外壳嘎吱作响,并且艇身略取倾侧。
曼寇索看着他杯中的咖啡,估计倾侧角大约六、七度。潜艇兵的男子气概使得他不
能表露出任何反应,但他从来没有干过这个,至少没有同“达拉斯”一起干。在美
国海军里有几艘潜艇是专为这种任务而设计的。知情者只要看一眼就能从几个外壳
配接装置的安排上认出它们,但“达拉斯”不是其中之一。
“我想知道要用多长时间?”曼寇紊向舱顶间道。
“也许根本不会发生,”克拉克说道:“几乎有一半不会发生。我不得不象这
样坐等最长的那次是……十二天,我想是的。好象是极长极长一段时间。那次就没
进行。”
“你能说多少次吗?”拉米乌斯问
“遗憾,长官。”克拉克摇摇头。
拉米乌斯若有所思地说:“你知道吗,我小的时候,在这儿钓鱼——就在这儿
钓过好多次。我们从来不知道你们美国人也到这儿来钓鱼。”
“这是个古怪的世界,”克拉克附合道:“鱼钓得如何?”
“在夏天时,非常好。老萨沙用他的船带我出海。这就是我了解大海的地方,
我学会成为一个海员的地方。”
“本地巡逻情况如何?”曼寇索问,把每人带回到正事上来。
“会处于一种低级战备状态。你们有外交官在莫斯科,所以战争的可能性是微
小的。在水面负责巡逻舰只的主要是克格勃的人。他们防范走私者——和特务。”
他指着克拉克,“对付潜艇不怎么样,但我离开时,这儿正在发生变化。那时他们
在增加北方舰队的反潜战训练,而且,我听说,波罗的海舰队也在。但这是探测潜
艇的坏地点。从河流灌进大量淡水,以及头上的冰层——都造成了困难的声纳条件。”
听起来真舒心,曼寇索心想。他的舰艇正处于一种极高的战备状态。声纳设备
全员配备,并将无限期保持。他在两分钟内就能使“达拉斯”动起来,他想那应该
是足够了。
格拉西莫夫也在想。他独自一人在他的办公室里。他是一个比大多数俄国人还
要能控制自己感情的人,既使办公室里没有别人注意,他的脸也不会显示出任何异
常的表情。在大多数人身上那就是卓越不凡了,因为几乎没有人能客观地细想他们
自己的毁灭。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象细查他官职的任何一方面那样透彻地、不带情感地评估
他的境况。他很好地利用了“红十月”事件,首先使戈尔什科夫作假,然后除掉了
他;他还利用这一事件来加强自己在第三管理局分支的地位。军方那时已经开始经
管自己的内务安全——然而格拉西莫夫抓住他那份来自代理人卡休斯的报告,说服
政治局克格勃单独就能保证苏联军队的忠诚及安全。这给他招来了怨恨。他报告说,
再次通过卡休斯,“红十月”已被毁掉。卡休斯告诉克格勃说瑞安有犯罪嫌疑,并
且——
并且我们——我!——走进这个陷阱。
他怎么能向政治局解释这种事?他最好的间谍之一被人搞成了双重的——但何
时?他们会问那事,而他却不知答案。所以从卡休斯那里收到的所有情报都会成为
疑点,他在未知的情况下被双重化这一点把全部都搞坏了。而那也就毁掉了他自夸
的对西方政治思想的洞察力。
他曾错误地报告说潜艇没有叛逃,而且没有发现这个失误。美国人发了一笔情
报横财,但克格勃却不知情。格鲁乌也不知道,不过那不是什么安慰。
他又报告说美国人在他们的军备谈判策略上作了一个重大的变动,然而那也是
错误的。
三项同时泄露出来他能幸存吗?格拉西莫夫自问。
大概不能。
在另一个时代,他面临的会是死路一条,那倒会使决定更加容易。无人选择死
路,至少一个健全的人不会,而格拉西莫夫在每一件他做的事情中都是冷静稳健的。
但那种事现在不再发生。他会落得贬到某某地方作部级以下工作的下场,来回捣腾
各种文件。他的克格勃关系人物在如有权进象样的食品商场之类无意义的恩惠之外
对他格毫无用处。人们会看着他在大街上步行——不再害怕盯着他的脸看他,不再
恐惧他的权力,他们会从背后指着他笑。他办公室里的人会逐渐抛开对他的敬重,
反唇相讥,一旦他们知道他的权力实实在在消失了,甚至会冲着他大吼。不,他对
自己说,我不愿忍受那样的事。
那么,叛逃?从一个世界上最有权威的人之一变成一个用他知道的事来换取金
钱和舒适生活的金钱奴隶、乞丐?格拉西莫夫承认他的生活从物质上来说会变得更
舒适这一事实——但失掉了他的权力!
毕竟,那是问题的症结。他是走还是留,成为平平凡凡的一个人……那会象死
亡一样,难道不是?
唉,你现在怎么办?
他必须改变自己的状况,必须改变“游戏的规则”,必须作一件如此戏剧性的
……但必须什么呢?
选择是在身败名裂和举家叛逃之间吗?失去他拼命努力的一切——在抬头可见
他的目标的时候——并且面临这样的选择?
苏联不是一个赌博者的国度。它的国家战略总是更多地反映了俄国对象棋的全
国性嗜好,一系列谨慎的、预先策划的招术,绝不冒太大的风险,总是通过在任何
可能的地点寻求渐进的小优势来保护它的阵脚。政治局几乎总是那样行动的。政治
局本身主要也是由类似的人组成。一半以上都是机关工作人员;他们说了恰当的话,
完成了必要的定额,捞了他们所能捞的那一把,他们通过一种冷漠无情来赢得了他
们的升迁,其完美的程度他们可以在克里姆林宫中的桌子旁显示出来。然而,那些
人的功能是提供一种节制作用来影响那些意欲统治的人,而这些人却是赌博者。纳
尔莫诺夫是一个赌博者。格拉西莫夫也是。他玩了他自己的游戏,把他自己同阿列
克山德罗夫联营,以建立他的意识形态支持集团,并且讹诈瓦涅也夫和雅佐夫去背
叛他们的主子。
而且这场游戏太精采了,不能这么轻易放弃。他必须再度改变规则,其实这场
游戏没有任何规则——除了一个:赢。
他要是赢了——奇耻大辱不会有什么关系,不是吗?
格拉西莫夫从他的衣袋里掏出那把钥匙,第一次在他的。办公桌灯光中查看它。
看起来是够平常的了。而一旦按设计的方式来使用,它就会使死亡成为可能——五
千万人?一亿?更多?在潜艇上和在陆基火箭团的第三管理局人员掌握着那个权力
——zampolit,政治军官独掌启动弹头的权力,如不这样,火箭只是放焰火的玩意
儿。在适当的时刻,以适当的方式转动这把钥匙,他知道,火箭就被转化成为人类
智慧迄今所能设计出来的最可怕的死亡器具。一旦发射,任何东西都不能阻止它们
……
但这条规则也将被改变,不是吗?
作为一个能够作到这点的人有多大价值?
“啊,”格拉西莫夫笑了。那比其他规则全部加在一起还要有价值,而且他记
起美国人也违反了一条规则,在“莫斯科人”铁路货场杀死了他们的交通员。他拿
起电话,打到一个通信军官那里。这一次,经度线可对他有利。
陶塞格博士看见信号时吃了一惊。有关“安”的一件事就是她从不更改她的常
规行动。尽管她冲动地造访过她的接头人,朝购物中心去是她正常的星期六惯例。
她把她的达特桑停在相当靠外的地方,以防哪个冒失鬼开着辆“雪菲·马利坡”跟
她的车来个门撞门。在进去的路上,她看见安的“沃尔沃”,驾驶座那边的遮阳板
朝下。陶塞格看看表,加快步伐朝入口走去。一进去,她就往左转。
佩吉·詹宁斯今天单枪匹马。为了尽快按华盛顿的要求——把这活干完,他们
的人马分得太散了,但那并不是件什么新闻,不是吗?监视场景又好又不好。跟踪
她的对象到购物中心相当容易,但一进去,正经盯住一个对象几乎就他妈的不可能,
除非你有实实在在的一队专员们在行动,她在陶塞格后仅一分钟就赶到门口,已经
知道她失掉了她。嗨,这只是对她的初步观察。例行公事,詹宁斯开门时告诉自己。
詹宁斯上下看看购物中心,没能看见她的监视对象。她皱了一下眉头,就开始
悠闲地从一个店转到另一个,一边盯着橱窗,一边想着陶塞格是不是看电影去了。
“你好,安!”
“碧!”彼霞里娜在“夏娃之叶”里叫道:“你还好吗?”
“事情很多,”陶塞格答复道:“你穿那件看起来太美了。”
“她很容易合身,”店主发表看法。
“比我容易,”陶塞格阴郁地表示同意。她从最近那排架子上取下一套衣服,
朝一面镜子走去。剪裁得很正规,正合她目前的情绪,“我可以试试这套吗?”
“当然,”店主立即说道。那是价值三百美元的套服。
“要帮一把?”“安”问道。
“当然——你可以跟我讲讲你在忙什么。”两个人向后面的试衣室走去。
在隔间里,两个女人聊开了,谈论着各种日常琐事,这在男人和女人之间没什
么差别。彼霞里娜递过一张纸条,陶塞格拿过来看了。后者的对话结巴了一下才点
头同意。她的脸色从震惊变成接受,然后又变成了某种彼霞里娜完全不喜欢的表情
——但克格勃不是付她钱才喜欢她的工作的。
她们出来时,店主看到衣服挺合身的。陶塞格付帐用的是大多数人的方式,即
用信用卡。安招招手离去了,在她出购物中心的路上,拐弯走过那家枪店。
几分钟后,詹宁斯看到她的对象走出成衣店,提着一个透明的塑料服装袋。哦,
是那么回事,她心中告诉自己。那天晚上不论什么都使她心烦,她去买东西来改善
心情,而且又买了一套套服。詹宁斯又跟了她一个小时才中断了监视。没有发现情
况。
“他真是个冷静的家伙,”瑞安对坎迪拉说:“我不指望他跳进我的坏抱,感
谢我的提议,但我指望某种反应!”
“嘿,如果他咬饵,他会轻而易举地传话给你。”
“是咧。”
21、流氓的花招
神箭手试图说服自己天气不是任何人的盟友,但事与愿违。天空晴朗,东北冷
风从西伯利亚寒流中心刮来。他却想要浓云密布。他们现在只能在黑暗中行动。这
使得进程缓慢,而他们在苏联境内呆得越长,越容易被人发现,一旦被人发现……
没什么必要去推测其结果。他只需探出头来就可看到沿丹格拉公路开行的装甲
车。附近至少驻扎有—个营,也有可能是一整团摩托步兵部队,不停地沿公路铁路
巡逻。他的部队按圣战者的标准说来很强大,但在俄国的土地上对付一团俄国人,
只有安拉本人才能拯救他们。也许他也不能?神箭手想了想,随之把自己没说出来
的亵渎神明的想法鞭挞了一顿。
他的儿子不会太远了,可能离得比他们刚才完成的路程还近——但在哪儿?一
个他永远找不到的地方。神箭手对此毫无疑问。他老早就失去了希望。他的儿子会
受异邦异教的俄国方式教养,他只能祈祷安拉能及时挽救他的儿子,否则将不可救
药。偷孩子,达真是最凶残的罪恶。剥夺他们的父母和信仰……行了,不必老想这
事了。
他的手下人每人都有憎恨俄国人的原因。家庭被杀或四处逃散,房屋被炸。他
的下属不知这都是现代战争中的常事。他们“未开化”,觉得打仗只是武士的事。
他们的队长知道这想法在他们出生之前早已不成事实。他不明白“文明”国家
为何改变了这一明智的规则,但他只需知道这事实就够了。这使他意识到自己的命
运不会是象他选择的那样。神能手不知人们是否能真正选择自己的命运,或都被掌
握在掌书握枪之手之外的巨手之中。但那又是烦杂而无用的想法,因为对神箭手及
他的下属来说,这个世界已经精练成为数极少的简单真理及深沉的憎恶感。也许这
总有—天会改变,但现在对圣战者来说,世界仅局限于他们所见所感那部分。寻根
问底将使人失去洞察力,那就意味着死亡。他的部下唯一的崇高思想是信仰,此时
此地这就足够了。
车队的最后一辆车在公路拐弯处捎失了。神箭手摇摇头。现在他已经想够了。
他刚看到的俄国人都在他们履带式BMP 型步兵战车里,在车内能拼命打开取暖
器保
暖,在车内他们却不能很好地观察外面。这事关紧要。他探头看见他的部下;
俄国军装把他们伪装得很好,他们藏在岩石后,卧在低洼处,成对成双,其中一个
可以睡觉,而另一个象他们的队长一样,注视着一切,严守岗位。
神箭手向上看到太阳低垂,很快就会滑下山脊,他的部下即可继续向北行军。
他看见一架飞机从高空飞过,转弯时阳光照在铝蒙皮上,闪闪发光。
邦达连科上校靠窗而坐,向下注视着险恶的山岭。他记得他在阿富汗执行任务
那段短暂的时间,那延绵不断,让人走断腿的群山,即使一人转了一圈,也似乎总
是在上坡。邦达连科摇摇头。至少那一切都过去了。他的任务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