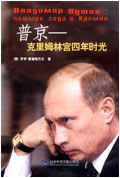克里姆林宫的红衣主教-第6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子,而不是他的眼睛。不是自我怀疑的时候。
他的窗外还是黑的。莫斯科的照明跟一个美国城市不一样。也许是在这时刻几
乎毫无车辆。华盛顿总有人来回移动。总有那种潜意识的确定性,即某个地方,人
们没有睡觉而在从事他们的事务,不管是什么样的事。这个概念在这儿不能翻译过
来。就象一种语言的文字从来不能精确地翻译过来,从来不能恰恰与另一语言的文
字一一对应,因此莫斯科对瑞安来说勉勉强强同他去过的其他重要城市差不多,而
它的差别益发显出异邦陌生的意味。在这儿人们不去从事他们的工作。多数的情况
是他们从事着别人分配的工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很快就会成为一个发布命令的
人,向一个已经忘记怎样接受命令的人发命令。
新
早晨缓慢地来到莫斯科。有轨电车的交通声响和卡车柴油机更深沉的轰随声被
积雪减弱些,瑞安的窗子不朝适当的方向,收不住黎明的第一道光。曾是灰色的天
空开始获取颜色,正象一个小孩在玩彩色电视上的控制钮。杰克喝完他的第三杯咖
啡,在七点三十分时放下他在读的那本书。在这样的场合下,把握时机就是一切,
坎迪拉告诉他。他最后一次使用了洗手间,才穿衣准备他的早晨散步。
街旁人行道上的周日晚降下的暴风雪已经清扫干净,虽然在路坎上还有一堆一
堆的雪。瑞安对保卫人员点着头,澳大利亚人,美国人,以及俄国人,这才上契可
夫街往北走。刺人的北风使他的眼湿润起来,他稍微调整了一下围着脖子的围巾,
向沃斯塔尼亚广场走去。这是莫斯科的使馆区。前一天早晨他在广场远端往右拐弯,
看到五六个随机混合着的使团,但这天早晨他在库德林斯基胡同上往左转——俄国
人至少有九种说“街”的办法,不过这项细微差别杰克体会不到——然后往右,然
后再往左上巴里卡德纳亚。
把一条街和一家电影院都叫“巴里卡德”〔原文BARRICADE 意即街垒、路障。
——译者〕似乎很奇怪。用西里尔字母〔西里尔字母是现代俄语等语言字母的本源。
——译者〕拼写看起来更奇怪。能认出B 来,虽然西里尔“B ”实际上是个V ,而
这个宁中的R 看起来是罗马字母的P 〔罗马字母是英语及其他西方语言所用的字母。
——译者〕。杰克改变了一点他的路线,随着他接近目的,他尽可能地靠着建筑物
走着。正如所料,一道门打开,他转了进去。他再一次被人全身拍遍。保安人员在
他大衣口袋里发现了那个密封的信封,但没有把它启开,使瑞安松了口气。
“来。”跟他头一次说的一模一样,杰克注意到。也许他词汇量有限。
格拉西莫夫坐在一个靠走道的座位上,在杰克走下斜坡去见这人时,他自信地
背朝着瑞安。
“早上好,”他冲着那人的后脑勺说。
“你觉得我们的天气怎样?”格拉西莫夫问道,招手示意那个保安人员离去。
他站起来,领着杰克向下朝银幕走去。
“我长大的地方没这么冷。”
“你应当戴顶帽子。大多数美国人宁愿不戴,不过在这儿它是必须品。”
“新墨西哥州也冷了。”瑞安说道。
“有人告诉我。你认为我将无所事事?”克格勃主席问道。他问得毫无感情色
彩,象一个教师对着一个顽真不化的学生。瑞安决定让他享受一阵儿这种感觉。
“我应当同你谈判格雷戈里少校的自由吗?”杰克中立地问道——或者说企图
那样。超量的早咖啡使他的感情色彩变得浓郁。
“如你愿意。”格拉西莫夫答复道。
“我想你会对这个很感兴趣。”杰克递过那个信封。
克格勃主席把它启开,取出照片。他翻看那三幅照片时没有表现出任何反应,
但当他转过来看着瑞安时,他的眼使得晨风变得象春天的呼吸一般。
“一个活着,”杰克报道说:“他负伤了,但他会康复。我没有他的照片。有
人在那头搞糟了。我们救回了格雷戈里,安然无羌。”
“我明白了。”
“你也应该明白你的选择现在就是我们打算的那些。我需要知道你做哪一个选
择。”
“这很明显,不是吗?”
“研究你们的国家时我学到的事情之一就是没有任何事情是我们所喜欢的那样
显然。”那引出了几乎是笑的一种什么表情来。
“我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
“相当好。”比你应受的要他妈好得多。
“我的家庭?”
“他们也一样。”
“你建议怎样把我们三人弄出去?”
“我相信你妻子是拉脱维亚人,并且她常常回家探亲。让他们星期五晚在那儿,”
瑞安说道,接着讲了一些细节。
“究竟是什么……”
“你不需要那个信息,格拉西莫夫先生。”
“瑞安,你不能……”
“不,长官,我能,”杰克截断他的话,不知为什么他叫了声“长官”。
“那我呢?”主席问道。瑞安告诉他所必须他的事情。格拉西莫夫表示同意,
“我有一个问题。”
“什么?”
“你们怎么骗了普拉托诺夫?他是一个很精明的人。”
“实际上跟证券交易委员全有点小纠纷,不过那不是重要的部分。”瑞安准备
离去,“没有你我们也不能干成这事。我们不得不推出一台好戏,一种你不能假装
的真戏。特伦特众议员六个月前在这儿,他遇到了一个叫瓦列里的伙计。他们成了
很好的朋友。他后来发现你以‘反社会活动’的罪名判了他五年。不管怎样,他要
复仇。我们请求他的帮助,而他却抢着这个机会。所以我想你可以说我们用了你自
己的偏见来反击你。”
“你要我们拿这些人怎么办,瑞安?”主席追问道:“你……”
“我不制定法律,格拉西莫夫先生。”瑞安走了出去。真是妙极了,他在返回
使馆大院的路上想到,风向变得吹着他的背。
“早上好,总书记同志。”
“你不必这么正式,伊里亚·阿尔卡季也维奇。有比你还高的政治局成员也没
有表决权,并且我们同事太……长了。有什么为难的事?”纳尔莫诺夫谨慎地问道。
他同事眼中的悲痛是很明显的。他们的日程是谈论冬小麦情况,但是
“安德烈·伊里奇,我不知道怎么开头。”说这些话时他几乎噎住了,眼泪开
始从他的眼睛淌下,“是我的女儿……”他抽抽泣泣继续讲了十分钟。
“然后呢?”纳尔莫诺夫问道,这时他好象完全停下不讲了——不过显而易见,
一定有更多的话。确实有。
“那么是阿列克山镕罗夫和格拉西莫夫。”纳尔莫诺夫在椅子里向后仰,注视
着墙上,“你来跟我讲这情况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我的朋友。”
“我不能让他们——即使这意味我的前途,安德烈,我不能让他们现在阻止你。
你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我们——你有太多的事情要去改变。我必须离去,我知道这
点。但你必须留下,安德烈。如果我们要完成什么事业,人民需要你在这儿。”
值得注意的是他说的是人民而不是党,纳尔莫诺夫想到。时代真是在变。不。
他摇摇头。不是这么回事,现在还不是。所有他完成的是创造出一种气氛,在这种
气氛中时代才也许有了变迁的可能性。瓦涅也夫是一个清楚问题更多的是过程而不
是目标的人。每一个政治局成员都知道——知道多年了——事情需要变化。正是变
化的方式没人能达成一致。这就象把船转向产个新的航线,他想,但是知道如果你
转向,舵可能会破碎。在同样的航程上继续航行会让船破浪直闯……什么?苏维
埃联盟正走向何处去?他们连那也不知道。但是改变航向意味着风险,如果舵一旦
破裂——如果党失去它的支配地位——那么就只会是混乱。那是一种理智的人绝不
会希望面对的选择,但也是一种理智的人不能否认其必要性的选择。
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的国家在做什么,纳尔莫诺夫自己心中想到。在过去至少
八年中,关于经济工作的所有数字都这样那样地掺了假,每个数字本身影响着下一
个数字,直到国家计委官僚机构编制的经济预测数字跟一份列着斯大林美德的单子
一样是凭空杜撰的。他指挥的船进入四面笼罩的谎言之雾越来越深,这雾是由那些
会被真理毁灭生涯的机关工作人员制造的。他是这样在政治局每周一次的会议上谈
论这个问题的。四十年玫瑰色的目标和预测仅仅在毫无意义的航海图上标绘出一条
航线来。就连政治局本身也不了解苏维埃联盟的国情——这是西方几乎不能想象的
事傀
另一种选择?那是一个痛处,不是吗?在他思绪灰暗时,纳尔莫诺夫不知道他
或其他任何人能否真正改变事物。他一生政治生涯的目标曾是获取他现已拥有的权
力。而只有现在他才完全明白那种权力是多么地受约束。在他向上攀登的事业阶梯
的每一级,他都注意到必须改变的事情,从来没有完全理会那将是多么困难。他所
施用的权力跟斯大林的不同。他较近的前辈们保证了这一点。现在苏联已不大是一
艘需要导引的船,而是一个巨大的官僚弹簧,吸收并消耗能量,只随它本身低效率
的频率振动。除非这点有所改变……西方正急速飞驰,驶进一个新的工业时代,而
苏联显然不能喂饱自己。中国正在吸收日本经济的经验,在两代人之内可能成为世
界第三号经济强国:十亿人,具有强大有力的经济,紧靠我们的边境,渴望土地,
并又带着对所有俄国人的种族憎恨,能使得希特勒的法西斯军团看起来象一群足球
痞子。那是一种对他的国家的战略威胁,使美国和北约的核武器相比之下毫无意义
一。而党的官僚机构还不明白必须改变,不然就要冒险成为自己的掘墓人!
什么人必须试图去改造,而这个人就是我。
但是为了去试,他首先必须生存,生存足够长的时间来传播他对国家目标的设
想,先对党,然后对人民——也许应该倒过来?两者都不易。党是自行其道,抵抗
变化,而人民,老百姓,再也不对党和它的领导人对他们所说的东西给予片刻的思
索。那是有趣的部分。西方——他的国家的敌人——比他的同胞们把他看得还高。
那这意味着什么?他自问道,如果他们是敌人,他们的好感意味着我是在正确
的道路上前进吗——对谁正确?纳尔莫诺夫极想知道美国总统是否跟他一样孤独。
但在面对那不可能的任务前,他还有自我生存的日常策略问题。甚至现在,甚至在
一个可信赖的同事旁。纳尔莫诺夫叹了口气。这是很俄国式的声音。
“那么,伊里亚,你怎么办?”他问一个不可能犯比他女儿犯下的更严重的叛
国罪行的人。
“我将支持你,即使这意味着我的耻辱。我的斯维也特拉娜必须面对她行动的
后果。”瓦涅也夫坐直身来擦着他的眼。他看起来象一个即将面对枪毙队的人,搜
集着他的男子气概准备最后的顽抗。
“我也许不得不亲自指责你,”纳尔莫诺夫说道。
“我会理解的,安德鲁什卡,〔安德烈·纳尔莫诺夫的爱称。——译者〕”瓦
涅也夫答复道,他的嗓音充满尊严。
“我宁愿不这样做。我需要你,伊里亚。我需要你的忠告。如果我能保住你的
位子,我会尽力的。”
“我不能比这要求更多了。”
是说好话笼络他的时候了。纳尔莫诺夫站起来,绕过他的办公桌来握着他朋友
的手,“不管他们告诉你什么,毫不保留地表示赞同。时机到来时,你将跟他们显
示你是什么样的人。”
“就跟你一样,安德烈。”
纳尔莫诺夫送他走到门口。他还有五分钟才到他的下一次约见。他的工作日充
满了经济事务,因为部级的干部不作决定而到了他这儿,为了得到他的恩准而找到
他,就象从一个乡村神父那儿获得祈福一样……就象我的麻烦还不够多似的,苏维
埃联盟共产党总书记心中告诉自己。他用他的五分钟来数票数。这对他应该比对他
的美国对手容易些——在苏联只有政治局正式成员才有权表决,并且只有十三名正
式成员——但是每个人代表着一种利益的总成,而纳尔莫诺夫要请求他们之中每个
人去做以前从未仔细推敲的事情。说到底,权力比其他一切都管用,他对自己说,
而且他还能够信赖国防部长雅住夫。
“我想你会喜欢这儿的,”波克鲁什金将军说,这时他们走过外围栅栏。他们
通过时,克格勃卫兵举手敬礼,他们两人都还了个无心的手势。狗现在不见了,根
纳第想那是一个错误,不管是不是狗食的问题。
“我妻子不会喜欢这儿,”邦达连科答复道:“她跟随我从一座军营走到另一
座快二十年了,现在终于到了莫斯科。她喜欢那儿。”他转身看着栅栏外面,笑了。
一个人真能厌倦这一景色吗?但我告诉我妻子这事时她会说什么呢?不过一个苏联
军人并不常有机会作出这样的选择,她会理解这点,不是吗?
“也许将军的星会改变她的想法——并且我们正努力使这个地方更加受用。你
能设想我是怎样辛苦地争取这件事?最后我告诉他们我的工程师就跟舞蹈演员一样,
他们必须幸福满意才能工作。我想那个中央委员是个大芭蕾舜团的崇拜者,那种说
法终于使他明白过来。那时剧场才批准下来,那时我们才开始得到用车运来的好食
品。到夏天时学校就会完工,所有的孩子都会在这儿。当然”——他放声笑道——
“我们还得加建一片公寓大楼,下一个‘明星’司令员也必须是一位校长。”
“五年之后我们有可能没地方建激光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