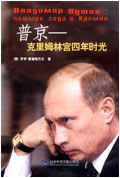克里姆林宫的红衣主教-第6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们还得加建一片公寓大楼,下一个‘明星’司令员也必须是一位校长。”
“五年之后我们有可能没地方建激光了。哦,你把最高点留给激光了,我明白。”
“是的,那场争论持续了九个月。仅仅为了说服他们我们最终可能想要建立比
我们现在已经拥有的这台更加强大的东西。”
“真正的‘明星’。”邦达连科评论道。
“你将来建立它,根纳第·约瑟福维奇。”
“是的,将军同志,我将去建立它。如果你还要我的话,我将接受这项任命。”
他再次转身环视地形。有一天这都将是我的……
“安拉的旨意,”少校一耸肩说道。
他开始厌烦听到这句话。神箭手的耐心以至信仰都被这个被迫改变的计划考验
着。在过去三十六小时里,苏联人一直间断不停地沿着山谷道路调动部队。这事开
始时,他已经把一半力量移过了这条公路,接着度日如年地煎熬着,而他的队员们
被一分为二,两边都观察着隆隆开进的卡车和运兵车,一边思量着俄国人是否会停
车跳出来,登上山来寻找他们的来访者。如果他们企图那样做,将发生一场血战,
很多俄国人会死去——但他不仅仅是到这儿来杀死俄国人的。他在这儿是为了以一
种简单的兵员损失永远也办不到的方式来损伤他们。
但是还要攀登一座山,而他现在严重地落后于时间表,任何人所能提供的安慰
仅仅是安拉的旨意。当炸弹落到我妻子女儿时,安拉在哪里?当他们抢走我的儿子
时,安拉在哪里?当俄国人轰炸我们的难民营时,安拉在哪里……?为什么人生一
定是这么残酷?
“很难等待,对吧?”少校说道:“等待是最难的事情。没有任何事情占据头
脑,问题就来了。”
“你的问题是?”
“战争什么时候结束?有谈判……不过多年来一直有谈判,我厌倦这场战争。”
“你大都花在另一……”
少校的头猛地转过来,“别说这个。多年来我一直给你的这一队提供情报?难
道你的首领没有告诉你这情况?”
“没有。我们知道他曾获得过一些东西,但是……”
“是的,他是一个好人,他知道他必须保护我。你知道有多少次我把我的部队
遣送上无用的巡逻以使他们错过你们,有多少次我被我自己的人民开枪射击——知
道他们想要打死我,知道他们是怎样咒骂我的名字?”这股突发的感情洪流把两人
都惊呆了,“最后,我终于不能忍受。我的部队中那些愿意为俄国人干事的——嗯,
不难把他们送进你们的埋伏围,但我不能只派遣他们,不是吗?你知道吗,我的朋
友,有多少我的部下——我的好战士——我送到你们的手下而死去?那些和我永别
的战士是忠于我的,是忠于安拉的,是彻底加入自由战士的行列中的时候了。为了
那些没能活到这个时刻的人,但愿上帝宽恕我。”每人都有自己的传奇故事,神箭
手沉思道,而唯一贯穿一切的主线只不过是一句话:
“生活是艰难的。”
“对那些在山顶的人来说,生活将会更加艰难。”少校环顾四周,“天气在变。
风现在是从南面刮来。云带来了潮湿空气,也许安拉毕竟没有抛弃我们。也许他将
让我们继续这次使命。也许我们是他的工具,而且他将通过我们向他们显示他们应
当离开我们的国家,免得我们来造访他们。”
神箭手咕哝着往山上看。他不再能够看到攻击目标,不过那没关系,因为,不
象少校,他同样看不到战争的结束。
“我们将于今晚把其余的都带过来。”
“对。他们都会休息得很好,我的朋友。”
“克拉克先生?”他在跑步机上几乎练了一个钟头。他关掉开关时。曼寇索能
从他满身的汗水看出来。
“是的,艇长?”克拉克取下耳机。
“什么样的音乐?”
“那个声纳小伙,琼斯,把他的机器借我了。他有的都是巴赫,不过它确能保
持大脑忙碌。”
“给你的电讯。”曼寇索把它递过去。这张小纸条只有六个字。它们是密码字,
必然是这样,因为实际上一点意思也没有。
“是行动的信号。”
“什么时候?”
“它没指明。那是下一道电讯了。
“我想是你告诉我这件事情怎样进行的时候了。”艇长评论道。
“不能在这儿。”
“我的卧舱在这面。”曼寇索挥手指道。他们往前走过潜艇汽轮机然后通过反
应堆舱,其舱门极其吵人,最后他们通过攻击中心,走进曼寇索的舱位。这大概是
在潜艇上能走的最长距离。艇长扔给克拉克一条毛巾,让他擦脸上的汗水。
“我希望你没有把自己累垮了,”他说道。
“是无事烦的。你的人都有事可做。我呢,只是坐这儿坐那儿,等着。等待真
他妈不痛快。拉米乌斯艇长在哪儿?”
“在睡觉。他不必这么早就参与这事,对不对?”
“不必,”克拉克赞同道。
“这活究竟是什么?你现在能告诉我吗?”
“我要带两个人出来,”克拉克简略地答复道。
“两个俄国人?你不是要搭一件东西?两个人?”
“对。”
“并且你要说你老干这样的事?”曼寇索问道。
“倒不完全是老干这事,”克拉克承认道:“我三年前干过一次,在那前一年
干了另一次。另外两次根本没执行,我没发现为什么不行。‘需用者知’,知道吧。”
“我以前听到过这个说法。”
“很有意思,”克拉克若有所思地说:“我敢打赌那些做决定的人从来没有让
他们的屁股蛋露在外头……”
“你要搭上艇的人——他们知道吗?”
“不知道。他们知道要在一定的时刻到一定的地点。我担心的是他们会被特殊
武器及战术队的克格勃包围住。”克拉克拿起一个无线电,“你这头很容易。我不
按正确时间,不以正确的方式说恰当的话,你就和你的潜艇赶快溜出这儿。”
“留下你不管。”这不是一句问话。
“除非你宁愿同我在列福尔托沃监狱会合。当然是同其他船员一起。在报上看
起来可能很糟糕,艇长。”
“我看你也是个很明事理的人。”
克拉克笑了,“那真是说来话长。”
“艾希上校?”
“冯·艾希,”驾驶员纠正杰克,“我的祖先是普鲁士人。你是瑞安博士,对
吧?我能帮你做什么吗?”杰克坐了下来。他们正坐在武官的办公室里,武官,一
位空军将军,让他们使用它。
“你知道我为谁工作吗?”
“我隐约记得你是搞情报那伙中的一个,但我只是你的驾驶员,记得吗?我把
重要的东西留给穿着柔软服装的人们。”上校说道。
“再不是这样了。我有一件工作给你。”
“你是什么意思,一件工作?”
“你会喜欢的。”杰克错了,他不喜欢。
他很难专心致力于他的正式工作。部分的原因是谈判过程的令人头脑发僵的枯
躁无味,但最大的原因是在他非正式工作中后劲十足的葡萄酒,而在他玩弄着他的
耳机来收听所有苏联谈判者第二遍发表的目前这篇演说的同声翻译时,他的头脑还
在那非正式工作上转来转去。前一天的暗示,即现场检查将比先前同意的还要有限
些,现在已删去。而他们现在请求更广的权限来检查美国场所。这会使五角大楼感
到满意,杰克偷偷地笑着想到。俄国情报官爬遍工厂,钻下发射井来观看美国导弹,
随时都处在美国反间谍报官员和战略空军司令部卫兵警惕的眼睛注视下——而这些
卫兵始终都手握他们崭新的“贝雷塔”牌手枪。潜艇那些小伙子常常把他们自己的
海军的其他部分当成潜在的敌人,对俄国人上他们的艇会怎么想?听起来他们好象
不能比站在甲板上更进一步,而在里面的技术员在潜艇全体人员及守卫导弹潜艇基
地的海军陆战队员警惕的目光注视下打开发射管口。同样的事情也会在苏联方面发
生。每一个送到核查小组的军官都会是个间谍,也许掺进几个指挥军官来注意只有
一个使用操纵者才会注意到的事情。真是妙不可言。在美国三十年坚决要求之后,
苏联人终于接受了双方都应该允许官方承认的窥探的这个主意。在前一轮关于中程
武器的谈判过程中,当苏方表示同意时,美国的反应曾是惊异而怀疑——为什么俄
国人在应允我们的条件?他们为什么不说“是”?他们究竟企图干什么?
但这是进步,一且你变得习惯于这主意。双方都有了一种知道另一方在干或者
干过的事情的方法。没有一方会信任另一方。双方的情报组织会保证这一点。间谍
仍然会四处游弋,寻找另一方的种种迹象,表明另一方是否在欺瞒,在一个秘密地
点装配导弹,把它们掩藏在奇怪的地方以便突然袭击。他们会发现这种迹象,拟出
临时警告报告书,并且试图彻底搞清这项情况。制度化的偏执狂将比武器本身更耐
久。条约不会改变这点,尽管报上有形形色色的欣快异常的评论报导。杰克把眼光
转向那位滔滔不绝的苏联人。
为什么?为什么你们这些家伙改了主意?你们知道我在“国家情报评估报告”
中所讲的东西吗?它还没有上报刊,担你们可能巳经见过它了。我说你们终于意识
到:①那些该死的东西要花多少钱,②一万个弹头足够八次烧焦整个美国,而烧焦
三四次大概就够了,③通过消除你们所有的老式导弹,那些你们再也不能很好地维
护的导弹,你们将省不少钱。这只是生意经,我告诉他们,而不是你们看法的改变。
哦,对了:④这是一项很好的公共关系,而你们仍然爱玩公关游戏,即使你们每次
都给搞拧了。
当然,我们倒不在乎。
一且协议通过——杰克认为它将通过——双方将省下他们的国防预算的百分之
三左右;对俄国人来说也许能达百分之五,因为他们有更加多样化的导弹系统,不
过很难确定。全部国防预算的一小部分,它足够让俄国人筹资兴建几家新工厂,或
者修筑几条道路,这才是他们真正需要的。他们将怎样重新分配他们省下来的钱?
至于这个,美国将怎样做?杰克也应当作出关于这点的估价,另外一份“特别国家
情报评估报告”。标题听起来是颇高的,而内容毕竟只不过是一个正式猜测而已,
在这一时刻,瑞安没有一点线索。
这个俄国演讲结束了,是咖啡小休的时间。瑞安关上他的皮革面文件夹,同每
人一起成群结队,走出谈判室。他选了一杯茶,只是为了换个花样,用小吃点心装
点他的茶盘。
“那么,瑞安,你以为怎样?”是葛洛甫科。
“这是正事还是社交活动?”杰克问道。
“后者,如你愿意的话。”
杰克走到最近的那个窗子前向外看。这些日子里总有一天,他向自己许诺道,
我将看一看莫斯科。他们这儿一定有些东西值得照点相片。也许和平总有一天会到
来,我就能把全家都带来……他转过身来。但不合是今天,不会是今年,也不合是
明年。太糟了?
“谢尔盖·尼古拉也维奇,如果世事通情达理,你我这样的人会坐下来,两三
天内就把这些傻事统统干完了。真见鬼,你我都知道双方都想削减一半库存。我们
争执一周的问题是意外核查小组到达前应提前几个小时通知对方,但是没有一方能
统一步调达成一致意见,我们正在谈论我们已经达成协议的东西,而不是继续进行
谈判。如果仅在你我之间,我会说一小时,而你会说八小时,我们会最终讲下来到
三四个……”
“四五个小时。”葛洛甫科笑道。
“四个小时,定了。”杰克也笑了,“你瞧?我们能解决这狗杂种,不是吗?”
“但我们不是外交家,”葛洛甫科指出,“我们知道怎样讨价还价,但不是用
已被接受的方式。我们太直接,我和你,我们太实际了。啊,伊万·埃米也托维奇,
我们还可以将你变成一个俄国人呢。”他刚把杰克的名字俄国化了。伊万·埃米也
托维奇·约翰〔杰克是约翰·瑞安的昵称。——译者〕,埃米特的儿子。
又是谈正事的时候了,瑞安想到。他改换了思维方式,决定轮到他来牵另外那
人的鼻子走,“不,我不认为如此。这儿变得有点儿太凉了。告诉你说,你去找你
的谈判负责人,我就去找欧尼大叔,我们将告诉他们我们所谈定的核查预警时间—
—四个小时。现在就去,怎么样?”
这一下把他搞蒙了,杰克看得出来。在短短的一瞬间,葛洛甫科以为他是说真
格的。这位格鲁乌-克格勃军官马上恢复了镇静,甚至连杰克也差点没有注意这一
失误。笑容几乎没有中断,但在这表情固定在嘴角周围时,它从眼中短暂地消退,
然后又返回来了。杰克不明白他刚犯下的这一错误的严重性。
你应该是十分紧张,伊万·埃米也托维奇,但你不是。为什么?你曾是这样。
那天晚上在招待会上你绷得那么紧,我以为你会爆炸。并互昨天你递给我那张条子
时,我能感觉出你手心上的汗。但是今天,你在开玩笑。你试图用你的戏谑之言来
引我失常。为什么截然不同,瑞安?你不是一个外勤情报官。你早先神精紧张征明
了这一点,但现在你的行动象一个外勤官。为什么?他自问道,一边随着其它人鱼
贯走回会议室。每个人都坐下来准备听取下一轮长篇独白,而葛洛甫科用眼观察着
他的美国对手。
瑞安现在不是烦躁不安,他有些吃惊地注意到。星期一和星期二他都曾坐立不
安。他看起来只是毫不感兴趣,不比这更不舒服。你应该是不很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