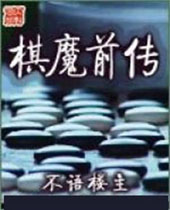昆山玉之前传-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牛车如风驰电掣,月光一路相伴数十里。和田的月色,先是绿洲沙枣树冠的明媚,而后是千寺遗址边缘的皎洁。当夜行人逐渐抛离了城池,巍峨浩荡的昆仑山脉连绵而出。那时,雪峰如银,月色如银。端午的魂灵,被这种自然美景,激越出狂喜的火花。
那火花留在少女脸颊上,又被她那双清亮的眸子,抛给前方广阔的大河。
那条大河在月下闪着无数银色的光点,川流不息,宛若生命。
尉迟注视她说:“这就是玉龙喀什河。突厥语是白玉河。没有它,就没有昆山玉。”
他发出一声长啸,车停在河谷碎石滩上。端午率先跳出了车子,她看似顽皮,捉着尉迟手中那根柳条。尉迟想要将柳条送给她玩,身子向前一倾,端午顺势扶住了他。
她旋即离开他,背过身去,挥舞起柳条,重重踩那些坚硬的碎石。她突然歪了下嘴,原来是鞋底忽然穿了个孔,露出两个脚趾头来。她吐了吐舌头,装作若无其事,回头看尉迟。
那尉迟手中持了根及腰的银杖,微微一笑,便向前走去。手杖敲击石子,叮咚作响。
端午随着他转过河弯转角。尉迟迎风站住,向她点头。
半片轻云,抚过银蟾。玉龙喀什河更像银河。端午居高临下,看清河中景象,不由惊叹。
大河哗啦啦冲刷河道,雪山在水里斑斓倒影。若隐若现的光斑中,竟伫立着一个个赤 身的西域女子。她们抱着淘箩,不时俯身,步步前行,任由雪融冰河漫过腰腿。夜色中,女子们的裸 背,散发着玉一样的清辉,令人忘却杂念。她们的头上,缠着色彩鲜艳的头巾。远远看去,就像成群天女下凡玉河,又像是散落于激流中的花朵……
尉迟嗓音低沉:“昆山玉,以此河之子玉为最上品。从古到今,我们和田的姑娘和妇人,都在月色下,到这条河中捞取美玉。我母亲说:美玉乃是月的魂魄,凡是月光最明朗的地方,就会藏着好玉石。然而,玉和珍珠一样,也是汇聚天地之阴气,所以这样的工作,只有女子才最能胜任。端午,你说,你会像喜欢合浦珠一样喜欢昆山玉吗?”
端午眺望着河,点了点头。其实,她喜欢的是合浦珠本身之美,而不是合浦珠的价高。昆山玉,在她心里,因为这个晚上,因为尉迟公子,更多了一份神秘的色彩。
她忽然问:“那些女人……是奴隶吗?”
尉迟摇头:“她们不是任何人的奴隶,却为了找玉而辛苦。玉石,能换来衣食药品。世间任何东西,都是要代价的。”
端午转了转眼珠。她想起尉迟所说的白玉帝国……那需要怎样的代价呢?
尉迟仿佛不知她所想,近乎痴醉,无声无息地望着玉龙喀什河。作为一个采珠司长大,见识了商人唯利是图的奴隶,端午忽然为他的神情而感动。她想到了八娘子,不由暗暗惆怅。她鼻子发酸,仰面天幕,一只山鹰,正展翅翱翔。
尉迟跟着仰头,此刻他的语音也近乎深情。
“端午,我知道你正在想你母亲。在我彷徨时,也会想起我母亲。我尚在襁褓中,尉迟家败落。人们肆意嗤笑这一失去了荣光的姓氏。父亲更抛弃了我母子,选了另一位佳人。因为他觉得我这样的男孩,无法继承他的志向。母亲去世后,我流浪世间,渐渐忘了她的容貌,但我记得玉河里她的笑声,她的足迹。无论我走到哪个地方,只要想起母亲 ,我就闭上眼睛,能听到这条河的奔流。它重复着回来,回来。你闭上眼,能听到海的声音吗?”
端午闭上了眼睛。过了片刻,她睁开眼皮,眼湿润了。
她吐了口气,坚定说:“总有一天,我要回去找我娘。”
尉迟引领端午走出河谷。大河从宽陡窄,两岸有芦苇萧萧。
大河对岸,黑影幢幢,坡地上有数簇火炬。
端午问:“那是房子吗?”
“不错,若要取得最美的玉石,就必须在玉龙河最险要地方,建立起管辖采玉人,及时选玉的场所。那些房屋还在兴建……再等等……”
他话音刚落,对岸隐起骚动。叫嚷声,脚步声,此起彼伏。
尉迟静听,目光灼灼。有数人快步涉水而来。为首的用和田土语报告什么。
端午本以为尉迟今夜形迹秘密。转念想:身为城主,不至于任性夜游。
尉迟摇手,唇边掠过一丝笑。端午为那丝笑惊了一瞬。不待她想明,尉迟说:“对岸不比此处安全。你且留在这,我去去就回。”
“……好!城主轻便。我哪也不乱走。”
尉迟将银杖给她,弯腰说:“此杖内有毒液,一刺便可置人畜于死地。拿着,别推辞!”
端午点头,心跳极快,仓促说:“你多小心。”
一个大汉背起尉迟,淌过河水。
端午凝望对岸,不由焦急。除了河水声,喧哗声,她听到了更多,那是来自昆仑山,来自鸟兽,来自黑夜的重重声响。她抱肩环顾四周,靠月光分辨一切。
突然,她警觉到河滩芦苇丛,爬出一条断尾蜥蜴。芦苇间,发出嘎吱几声。
她没大喊,压抑着恐惧。先发制人……她不能等任何人攻击她。
白花芦苇,月下含着妖气。端午静默,举起手杖,忽朝那地方冲过去。
她刺过芦苇,用手杖尖点住生物。她呆住了,那蜷缩着的人,也“呀”一声。
是个红头发小孩……是随他们一起进城的小松鼠!
“怎么是你?”端午凶巴巴威胁:“喂,我不许你动一下。”
小松鼠牙关咯咯,浑身寒颤。他缠着手帕掌心,像被什么东西穿透了,鲜血淋漓。
端午壮胆蹲身,小松鼠张嘴,却喷出一股松子甜香。
他盯着端午,吃力说:
“美丽姐姐啊,
不要同情我,
也别帮助我。
我已准备好:
有金就有蛇,
有花就有刺,
有甜就有苦,
有生就有死!”
端午眼冒怒火,低声:“你犯了什么错,小小年纪就准备死?我杀人,也骗人,可我觉得,活着总比死好。你只会说漂亮话。既然准备死,躲这里做什么?”
小松鼠闭上了眼。他从牙关里蹦出几个字眼:“……哥哥……哥哥……”
端午面前,迷雾顿起:怎么办?引发对岸骚动的就是小松鼠?他不是一个流浪的小诗人吗?喧哗复归于平静,没有多少时间来决定了……她捧起苇丛边几块沾上血迹的石子,推入水中。快速起身,顺着河岸线向前方跑去。跑了好一会儿,她下水,以手杖拨弄河面。
对岸人已发现她,尉迟大喊:“端午?”
她大声答:“方才有条大鱼……”脚跟打滑,她倒在水中。
尉迟不要人背,以超乎想象迅捷,拽行到河滩。
端午露水,一手拿杖,一手抓快石头:“玉!城主,我找到了一块玉!”
尉迟笑而摇头:“那不是玉。快上来!”
端午心思百转,露齿一笑。几个人顺着河岸下去,好像也要找“大鱼”。
端午被带到一间烧火木屋,尉迟给她喝了点鱼汤。她问:“危险过去了吗?”
“嗯。过去这些河滩,常有野猪,野狼出没。也许是在山中太饿,才会下山的。他们一时惊乱,不足挂齿。”尉迟语气稳妥。
端午寻思,要不要告诉他小松鼠的事?如果……他不能饶恕小松鼠呢?小松鼠……究竟做了什么?她飞快坚持了方才决断:即便是小松鼠有滔天大罪,她不愿成为揭发他的人。
她不想让尉迟看出来,也亏心于面对这蔼然微笑,她只能装瞌睡。
尉迟似不忍心唤醒她。端午真要睡着了,他才来拍她:“回去了?”
连上车,她都是疲倦样子。牛车停在尉迟府前,她才彻底睁眼。
天还漆黑,月影朦胧。
尉迟不急于下车,凝视她,认真说:“端午,我会让你留在这里。"
她脸上发烧,那不是少女怀春,而是出于愧疚。
从金刚顶阴影下,闪出来一位牵马的年轻人。
此人面如冰玉,语气更冷:“那可不是你说了算,无意哥哥。”
尉迟沉默片刻,懒懒笑道:“是子京?看来,你的酒量见长,功夫也见长了。”
端午伸头。天哪,燕子京……他没有醉……?难道,他一路跟着他们?
燕子京冷笑:“我酒量没长,只戴了个解酒用的戒指而已。我听说,采珠司有人不断打听你,所以借这丫头来试探。果然,公子无意,处处有心。你让老头送上珍珠的时候,我就知你想跟我玩。伸手就摔断项链的人,哪能被你差遣去蒙古王廷?”
尉迟保持笑容:“子京,你实在聪明。我是和采珠司有渊源。然我这种白手起家的人,总爱对发迹历史讳莫如深。我刚才确定端午是故人之女。本想等你休息好后,才找你商量。”
“我已休息了个够。你拒绝帮我,我不能强求。我比你们早回到城里。仆人们已尽数在城门等候。这女孩是我的货。我现在不乐意卖她,也不会把她送你,因为你终究骗了我。”
尉迟叹息:“子京,你太多心了。你来我府上,先说要通关文书。可你身边难道没藏着大元知枢密院事 燕帖木尔亲笔盖印的过关信?当然,我并不责怪你。”
“无商不奸。是你教我的。”燕子京道。
“毋宁说‘兵不厌诈’。我也教过你。”尉迟说。
端午全然清醒,咬住嘴唇。燕子京不可理喻,而尉迟本不可能单纯。
跟着燕子京走,会痛苦。留在尉迟家,也没那么容易。
尉迟缓缓到燕子京身边,扬出赶车柳条,好像要抽头顶金铃,又猛然收手。
他问:“这个人,你当真不能留给我?”
“不能!先前,我已令使者绕开和田,快马加鞭,把我的礼单上呈给诺敏王府。如果你执意留下她,我不知是否会激怒谁。”燕子京斩钉截铁。
尉迟收住笑。他手里柳条蓄势待发。
燕子京直视他,忽而话锋一转:“无意哥哥,我和你如此争执,太伤和气。不如问问端午,她想去,还是留?端午,我忘了,你包袱还在那辆驴车上。先拿了包袱,再决定。”
带棚驴车,藏在大门边。燕家仆役闻声,将车赶到端午面前。
端午疑惑,那几件破玩意,还能成我包袱?她走到车前,掀开帘子。
她瞳仁变大,手一顿,眨眨眼。
尉迟把脸转向她,她脑子一片白茫茫。不过,那只是一瞬间的事。
接着,她对尉迟躬身:“多谢城主。我还是打算跟爷上路,包袱嘛,还是放车上好了。”
尉迟似感意外。他望了一眼燕子京,没说话。
燕子京好像对端午决断那么快,也有点意外。他望了望天,东方既白。
尉迟凝望端午良久,语调恢复了平静:“后会有期。”
端午深深鞠躬。她相信,尉迟说后会有期,一定有期。
尉迟从怀里掏出本东西:“子京,通关文书,我预先备好。这路上,最好不要显露你和大元高官关系,免得遭忌。还有,你别走小路,一定走官道。当心昆仑山匪帮……千万千万。”
燕子京拱手,骑马先行。端午上驴车,挥手告别。尉迟负手而挺身,端立门庭。
过一会儿,端午再从帘缝回望。那门庭已空无一人,只余萧瑟。
驴车里起了呻吟,端午低头,捆绑手脚的小家伙,终于醒来了。
她替那孩子拿掉塞口布条。小松鼠迷迷糊糊道:“哥哥……?姐姐,你!?”
端午笑得难看。心想:不是我这傻瓜,还能是谁?
第六回:浮光魔影
端午决定跟着燕子京走,确实是因为看见小松鼠。但是,并不是因为小松鼠被人贩子抓住,她才会受了燕子京要挟。有了腊腊的教训,端午对其他孩子多了份警惕。与其说她想要把小松鼠从燕子京牢笼里救出来,不如说她先想弄明白小松鼠为何要出现在白玉河边。
昨晚,她在尉迟无意身边经历了太多。回府路上,似在沉睡的端午,忍不住困惑。感受了惊愕,痛苦,欢乐,恐惧之后,她眼中的尉迟,已不是初见时的他。凭借十几年阅历,她不足以让自己信服。安逸的生活,温雅的男子,白玉国的辉煌,都唾手可得。世上有那么容易的幸福吗?苦尽甘来,只需一通奇遇?无疑,自己是能识别宝物的。但以尉迟之慧,遇到她之前,可能只寄希望于远在南海湾的小奴?紧锁铁门之后的女子们,也是白玉王国的助手?
采珠司人情淡薄,端午习惯了不添麻烦,尽量能胜任愉快。让她捧痰盂,她会喜爱痰盂。让她赶苍蝇,她就喜爱蝇拍。让她打算盘,她做梦都梦到算盘,更不要说后来在交易屋成日与珍珠打交道。虽离廉州万里,但习惯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中改变。以府门口尉迟对燕子京的形状,她若选择留下,尉迟就不得不和老相识燕子京翻脸。翻脸也罢了,以燕子京之人脉,尉迟还会因她而得罪诺敏王府,大都城贵人。无论如何,这不是端午所要的。
她跟着燕子京行路,是为了见机行事,也是为了不欠尉迟。
端午想到这,长出口气,不再觉得自己傻。
小松鼠脸色灰白,端午跪下来,拍拍他肩:“喂,要挺住!你总不想让人家说诗人的儿子骨头软吧?”
小松鼠“嗯”了几声。端午听着不紧不慢的驼铃声,心情一阵紧,她掀开车帘,焦躁喊道:“要死人了!水呢?”
燕子京飞步而来。端午如今才知道,他有几分武艺,难怪尉迟说他“功夫长进”。他能跟踪尉迟到玉河而不被发现,又能趁乱从尉迟眼皮下带走小松鼠,几乎堪称高手。
他脸上并无“要挟成功”的得意,那双眼也不再是半合办开的“瘟神样”。
他轻捷跃上棚车,手指轻拨端午。端午往后一撞,肩部都被震麻。
燕子京一把将小松鼠裹手帕扯开。那孩子痛楚呻吟。端午皱眉。
晨曦下,小松鼠手掌伤口,更为可怖。
燕子京掌覆小松鼠腕骨:“你半夜三更在沙漠死者的坟场出现,我就觉有鬼。说!是谁叫你去独闯禁地?那声名显赫的城主,向来爱用机关。你这手被‘噬骨钉’穿透,十有八九废了!你不说实话,我不会救你。反正奴隶手残,也卖不掉。”
小松鼠痛得发抖,咬住缕红发答:
“万年前便有玉河,一切归于造物。人人自命为主子,我却不知何为禁地。”
燕子京摊开他血肉模糊手掌,他惨叫一声,端午呼吸急促。
“说!你一直喃喃哥哥。谁是你的哥哥?”
小松鼠抽搐着,像落在干涸沙漠的鱼儿。他吃力道:
“爹娘之爱有十停,九停都赐给了我。还有一停,他们带去天国。我没手足兄弟……”
燕子京还要发力。端午忽纠住他袖子,斥道:“别再折磨他!他死,我保证你会损失俩个人。”
燕子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