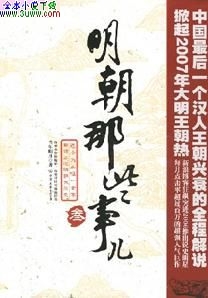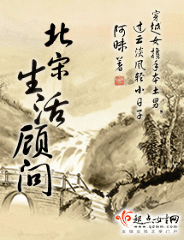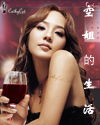�������峯������-��14����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Ů���ű��Ǹ����ֺ���һ���������Ȼ�����������˵��Ů������������ѹ��Ů�ӵĹ�������������˵Ů�����������������ʵ�������Ϳ������Щʹ�ࡣ���������ﲻ�ǽ����������ǽ�ʵ�ʡ���������
��������������ʵ�ʳ����Ƿ���ġ��ϲ����Ů�Ӷ��������࣬�������Ķ࣬�Ѹ����ļĶ࣬�²����Ů�ӵ���Щ���������٣��Ѹ��ټĶࡣ˭���ط⽨����˭��ù�����ݽ���ʷ���ż����Ѹ���ǰ����������Ԭ��˵�öԼ��ˡ�Ԭ�����ش�һ���գ��ڡ������־���������ݸ�־���ﱻ���˴���������ʷ�塷Ҳ����д�롶��Ů������������ʷ�����ˣ��������˵�������������ҡ�Ѫ�ỻ���Ľ���֮����ʵ��̫�п��ˣ��������ֵ��µ����̫���ࡢ̫����ʹ���ˡ�Ԭö��Ԭ���ֵܰ�Ԭ���IJ��ҹ�֮�ڶ����вţ���һ����������Ů�IJ��ң�ȷ������кܴ��ϵ������֮���ã��ڹŴ���������Ů�����ϣ�����������ʩչ���ܣ���������ɶ�����ˣ�����������ô������ͼ�������������ǶԲ�ͬ���˶��Եģ�������ʱ������ƶȾ����ġ�����ͳ��Ů�Ե���ᣬ��ϣ��Ů����������Ȼ����д������ǵ�Ů�������صĴ�������Զ���֮�������ùؼ���������ƶȺ����ߣ������Ǹ��������������Ů���Լ����˶��鲢�������á�Ԭ������ͬ���˵�Ů�ӵ���ʷ���������Լ���һ������ƶȵ����ӡ����ܸ��������Է��Ӵ�����ܣ��ر����ܸ�Ů���˷��������������ᣬ���д������ġ��л�������ᣬ����֮��
��̬��Ӱ��������13�ڡ���Ů��ϰ����Ӥ�õĽ�����1��
����������Ů��ŮӤ��һ�أ��ͱ������������������൱���еĶ�ϰ���������꣨1878������Ժ������������д���ۣ������ֹ�����Ů����д������������
�������������Ů��������ά�裬��������ң�����Dz�ޣ��������ͱ����£��˷��ʡ���У�������ʢ����ʡ���о������Ļ��³̣���֮���꣬ȫ��١�����ط��ٷ��в�����������δ�ܱ��У������������Ȱ�졣��������
���������峯��˷������ͣ�Ҫ����Ѳ������谶������ع�����������Ļᣬ�����;�����Ȣ��Ӽ���������Ů֮Դ���������и�ֱʡ������һ���մ˰�������������������ͳ�뼯�ɡ�����ʮ�ˣ���������ۺ����ͣ�ȫ���漰����Ů���������ԭ��״�������Ȱ취���������̸̸��Щ�������⡣������������˵����Ů�Ƿ���ȫ�������飬�Ⱦͱ����������ϣ��б�����֮����������
������������״�����ϳ�����������
�������������ڶ���Ů�����Ѿã�����Ϊ��Ȼͬ�Ρ�������־�����塶���ס���������
���������˻�������Ů�����ܡ�ƽ����ĸ塷�¡�����֪������ɽ��״����������
����������ƽ��Ů����֮���졶�ɽ���־������ʮ�ߡ�������������
��������ʯ����Ů�����ؽ�Ȼ��ʯΪ�����⡶ʯ����־����һ�����ס���������
���������˹���Ů֮�������Ѿã�Ŀ��Ϊ��ͬ�Ρ��˹���־����ʮһ�����ס���������
���������㽭���ҷ�����Ů���㽭������ʢ�������ʳ���м¼������ʮ�ˡ����ס���������
�������������ײ�Ů������졶�ɽ���־������ʮ�ߡ����崫����������
���������㶫���گ�ν����ϵ�����������Ů��������־���������ټ�����������
����������������Ů�����ٹ������ζ���־����ʮ�����ſ�ҵ������������
����������������ʢ��Ů�������������־�����������ס���������
����������������Ů������������־������ʮ�塶��豴�����������
�����������պ�������Ů�������������־������ʮ�ˡ���˼�ʴ�����������
������������ͬ�ϼ��졶����־����ʮ�š�ܲ�С���������
���������ߺ�����ϲ����Ů�������ڼ��졶�ߺ���־������ʮ����Ӥ�ñ��ǡ���������
������������������Ů�������ζ���־����ʮ�����̺�����������
��������캵�Ů�������ټ��졶캵���־����һ�����ס���������
�����������ݸ�����Ů���⡶���ݸ�־����ʮ��������������������
��������ͭ���ϰ��Ů������ߣ�������Ů֮��Ǭ¡��ͭ����־�����������ס���������
��������������Ϫ����Ů�������Ч����Ǭ¡����Ϫ��־�����š���������������
������������������Ůͬ�Ρ���Ԫ��������־������ʮ�ġ�Ҷ���ʹ�����������
����������������ŮǬ¡����Ϫ��־�����š���������������
�����������ϳ��¸���ϣ֣��֪����������Ů���������־������ʮ�ˡ���ϣ��������������
������������½����Ů�߶��ױ�ƣ���������֮�������Ů�����½����־�����ġ����ס���������
�����������վ��ݲ�Ů�߶���֮������������־����ʮ����֮��������������
�����������ݸ�������Ů���������������־������˶���������崫����������
���������ߴ���Ů��ϰ֮���ң����紾�߹������ߴ���־������ʮһ����Ů�䡷��������
�����������صض���Ů���������־������ʮ������λ������������
������������������ʡ�ĸ��أ���������Ů��ϰ���صĵط����������������������潫Ҫ�������ĸ��������Ů����������Ӥ��һ�£�������¶��Ω�DZ����Ķ��ؼ������Ƿ�־���㣬�������ꡣ��������
��������������������Ů�أ�������˵�öԡ���������ά�衱��������ġ���Ϫ��־��˵����ƶ����Ů��١���ƶ���˼������˿ڶ��������棬����ŮӤ�����Ƹ�����ά�֣�ֻ����ʹ�ͱС�
��̬��Ӱ��������13�ڡ���Ů��ϰ����Ӥ�õĽ�����2��
�����������Ǻ���ֻ��Ů��������Ӥ�أ��������潲��ֻ��һ������ԭ���������������ޣ�Ů�������żң�û�������ļ�ױ�����˿����𣬻�Ҫ�ܹ��š��没�С�õ��������ƷѰ��ױҲ���С����䵽��ʱ�Ʋ���ޣ����粻Ҫ�����ˡ��������������˵�ġ������ң�����Dz�ޡ����ʶ���Ϊ��Ů��һ��ԭ�������͵ġ���Ȣ��Ӽ��Ҳ�ǿ��������Ƽ�����Ů�Ĺ�ϵ����Ůʢ�еĵط����������������������ͬ�Ρ�������־��˵����Ϊ����֮�����ΪɱŮ֮�¡����еĵط����軧��Ů����Ҫ������������ӣ���Ի�����������軧Ϊ������ָ���������ŮӤ����������־������ʮ�������С���ת���Ը����衶����ũ����ᾭ�á�������������
��������������ݣ���ʱ��Ϊ�и����仨���������ӽ����Ѳƣ�Ϊʲô������Ů�أ�������⽨�Ĵ�ͳ�̳��ƺ�������Ů��˼��������Ҫ�����á���ͳ����ͥ�Ʋ�����������̳У�ÿ����ͥ��Ҫ�������Ժ��ˣ�����ҲҪ�и����̻���˰�����Ů����Ҫ��ȥ�ģ������˼ҵ��ˡ���˶��ڼ�ͥ��˵��Ů�������DZ����еģ��ɴ˲���������Ů˼�롣������������������Ůֻ��ȡ��һ��ʱ��Ȩ�����أ������ж���Ů�ˡ�������˼��֧���£���Ů���Ǻ���Ȼ�����ˡ����еļ�ͥ��ͷ��̥������Ů�������ҳ����������ձ������Ϊ����ŮӤ����Ѹ�����У���������������ŮӤ�������Ǭ¡�����ġ�����־����д�ġ������м�Ů�������ü���Ŀǰ֮���С���������ŮӤ�ˡ���������
����������Ůªϰ�����У�ʹ�˿���Ů���������ӡ��弾�ղ��˿ڣ��ݡ��峯������ͨ�������صı�����˳�츮�����֡���������ֱ����ɽ�����㽭���������Ĵ������ݵȵص�ͳ�����֣��пھ�����Ů��10�����ϡ��˿��Ա�ƽ�⣬��ϵ�����౾���ķ�չ�����Գ�Ϊһ��������⡣��������ĩ��ͳ�ƣ����ж�Ů�ٵ������ǵ���ʱ��ð�����ġ��ڴ���ǰ��ͳ�����Ѹе���Ů��������أ�һЩ�ط��ٲ�ȡ����ķ�������ֹ�������ŮӤ��Ǭ¡ʱ��Ϫ�������ơ���ʾ�Ͻ�����Ů�������������͡���ϣ������֪����Ů�ĺ����ٸ���̬�ȣ���Ǭ¡��Ϫ��־�����壩������ʱ��֪����½��������Ӥ����Ϊ����Լ��ʱ�ڵط�������Ȱ�䣬�����������Ӥ�ã�����ƶ�������������Ӫ�������ס����������еĹ��ź�ʿ����һЩ��ֹ��Ů���������纲��Ժ�̽�ʩ����������Ů�衷��Ȱ�˴�ŮΪ�ƣ��������ġ���ɽ�������С��е������������ϲ����Ҳ��������������������������������Ů�䡷����Ϊ�ڹ�Ҫ���������ء����Ը�ҥ����ʽ������Ů�����ֺ�Ϳ�������Ů�Ƽҡ���Ů���������ȣ�һһ���Բ��ۣ���˵����������Ů����ƶ��������������ס�����ǧ��һ����������լ�Ȱ����������Ӳ�һ���ܱ��ҡ����ң��α��ܿ��ż�Ů��Ǯ����˵�������ƾ�Ů����������ѡ����˭��֪���������������Ů��˵����ƶ��ɱŮ�ղ���������ʯ���㡣�����������������ס����ס���ѵ����������һ����������ȷ����������ʡ����������
���������ط��ٺ�ʿ�˵�Ȱ����Ů�Ĺ涨������������������Щ�˵�ҵ�������֣���˵�յ������õ�Ч���������������Ը����ª��һ�䡱��ʵ�����ڶ�ʱ���ڣ��õ���Ů����һЩ����ν���������������Ȱ���ߵĹ���֮�ʡ�����ȥ�ã���Ů������������������ʢ����Ů�Ľ������������ξ������Ϫ����������ڽ�ֹ�����ҹ涨��������Ů���ģ��������������Ŵ�����ʱ���֡�����Ů�ߡ��ľ��棨��������ͤ��־����ʮ�ģ������Ǻ������塢���گ�Ȼ��������ֹ��ֱ����ĩ����˵����Ů���أ��ɼ�������֮��������ʼ��������Ů�Ķ�ϰ��ֻ������ʱ����Ϊ��һ�㡣����������Ǭ¡��֪���̺������ͽ���ª��Ϊ�䡱���������ζ���־����ʮ������������û�б䣬ͬ�μ�����ġ�������ͨ־��˵�����������أ�Īʢ��ͣɥ����Ů���¡�����������ס�
��̬��Ӱ��������13�ڡ���Ů��ϰ����Ӥ�õĽ�����3��
���������⽨�IJƲ��̳��ƶȡ�����ƶȺ�˰�ƶ��µ�����ƶ�������м�Ů�Ĺ������������ݻ��ӷѣ���Щ�ƶȺͷ�ϰ���ı䣬��Ů����ֻ�ܳ��ڳ�����ȥ��������ijһ����ܽ���ģ�Ҳ���ǿ�������������Ч�ġ�����䣬÷������ȷ��ָ������Ů���Ƿ����ܽ�������Ϊ����������ʳ�����������£����ĸ���ܱ����ӡ���������ɽ���ļ�����ʮһ��������������Ϊ�˾��õ�Ե�ʶ���Ů������ijЩ����ֻ�����Ķ��ر������������⡣����÷������û������ȱ���������ֻ���ڽ�����Ӥ���ϴ����⡣�ðɣ����ھ�����������취����������
��������������Ӥ�á����Ļ�֮��ȼû������ǴӾ���������ƶ�ˣ���������ŮӤ�������Ӥ�����Ľ���������س��������ݡ�������ͨ�ݡ����ˡ����ݡ����ݵȾ��á��Ļ�����ĵ��������������־������ʮ����������ʮ���꣨1706��������ʷ����ԭ������Ů���أ������ʡ������Ӥ�ã����Թ���ʡ����õ��������������������ijа죨����ʥ��ʵ¼���������ģ�����һ�����ٽ��˵ط��ٶԽ�����Ӥ�õ����顣�������عٺ͵ط���ʿ��ϣ���Ǯ����������ֹ�����ѣ���Ϊ��Ӥ�õĹ̶��ʲ����Ӷ�����������������Ӥ�ö������ʿ�������ط��ټල���簲�ջ�����Ӥ�ã�����Ǭ¡ʮһ�꣨1745����Ѳ����˼鰡�����֪��������֪�س¼��Ǿ��ļ�������ڵ�����꣨1822���ɲ���ʹ�����Ⱦ�����������ؼ���������Ⱦ�Ǯ������Ϣ����ʼʱ����ʿ�����¡������ɺ����þ��ܣ����⡶������־����ʮ���������ص���Ӥ�ã�����ʿΪ���ã���ԱΪ���¡������������Ѻ�־�塷��ʮ�ߣ�����������
����������Ӥ�ñ�����������⣬�������Ǯ��ծȡ����ǰ��������Ӥ��ÿ�����Ϣ��3700�������263ʯ�����Ӥ��ʼ���ڼ��죬��ͬ��ĩ������1400��Ķ�����չ�11��8000�Ǯ6484ǧ�ģ���������ʮ���꣨1903������ҵ������1868Ķ��ɽ210Ķ����52Ķ�����������־����������������Ů���أ�Ȼ����Ӥ�õĹ�ģ������Ƽ���س���Ӥ�ã�ÿ��������400ʯ����ʥ�硢������������緻������Ӥ�ã��յ��⡣����ͬ�μ�Ʋ���ʧ������Ӥ��ֻʣ�����䡢��ʮ��Ķ��ͬ�Ρ�Ƽ����־�����������Ʋ����٣������ã���������������£���������ǿ�������Ļᡣ������¹涨���������ɷݣ��������Ϲ���ÿ��ÿ�½�Ǯ���ģ�100�ɿɵ�600�ģ��Ը�����ƶ����Ů֮�ҡ���������
����������Ӥ�����й������߸���ŮӤ�İ취���е��ñ��з��ᣬ����Ӥ�������ã����鸾ι�����еİ�ŮӤ�����鸾���ؼҸ��������·�������ѡ���������������·������ɽ�����Ӥ�ð�ŮӤ���ڵ軧�Ҹ���������Ǯ�ף�������ÿ�³���������ӡ���˳½���ڡ��ɽ���衷��ӽ������������
��������ˮ��ͤ�����ÿ����������Ż��麢����������
���������ǵóǶ������ӣ���ũ�µ�����������������
����������Ӥ���ڸ������������ɾȻ���һЩ��Ӥ�����˺��¡����Ǹ�����Ӥ�����ž�����Դ���ȶ�����Լ������ʱ��ʱû������һ���֣������ͣͣ��������һЩ�ط�����꼻�һ�֡���ʹ�ڿ����ڼ䣬���������ѣ������ڶ��ƶ���˼ҵ�������ŮӤ������ҲԶԶ����������Ҫ��������������ͳ���ߡ����С������������ĵ��������ܽ����Ӥ��������⡣��������һ������Ů֮���������С����ǣ���Ӥ������������ҵ��һ�֣��Ա�����ᱣ����ҵ�Ĵ�ͳ�����ԣ���Ӥ�õ������������ǰ����һ�ֱ��֡�
��̬��Ӱ��������14�ڡ�����ʳ�������˵ķ�����ĸ
�������������ɷ������ǵ����Ĵʻ㡣�ǵ�������ʮ�����ũ��ɲ����������磬��ũ��ҳԷ�������Ʊ��һ��Ǯ�����������ɷ�������ȥ��ũ���ཫ���˵������ˣ�������Щ�óԵġ�������˵�ij��ɷ�����һ���£�ϵָ���ʧȥ�Ͷ��������길ĸ���ֻ����Ѿ��ֿ�����Ķ����Ǽ���Է������ϣ���ʱ�˰����������ķ�����������ʳ������������
�����������ٶ���ǰ��1683�꣨������ʮ���꣩�����ճ����أ������Ϻ��У���λ�����������99�꣬�������ӽ�����С���꣬����˵���ǰ��������������ĸ����ӣ�����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