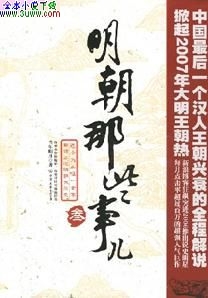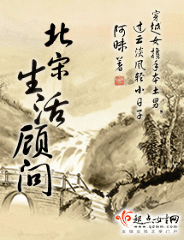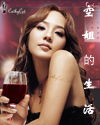�������峯������-��31����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Ӻ������������֪�丸ĸ���ϣ�Ϊ����Т��֮Ը��������Ϊֱ����ƽ֪����ɽ�������˼ֱ�����������֪�ݣ��������������Ƶ����翴����ĸ��Ӻ���������������ʹ���ĸ��Ƥ�¡��㶫������⾼��ĸ�����ϡ��Ӻ�����شͲʶк����顰�����֡������ʹͣ����й�����Т֮�⡣��������
��������Ӻ����������Ƭ�������������������Լ�¼�����Ӽ���Ա��ӡ�����硰�ԲԶ��ġ�����̫���������ˡ���������Щ�����������������ˡ������ƺ�Щ����������������ģ����ˡ����������ٲع�����������Щ�ġ��������Զ����ӡ����������ӡ�����Ѿͷ�ǣ��ƣ���һ���ˡ����������ٱ���Щ������һ����������������Щ�������ƴ���������������һ��֮�������������������ˣ�Ǭ�幬�����������ˡ������Լ������Ӹ�����������С�����̸����������ģ����棬�dz���Ҳ���������ƻ��ˡ�����ֻ�ָ��ٲ�Щ�������ø��ࡱ�������Ե���ͷ�ӡ�������С���ģ�������ª�����ȵȡ���Щ���ڻʵ۵���������Ƽ�����Լ�����������Щ��ʽ�����������У��ʵ۰������ѵ��������ׯ�أ�������ţ����ݵ������ϵ���ʥ�����ַ��ľ�����ɫ����������ȴ�����������е������Ƥ����������Ѷ��˵Ŀ������ӳ��ࡢ�������Ը����������������������ֳ�����ľ�����һ��ͨ��������ˣ���Ѫ��������е��ˣ���һ���ˣ�����������֮��Ĺ����ν�������ӣ�����������
����������֮����������еĴ��˽��P����������Dz�֣����ֳ�Ӻ���۷��˵�һ�棬����Ҳ�����ԣ�Ҳ���������顢�������飬��֪���飬����һ���̶������س���֮�飬��������˵Ӻ������Ȼ�����Ͽᣬ��Ҳ������ζ��һ�档
����Ȥ����3�ڡ�Ӻ�������ʿ��ʿ��
��������Ӻ�������̹�ϵ���У�ǰ��˵�����������������Ķࣻ�����͵���Ҳ���йϸ�Ȼ�����߽��٣���������һ������������
��������������ʮ���꣨1716�����죬��ʱ����Ӻ������ط�G�ӵ������˴��������������д������������·������ɽʱ������һ����ʿ�����о����֣���֮��̸���������棬ٹū������ϸϸ��֪������Щ��һ���˿�����������Ļ���ȴʹط�G�����һ���˷ܼ���������Ȥ���������������ʴ��죺������������˵֮�������ϸϸд��������������������˵��������ʿ��ʱ���������ӵ�ǰ����Σ���ʿ��˵��������һ��������������������˵��ϸ���εȽ�������ʱ�������档ط�G���ź��쳣���ˣ����������������������˵��ˣ�����컯�������ѵ�ʿ�������ˣ�����֪�Ⱦ��������˵Ļ�������Ԥ���˵�δ�������������˽�������Ȼ�Ǹ����������컯�����ˡ�����˵ط�G�ǡ�������������˵ط�G���뿪Ӻ������ۡ�����ɾ��壬������ڣ���Ϊ�������ϵĻʵۡ�ط�G�ڻ���֮�࣬Ҳ���е㲻���㣬���Ǵ���û�аѵ�ʿ�Ļ��꾡д������������֪���������Ȳ��ô���ؾ�������������������˵�Ļ���ϸϸд������ط�G������ɽ��ʿ�Ļ�����˹��ġ����ӣ�������Ϊ�С������������ݡ�����ǵ�ʱط�G����Ƕ���ע���£�ط�G�İ˵��ʶT�ھ��У��������������¿��࣬�ŷ�����ǡ����ࡱ���ؽ������������ط�G����һ���ܸܵ�Զ������������ǰ�����������������ĵ�˵������Ԫ�䵱Ȩ�����ԣ��������о���֮�𡣡����������̾�����Ե����ϣ���г�һ��Ӧ����ʿ�Ļ��ǻ��ƹ¡����ǵĸ��ʿ�������Ϊ�������ǽ����ʶT��գ��������������ʶTҲ������˲��ǡ��ɼ����������Ƿ������Ϊ�����������ɽ��ʿ�Ļ����Dz���������Ҳ������й©��ȥ����ڿ������Ĵ�λ֮���У������ĵ�ʿ��û�г������ף�Ҳ���˻����ǵ�ı����ʿ����������
���������й���һ��ʷ��������һ��Ӻ��������ĸ��ط����������ͣ������Գ��˺ü��ݡ��������£������ķ���������ƺ�ҽ���������������֮�ˣ����ʿ����֮��ʿ�ҡ�����Ե�õ�ʱ����ί�������������ִӷ��ã�������֮���ơ���������ң�һ�����ţ�һ�������Ŵ��������ǣ������ô�������������֮������Ԥ������֮��������ͷ��ˣ������Ҳ������������֮������������ʡ֮�ˣ����ٽ����������������ţ����ٴ��ö����ò飬������Ϊ���Ĵ��¡��������ʹ�ã��Է����⡣����Ϊ֮����������
���������������û�������£�ȻӺ�����꣨1730�����������ز���������ʹ�Լ��Ϊ�˶����������������ҽ������������������ʿ��ʿ����Ӻ�����ٽ�Ե���������ɥ������ʿ��ԭ�Ǿ����������ĵ���ʥ�ذ��ƹ۵ĵ�ʿ��������������Ϊ������ͨҽ�����������������֡�Ӻ�����ټ��е�����թ��ʵ���ʹ�ȥ�ˡ���������
����������ʿ�������˼����ϣ������������㽭�ܶ�����Ľ��������Ϊִ��Ӻ���۵����ͣ��ٴΰ����Ƽ�������Ӻ�������Ӷ��ܶ����ľ�����ʿ���͵�������ʿ����ʼ��Ӻ�����β����������֣���Ч���ߡ�Ӻ����ʮ�ָ��ˣ����ָ��購�ơ������ܶ�����̩��˵������Υ�ͣ��ʵ����˼�ʿ��������Ч�����ֵ�ʿ�ɱ���������ˣ�һ��Ϊ�ܳ��ŵ����ˣ����۶����ٱ�����֪���¼�ʵ�ͻȻ�����������ʮ�¼��д�ն��������Ҳ��ͷ���������ô�����أ�ԭ����һ�죬�ֵ�ʿ��Ӻ�����β���һ�����ְ�Ħ��һ����о��䣬ֻ�������������������֣����������ʹ����Ӻ�����������Ȼ��ŭ�����룺���������Ļʵۣ�����������Ľ��ӣ��������������o����һ������ĵ�ʿ����ȻҪ����������ڲ����ⲻ�������������㲻���Ǵ��治�ҵķ����𣡵�ȻҪ����ն�ˡ���ʵӺ���۵���ŭ������������Ϊ��ʿ�����β���Ŀ���ڲ��ݻʵ۵Ľ��������������Ҳ�����벻�����������ֲ�����������ܳ��䷶Χ�ߡ�����ʿ�����˱��ӵ�Ҳ���ҿ����ֿ��ƻʵ����彡������Ц������Ӻ�����β�����ȻҪ�߾�ȫ�����ʵ���������������Ӻ���۵ĸо�Ҳ���Ƿ��������ġ���������Ǽ�ʿ���ۺ�ʹ�ô���������Ħ����������Ӻ���ۡ�������
�����������ƣ��������������ã���Ӻ����ʱ������Ч����ʱ��ʧ���������Ϊ�����������念������ʿ���С����ְ�Ħ֮����������ʩ�а�Ħ����ͬʱ�����о��䡱��װ��Ū�����ԡ�����Ϊ�ʵ��Ƽ�����������Ҳ���ܻ��������������ʵ۷�������Ħ������䣬�յ��ʵ۽���˯��״̬���Ա�õ���Ϣ����Ħ����������������ʩ����Ч��Σ�Ҫ��ʩ���˵Ĺ�����������Ҫ��ʩ���ߵ���ϣ���Ϊ��ʩ���ߵ������������;���״̬ͬ��Ӱ������Ч������������
����������������ʿ�������е㹦���������ޣ����Ӻ��ϳ�����ʱ��Ӻ���۶����������ߣ�������ϵúã������Щ��Ч�����������ã���װ��Ū����ƭ�ʵۣ�ΪӺ����ʶ�ƣ�Ҫ�������������ֵ�ʿδ���Լ���������Ȼ�㲻��ʲô���ˣ�Ӻ���۴�ˣ������ϲŭ����Ҳ���Ǻ��֮�����ֵ�ʿ���������������ϡ������黢�������衣��������
��������
����Ȥ����4�ڡ�Ǭ¡�۵ĺ�ʤ�Ը�1��
����������һ����Ȥ����ʷ����Ӻ���ۡ�Ǭ¡�۸�������֮ʱ���������ָ����ʮ�������ָ��Ӻ���۵���ı������ĸ��߱�֡����ܡ�̰�ơ���ɱ����ơ���ɫ�����ҡ��������������ʵ۵��ļ�������Ӻ���۰䷢�ġ��������¼�����Ա��棨���������¼���������й����Ժ��ʷ����ʷ�о��ұࡶ��ʷ���ϡ���4������Ǭ¡�۵ǻ������������¼����Ϊ�����飬���������������������ǡ��岻�ɽ⡢ʮ������������ٽ蹤����������Ƶ�����д����ν����塱��Ǭ¡����ʮ���꣨1751��������������������棬�����ֻ��֪������������״����Ѳ��ɱ��ګ�ա�ͬ�������ѻʵ���ʮ����״��һ���ǹ�����һ�������٣��ڴ������ǿ��������ʵ����������̬����ͬ������������Ըض����в�ͬ�����ξٴ룬������������Ȥ����Ǭ¡�ۼ�λ֮�������£����ɴ˿���Ǭ¡�۵�����������Ը�������
��������Ǭ¡�������������ı�Ӻ���������ξ����Ļ�������ߣ���νȥ������ʩ��������̰ͣ�ٵ��⣬���÷�Ա��Ϊ���η����������ij�̶ֳȵ�ƽ�����������ѻġ���·��ʰ�ż������𣬵��еij������Ե����飬�����ֿ϶��ˣ���ij��������˵�������ڷ�ǰ���İ���ֻ���ƶ��Ե�����δ��������Ǭ¡����ʩ�п�����õķ���Ϳ�ƽ���ߣ����ַ������ߵIJ���������Ǭ¡�۸��Կ�������֮�⣬���ڻ������ʱ�����γɵģ������ܿ����۵Ŀ���˼��Ѭ�գ�����Ӻ�����������ε�ijЩ����Ӱ�죬�Լ�����ı���������������������������˵�Ȩ�������¡���������
��������������������Ǭ¡�ۿ����������˼�����������ں���Ǭ¡�ۼ�λ�ĵ�����䲼���лʵ���گ������������������Ȼ�е���Ӻ������Ը���е�����Ǭ¡�۵�Ը����������һ����Ӧ����Ǭ¡�۵��������������
�������������̷�����֮�裬����ڵ���������̰��а���Զ˷��ף�����ٷ���Ҳ��Ȼ����֮�ã��ֱ������ʱ����ǰ�����齽��������Ӫ˽����ϰ�ɷ磬��֪ʡ�ģ��Ʋ��ò������������Խ佫���������Ĺ�֪�����ӣ���������ǰ֮�������������״����ߣ������Կ��ø����£����ޱ���Ҳ��������˵��£����ټ����ã�����Ӧ�����ߣ����վ����С�����������ʵ¼����һ��ţ�ʮ������¼����л����1985��Ӱӡ������������
��������Ǭ¡�۽���Ӻ���۵����壬����������������µĿ��Ͻ���ʹ�����⣬������ʾ���ϴӿ�����һ�����º��ټ�����������������������õ�ʩ�����룺��������
��������������֮����������У��ʿ����֮���ͣ������֮�Կ��������ǡ���һ��һ�ڣ�Ϊ����֮����������Э���У��ǿ��Խ�������Ҳ������ʥ���ʻʵۣ����ʺ�����ʮ��������Ϣ������������ѭ�����������й���֮�ס��һʿ��ܳд�ͳ�������٣������γ��壬������������֪η��Զ��������Ƚ���֮�ģ��˻ʿ�֮��ʱ���������Ե�֮�����У�������ٷ����ǻݰ�˹��֮����Ҳ���ʿ�������Ϊ���Կ������Ž̽�֮��������ʥѵ�����þ��裬�ȵ�����֮����ʱʱ�Իʿ�֮��Ϊ�ģ����Իʿ�֮��Ϊ����Ω˼������ã�������������ƽ����ֱ֮�Ρ�������֮������������֮��ϳڣ����ƶ�ʵ��ͬ����֮��ν���ߣ������֮�˴���������֮�˻ݱ�������ν���֮����Ϥ�⣬�̷�֮���Թ��ݣ�������֮���Ե��Ķ�����Ҳ���۽������������������г�������֮��������������ģ����������������������Ү�����������ģ��������ÿ�֮�������ӡ���������ϰ�վã�����������ԣ�����ϳڣ������в��ò���֮�ơ��˲�Ω����֮���ң���������֮���ң�������֮�����ӡ����������ʵ¼�����ģ�Ӻ��ʮ����ʮ�¼�������
����Ȥ����4�ڡ�Ǭ¡�۵ĺ�ʤ�Ը�2��
���������˺�Ǭ¡�۲�������������õ�ʩ����������������ּ�����εĽ�������֪Ǭ¡�۵Ŀ�����á�������õ��ں����ڣ���������
����������1����ʱ���ˣ�����ǰ��ĩ�����µıˡ���������
������������ĩ�꣬������Ϣ�����ֿ���֮�ף�����Ӻ���ۼ�λ���ò�ʵ�����ͷ��룬���������������ֲ����Ͼ�֮�ף�����Ҫ�����Ը�����Ǭ¡�۵�����ֻ���ÿ��ʷ���ȡ������֮����Ӻ������������Ǭ¡�����ݾ�Ϊ����ʹȻ�����ǵ����������ȡ�ģ����dz��Ե����߸��˵ĺö�����Ǭ¡���Ŵ�˵����ʵ�п������ߣ�����������ϳڣ����ͻᱻ�Ȳ�ȡ�Ͼ����룬ϣ������ͬ����ϣ����÷ϳھ���ij��֡��ɴ˿�֪����ν������ã��������������ֱˣ����á������������ȣ���������������ë�������ԡ���������ƫ������ַ������⣬ֻ�ø��С���������������ʱ���˵�����˼�롣���ϡ����Ǻ��£��Dz����Ѷ���֮������Ҫ�ߵ������ݡ������ι���ϡ���������
����������2��ִ�����У�ǿ����ӹ��г����������
����������������֮���������䡮�С�������һ��Ļ���Ǭ¡�۲�֪���ظ��˶��ٱ顣��λ��ʮ���죬��Ӻ�����ⶨ�ֺţ������˸������С���ڡ�Ӻ��ʮ���꣨1735��ʮ����Ǭ¡��˵����������֮�ųڣ�����֮����Ω�ֲ���Э����������֮�ء���ͬ����˵���������ʿ�ʥѵ������ƽ֮�������¡������������ʵ¼�����ţ�Ǭ¡Ԫ����������������������ε�����á��С����������ɹ�������������֮�£���һ��������һ��������֮�飬�����ã�������ƫ�����ԡ��е������ѡ������������ʵ¼����ʮ����ͬ��ѵ�������������֮�¡������ʺ����С������µ��Բ��ۣ���ִ�����ڹ�ʿ������Ω�η�Ī��������Ң˴�ഫ֮�ķ���Ω����ִ���С����������з��Σ���ʥ�ഫ��Ȼ���С����壬��ʱ���ã����¶�ʩ�����������ʼ��У��ʷǿ�Ҳ�����������弴�У������Ҳ�������ʶ�ʧ�ڿ��������ʧ���ϣ������Ҳ���ε���ʹ֮��Э����Ү�������������ʵ¼����ʮ���������������͵����Ǭ¡�۵���˼��ʵ����ӹ֮����ִ�����Σ�����������ã�������������ַϳڵ��������϶����������ײ�������ƫ��һ����Ӧ����ֹ�������εķ���������Ĺؼ����ҵ����еķ����������ã�������㣣�ʩ������Ҳ���������������������Щִ�е�����ͬʱ�����Ÿ�볼��������ʵ�п��������з��ݵ���ͷ�����ܲ����Ծ��衣����˵��ʩ�А���������ã����¡���������ּ�������ڷϳ�֮�⣬���̾��ɡ����������ʵ¼����ʮ�������ÿ����ϻ�����ϣ������Ǹ��ѿ�����ƫ��һ�ߡ�Ԫ��������������������������俪ʼðͷ�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