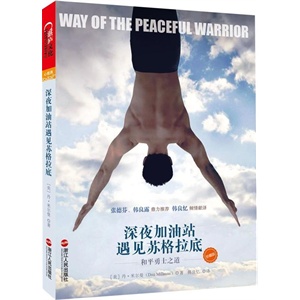深夜加油站遇见苏格拉底-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大二结束时,我已代表美国体操联盟到过德国、法国与英国,赢得了世界蹦床锦标赛。 参加蹦床赛所得到的奖杯在房间一角越堆越多,我的照片经常被登在《加州日报》上。由于太常出现了,开始有人认出我来,我越来越有名,走在路上,常有女性对我微笑。我有位可人的女性朋友,叫苏西,她总是那么温柔可爱,留着短短的金发,微笑的时候会露出一口洁白的贝齿,她常来找我,对我颇有好感。就连我的学业也十分顺利无碍,这一切的一切都让我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世界的顶端。
然而,当我升上了三年级,也就是1966年的初秋,有种阴暗又无以名状的事物开始成形。那时我已搬出宿舍,独居在房东家后面的独立小套房。在这段日子里,尽管事事依旧如意,我却越来越忧郁。不久之后,梦魇迅速袭来,我差不多每晚都会惊醒,浑身冒冷汗,而梦境几乎一模一样:
我走在市区一条漆黑的路上,重重的黑暗迷雾中,没有门也没有窗的高大建筑物阴森森地向我迫近。
一个全身罩着黑斗篷的庞大身影,冲着我大步走来。我看不见它,只是感觉有个叫人不寒而栗的幽灵,一个发亮的白色头骨,黑色的眼窝紧紧盯着我。周遭一片沉寂,流露出死亡气息。它灰白的指骨伸向我,关节弯曲,仿佛一只爪子正在对我招手。我浑身僵硬。
一个白发男人从那罩着斗篷的恐怖形体后方出现,神态从容镇静,脸上没有丝毫皱纹。他走起路来无声无息,不知为何,我直觉到只有他能助我脱逃,他有能力救我,可是他看不见我,我又无法出声呼喊他。
披着黑斗篷的死神嘲笑我的恐惧,倏地转过身去,面对那白发男人,谁知后者竟冲着死神哈哈大笑。我吓呆了,愣愣地瞧着。死神气得伸手去抓他,可忽然,它又转而冲向我,但老人瞬间抓住它的斗篷,将它猛地向风中一抛。
死神突然消失无踪。白发男人看着我,展臂做出欢迎的姿势。我走向他,然后直接进入他的躯体,和他融为一体。我低头看着自己,看到自己一袭黑袍,我举起双手,看见泛白的骨头合在一起,做出祈祷的手势。
我醒来,大口大口喘气。
当晚,我躺在床上,听着风声穿过公寓窗户的小缝隙肆意咆哮。我辗转难眠,索性起床,套上褪色的牛仔裤、T恤、球鞋和羽绒外套,走进夜色中。那时正是凌晨3:05。
我漫无目的地走着,深深吸进潮湿清冷的空气,抬头仰望星光闪烁的夜空,倾听寂静的街道上稀疏传来的声响。寒冷使我肚子饿了起来,因此我走向一个24小时营业的加油站,想买些饼干和饮料。我双手插在口袋里,匆匆穿越校园,经过沉入梦乡的房子,来到灯火通明的加油站。举目望去,四下尽是已经打烊的餐馆、商店和电影院,阴暗、凄凉,在这黑暗的荒野中,加油站俨然就像萤光绿洲。
我绕过加油站附设的修车房的角落,差点撞上坐在阴影中的一个男人,他的椅背就靠在加油站的红色瓷砖墙壁上。我吓了一跳,往后退了两步。他戴着一顶红色羊毛软帽,穿灰色的灯芯绒裤、白袜和日式夹脚凉鞋,身上披了件轻便的防风外套,看起来挺舒服的样子,可是他脑袋旁那墙壁上的温度计却显示:摄氏四度不到。
他并没有抬头,只是以近乎歌唱似的低沉嗓音说:“如果我吓到了你,对不起啊。”
“喔,呃,没关系。这里有没有汽水(soda pop)卖?”
“只有果汁。还有,别叫我‘老爹’(pop)!”他转过身,冲着我,脸上半露微笑,然后脱下帽子,露出一头银得发亮的华发。接着他哈哈大笑起来。
那笑声!我愣愣地瞪着他好一会儿,他就是我梦中的老人!那白发,那清爽没有皱纹的脸庞。他长得又瘦又高,看起来五六十岁的样子。他再次大笑,我感到茫然,不知怎地,竞走向那扇标识着“办公室”的门,推开走人。除了这扇办公室门,我觉得仿佛还存在着另外一扇门可以通往另一个空间。我跌坐在一张旧沙发上,浑身颤栗:心里想着,待会儿搞不好会有什么东西尖叫着破门而人,闯进我秩序井然的世界。我心里又是害怕,又有点着迷,一种我无法理解的怪异感觉。我坐在那儿,呼吸短而急促,试图重返正常的世界。
我环顾四周,这办公室被布置得和一般感觉乏味、凌乱的加油站迥然不同。我身下的沙发铺着一条褪色的墨西哥彩色毛毯,左侧靠人口处放了一只箱子,里头整齐地摆着旅行辅助用品,地图、保险丝、太阳镜等。在一张深咖啡色胡桃木小书桌后面,有一把用褐色灯芯绒布铺面的椅子,一台饮水机看守着一扇标示着“非请莫入”的门。离我较近的地方,另有一扇门,通往修车房。
这屋里洋溢着居家的温馨气息,博取了我的好感。地板上铺着明黄色的绒毛地毯,一直延伸至门口那块迎宾踏毯前面;墙壁新近才刷了白漆,几幅风景画增添了几分色彩。柔和的灯光使我的情绪镇定下来,这里和外头刺眼的萤光形成对比,让人心情放松。整体来说,这房间有种温暖、井然有序又安全的感觉。
我哪里料想得到这地方将为我带来不可预测的历险、魔法、恐怖和浪漫呢?当时我心里只顾着嘀咕,这里如果装上个壁炉,倒也挺适合的。
不久,我的呼吸慢慢舒缓下来,我的内心就算对眼前一切不尽满意,也不再是乱纷纷的一团糟。白发男人长得像我梦中的那个男人,当然只是纯属巧合。我叹口气,站起来,拉上外套拉链,迈步走进冷冽的空气中。
他依然坐在原地。我经过他身旁时,迅速地偷看他最后一眼,而他亮晶晶的眼神引起我的注意。我从未见过这样一双眸子,乍看之下,眼中似乎噙着泪水,就要夺眶而出。接着,泪水却开始闪烁发亮,就好像倒映着满天星光。我更加被吸引,直到星星变成只是他眼里的反光。有那么一瞬间,我迷失了,除了那一对眼睛,我什么也看不到,那是一双如同婴儿一般顽强又好奇的眼睛。
我不知道自己在那儿站了多久,可能是几秒,也可能是几分钟——说不定更久。我突然惊觉自己身在何处,喃喃道了晚安,随即脚步凌乱地匆匆走向街角。
我走到路边,停下来,脖子一阵刺痛,我感觉得到他正在注视我。我回头看,顶多才过了15秒吧,他却已经站在屋顶上,双手交叉抱胸,仰望星空。我目瞪口呆,看了看仍靠在墙上的那把空椅子,再抬头往上瞧。这是不可能的事!就算他替一辆由大老鼠驾驶的大南瓜车换轮胎,也不会比此情此景更令我瞠目结舌。
在寂静的夜里,我抬头瞪着那个清瘦的身影,虽然隔了段距离,他看来依旧气度不凡。我听见星星在吟唱,仿佛风中的铃声。他忽然转过头来,直视我的眼睛,我们之间相隔约二十米,可是我几乎能感觉到他呼吸的热气吹在我脸上。我打着哆嗦,不是因为寒冷,而是那扇通往现实和梦境相互交织的门再度被打开了。
我抬头看他。
“什么事?”他说,“我能帮你吗?”简直就是先知的口吻!
“很抱歉打扰你,不过……”
“我原谅你。”他微微一笑。我脸上一阵燥热,有点不高兴。他在跟我玩游戏,我却不知道规则。
“好,你是怎么上到屋顶的?”
“上到屋顶?”他问,一副无辜又大惑不解的样子。
“对,你是怎么从那把椅子……”我指指椅子,“在不到20秒内,跑到屋顶上?你本来是靠墙坐着,就在那儿。我转身,走到转角处,然后你就……”
“我在做什么,我知道得一清二楚,”他拉大嗓门说,“用不着你来告诉我。问题在于,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吗?”
“我当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厂我开始冒火了,我又不是小孩,犯不着听他教训!可是我实在太想搞清楚这老头耍的花招,只得克制住心头的怒火,保持礼貌地问:“先生,请告诉我,你是怎么上到屋顶的?”
他却不发一语,只是低头看着我,直到我后颈开始感到刺痛。最后,他总算回答:“用梯子,就在后面。”然后就不再理我,兀自凝望天空。
我慢慢走到屋子后面,果然有把旧梯子斜靠在后墙上,可是梯顶离屋顶边缘起码还有一米多,就算他真的用了梯子——这一点还十分令人怀疑——也没办法说明他如何在几秒内上到那儿。
黑暗中,有什么落在我的肩头,我惊喘了一口气,倏地转身,看到他的手。神不知鬼不觉间,他竟已下了屋顶,偷偷接近我。此时我脑中浮现惟一可能的答案:他有孪生兄弟,他们显然爱耍这招,把无辜的客人吓个半死。我立刻开口责备他:
“好了,老兄,你的孪生兄弟在哪儿?我可不是笨蛋。”
他轻轻蹙了蹙眉头,接着放声大笑。哈!可给我逮到了,我拆穿了他的诡计,可是接下来他的回答又让我不是那么有把握了。
“我要是有孪生兄弟,何必浪费时间站在这里,跟一个‘不是笨蛋’讲话?”他再次哈哈大笑,大步向修车房走去,留我一人站在原地,哑口无言。我简直不敢相信世上竟有脸皮这么厚的人。
我连忙跟过去,他走进修车房,在一辆绿色的老福特货车的车盖下修理化油器。“那么,你以为我是个笨蛋了?”我说,语调比我原本打算的更带有火药味。
“我们全是笨蛋,”他回答,“只不过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知道,你好像是后者。麻烦你把那把小扳手拿给我好吗?”
我把那把该死的扳手拿给他,准备跨步离开。可是在走以前,我必须知道答案:“请你告诉我,你是怎么那么快就上到屋顶去的?我真的很好奇。”
他把扳手递回来给我,说:“这世界本来就叫人猜不透,用不着想太多。”他指指我身后的架子:“我现在需要锤子和改锥,就在那儿。”
我没辙了,无奈地盯着他一分钟,绞尽脑汁想让他告诉我我想知道的事情,可是他似乎忘了我这个人。
正当我完全死心,走向门口时,却听到他说:“别急着走,做点事吧。”他卸下化油器,动作娴巧得有如一位正在进行心脏移植手术的外科医生。他小心翼翼地把化油器放下,转身面对着我。“来,”他边说边把化油器交给我, “把这个拆开,零件放进那个罐子里泡着,这样你就不会老想你的问题了。”
无奈感逐渐变成笑意,这老头或许有点惹人厌,可也挺有意思。我决定要表现得随和一点。
“我叫丹,”我边说边伸出手要和他握手,脸上堆满不怎么真诚的微笑,“你呢?”
他把改锥放在我伸出去的手里。“我叫什么并不重要,你的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名字以外和问题以外的东西。好,你现在需要用这把改锥来拆开那个化油器。”他指着化油器。
“在问题之外并没有什么东西。”我反驳,“问题是,你是怎么飞上那屋顶的?”
“我并没有飞,我是跳上去的。”他板着脸回答,“那不是魔术,所以别离兴得太早。不过呢,因为你的缘故,我说不定得变一个很难的魔术,譬如把一头笨驴变成人。”
“你以为你是谁啊?”
“我是个勇士!”他厉声说,“除此之外,我是谁,取决于你想要我当谁。”
“你就不能直截了当回答问题吗?”我狠狠敲着化油器泄愤。
“你就问一个吧,我尽量回答。”他说,脸上挂着无辜的笑容。改锥滑落,刮伤了我的手指。“可恶!”我一面嚷,一面走到水槽边清洗伤口。他递给我一片创可贴。
“好吧,这里有个直截了当的问题,”我决心不露出厌烦的声音,“你怎么可能帮得了我?”
“我已经帮了。”他指指我手指上的创可贴,回答说。
我再也受不了了,“听好,我不能再把时间浪费在这个鬼地方了,我需要回去睡一会儿。”我放下化油器,准备离开。
“你怎么知道你不是一直都在沉睡?你怎么知道你此时此刻不是在睡觉?”他说,带着热切的眼神注视着我。
“随便你,”我累得不想争辩,“不过,还有件事。我走之前拜托告诉我,你是怎么表演那手特技的,你知道,就是在……”
“明天,丹,明天。”他打断我的话,露出温暖的微笑,霎时我所有的恐惧和无奈都消逝无踪。他伸出手,紧握我贴着创可贴的手。我的手、我的臂、我的整个身体瞬间感到一阵刺痛。他又补上一句:“很高兴再次见到你。”
“你说‘再次’是什么意思?”我脱口而出,接着又勉强按下这股冲动,“我明白,明天,明天。”我们俩都笑了起来。我走到门口,停下,转身,看着他,然后说:“再见,苏格拉底。”
他露出困惑的表情,接着耸耸肩,一副悉听尊便的样子。我想,他应该也喜欢这名字,接着我便离开,没再说任何一句话。
第二天早上我睡过了头,没去上8:00的课,直到下午体操训练开始前才醒来,准备好去练习。
我和瑞克、席德还有其他队友,先在看台的阶梯跑上跑下,接着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地躺在地板上,做腿部、肩膀和背部的伸展运动。通常在做这个运动时,我都一语不发,今天却突然很想和他们说说昨晚发生的一切,我本来打算一吐为快,然而想了半天,却只能够说出一句:
“昨天晚上,我在加油站认识一个很不寻常的家伙。”
不过显然,他们比较在意伸展腿部时的疼痛感,不怎么关心我的芝麻小事。
我们做俯卧撑、仰卧起坐和举腿动作,很快就热好身,开始做一连串的翻滚动作。我在单杠上旋转身体,在鞍马上做正反交叉,并苦练新加进来的一项绷紧肌肉的吊环动作。我一次又一次地在空中飞跃,一面飞,一面在心里纳闷,我称为苏格拉底的那个男人怎会有那么神奇的本领。我心中有个忐忑不安的声音,劝我离他远远的。然而,我打定主意非摸清楚这谜样人物的底细不可。
吃过晚饭,我匆匆温习过历史和心理学作业,写好英文报告的草稿,然后就冲出公寓,当时正是晚上11:00。我越接近加油站,心里越觉得七上八下,他真的想再见到我吗?我该说什么才能让他刮目相看,让他知道我是个聪明人?
他在那儿,站在门口,微微欠身,手挥了挥,欢迎我进他的办公室。“请脱鞋,我这里一向如此。”
我在沙发上坐下,把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