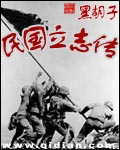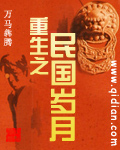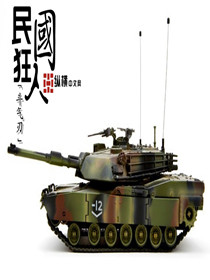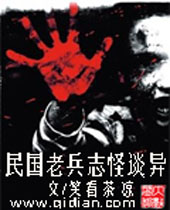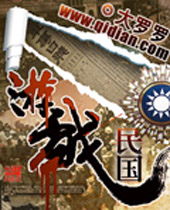民国背影:政学两界人和事 作者: 张耀杰-第3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易卜生主义》的第三部分里,胡适介绍了易卜生戏剧中的三大社会势 力,一是法律,二是宗教,三是道德。在第四部分里,他通过对于《国民公敌》的 介绍,说明了易卜生笔下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最爱专制,往往用强力 摧残人的个性,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一切维新革命,都是少数人发起 的,大多数人总是守旧、麻木不仁的,只有极少数人^有时只有一个人, ^不满意于社会的现状想要维新、想要革命。”
《国民公敌》中的男主角斯铎曼医生最早发现当地的温泉具有疗养的功 效。当地人觉得有利可图,便筹集资金建造浴池,吸引各地游客来到这里避暑 养病,还聘请斯铎曼担任负责卫生监督的官员。随着游客增多,当地的经济开 始繁荣,洗浴的人中间却出现了一种流行病。斯铎曼从浴池里取出水样,寄给 大学的化学试验室,化验结果表明,是他的岳父经营的皮革厂污染了水源,又 由于浴池里的水管安得太低,从而导致浴池里产生了有害病菌。斯铎曼向市 长和浴场主提交报告,建议对浴池进行重新改造。考虑到改造浴池要花费很 多资金,并且要歇业一两年,市长和浴场主拒绝了此项建议。斯铎曼据理力 争,他费尽心机找到一个会场,当地居民不但不听从他的建议,还把他赶下台 去,然后通过表决宣布他是国民公敌。第二天,斯铎曼的市长哥哥亲自免除了 弟弟的医官职务。斯铎曼的岳父也告诉女婿说,自己留给女儿和外孙的遗产 已经全部换成浴场的股票,浴场如果破产将面临巨大损失。接下来,斯铎曼的 房东赶他搬家,他的两个儿子在学校里面先被同学围攻而后被校长停课。在 这种情况下,斯铎曼依然不肯屈服于多数人唯利是图的蛮横无理,从而说出 了剧中最为著名的一句台词:“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 ”
在第五部分里,胡适主要介绍易卜生的政治观念。易卜生起初是一个极 端反对国家观念的无政府社会主义者,在亲眼目睹巴黎公社的武装起义失败 后,他开始放弃无政府社会主义思想;从而选择了宪政民主制度。
在《易卜生主义》的第六部分,胡适正面总结了他所理解的“易卜生主
《新青年》时代的戏剧论争| 193
义”:“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易卜生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都 写出来,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会原来是如此黑暗腐败, 叫人看了觉得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一一这就是易卜生主义。表面 上看去,像是破坏的,其实完全是建设的。……他主张个人须要充分发达自己 的才性,须要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
在胡适眼里,发展每个人的“自己的个性”,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须 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娜拉的离家出走,就是 承担自己的个人责任的第一步。而易卜生的一生,就是持之以恒地呐喊呼吁 全社会要容忍鼓励包括娜拉、斯铎曼医生之类的先驱者,从而保障人类社会 中不断涌现敢于说真话的“国民公敌”。
二、胡适创作的《终身大事》
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真正富于现代意识的第一部戏剧作品是胡适创作 的《终身大事》。
1919年3月,《终身大事》刊登在由高一涵负责编辑的《新青年》6卷3号中, 胡适专门为该剧加写了一个副标题:“游戏的喜剧。”
事实上,《终身大事》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社会问题剧,剧中的女 主角田亚梅,更是中国戏剧史上第一个娜拉式的女性人物。她与易卜生笔下的 娜拉的主要差别,表现在她所反抗的并不是夫妻生活中的男权丈夫,而是宗法 制家庭中的严父慈母。这是刚刚启动现代化进程的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色。
田亚梅与陈先生是在东洋留学时相识的一对情人,两个人回国后打算征 求父母的意见正式结婚。田亚梅的母亲田太太是“不敢相信自己”的一个人, 她疼爱自己的独生女儿,希望女儿不要“糊里糊涂”地嫁给一个合不来的人,就 背着家人去观音菩萨面前求签,然后又请来一位瞎眼的算命先生。算命先生 说自己是“据命直言”的,按照命书上的说法,陈先生和田亚梅在属相上是属蛇 和属虎相克,在时间上是猪和猴相克,这两个人要是成了夫妇,就犯了夫克妻
194 I元闽货I
| ―政学两界人和事
的命,肯定不能够白头偕老。
在这种情况下,田亚梅只好把希望寄托在禁止家人拜菩萨和请算命先生 的父亲身上。她的父亲田先生回家之后,先把田太太教训了一通,接下来却说 出了反对这桩婚事的另一项理由:“两千五百年前,姓陈的和姓田的只是一 家。后来年代久了,那写做田的便认定姓田,写做陈的便认定姓陈,外面看起 来,好像是两姓,其实是一家。所以两姓的祠堂里都不准通婚。”
田先生因为害怕被革出宗族祠堂而被老先生们笑骂,竟然玩弄起孔门儒 教“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道学把戏:“要是你这位姓陈的朋友是没有钱的, 倒也罢了;不幸他又是很有钱的人家。我要把你嫁了他,那班老先生们必定说 我贪图他有钱,所以连祖宗都不顾,就把女儿卖给他了。”
田亚梅在绝望中看到女仆李妈替陈先生送来的情书,上面写着:“此事只 关系我们两人,与别人无关,你该自己决断!”于是,她当机立断写下一张字 条:“这是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应该自己决断。孩儿现在坐了陈先生的汽车 去了。暂时告辞了。”然后把字条留在桌子上匆匆离开。
《终身大事》是一部很短的独幕戏,戏中的观音菩萨是中国传统佛教的化 身,算命瞎子是中国传统道教的缩影,田太太所充当的其实是佛、道两教代言 人的角色。自以为文明新派的田先生,却偏偏是孔门儒教的代言人。田亚梅的 离家出走,一方面是她自己主宰自己命运的第一步,同时也是以现代人道反 抗儒、释、道三教合流的传统宗教神道的第一步。该剧在当年曾经引起很大 反响。1919年6月19日,北京学生联合会为了给“五四”运动筹集活动经费,邀 请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院和北京农业专科学校的新剧团,在珠市口第 一舞台举行联合公演。第一天晚上由北大学生演出《新村正》和《终身大事》; 第二天晚上由高师学生演出《波兰亡国惨》和《劫余泪》;第三天晚上由农专 学生演出《美人剑》和《笑死你》。周作人于6月17日从刘半农手中购票两张,6 月19日晚上与鲁迅一起观看了演出。鲁迅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晚与二弟同至 第一舞台观学生演剧,计《终身大事》一幕,胡适之作,《新村正》四幕,南开学 校本也,夜半归。”①
《新青年》时代的戏剧论争| 203
三、钱玄同挑起的戏剧论争
早在胡适正面提倡并且亲自创作“易卜生主义”的现代戏剧之前,钱玄同 在1917年2月25日写给陈独秀的读者来信中,已经率先挑起针对中国传统戏 曲的戏剧论争:“返观中国之小说戏剧,与欧洲殆不可同年而语。……若今之 京调戏,理想既无,文章又极恶劣不通,固不可因其为戏剧之故,遂谓有文学 上之价值也。……屮国戏剧,专重唱工,所唱之文句,听者本不求其解,而戏子 打脸之离奇,舞台设备之幼稚;无一足以动人情感。”
这封来信刊登于《新青年》3卷1号。在随后的3卷3号中又有胡适的《历史 的文学观念论》,其中写道:“词曲如《牡丹亭》、《桃花扇》,已不如元人杂剧之 通俗矣。然昆曲卒至废绝,而今之俗剧(吾徽之‘徽调’与今日‘京调’、‘高腔’ 皆是也〉乃起而代之。今后之戏剧或将全废唱本而归于说由,亦未可知。此亦 由文言趋于白话之一例也。”同一期中还有刘半农的长文《我之文学改良观》, 用16个字概括了传统戏曲的表演形式:“一人独唱,二人对唱,二人对打,多人 乱打。”
到了由胡适编辑的《新青年》4卷6号即“易卜生号”中,以《新文学及中国 旧戏》为标题,刊登了北大学生张厚载(镠子〉的读者来信,以及胡适、钱玄同、 刘半农、陈独秀的分别答复。张厚载在来信中写道:“记者足下:仆自读《新青 年》后,思想上获益甚多。陈、胡、钱、刘诸先生之文学改良说,翻陈出新,尤有 研究之趣味。……盖凡一事物之改革,必以渐,不以骤;改革过于偏激,反失社 会之信仰,所谓‘欲速则不达’,亦即此意。改良文学,是何等事,决无一走即到 之理。先生等皆为大学教师,实行改良文学之素志,仆佩服已非一日。但仆怀 疑之点,亦不能不为胡、沈诸先生一吐。”
张厚载的“怀疑之点”,其一是胡适和沈尹默等人的白话诗,“弃中国固有 之诗体,而一味效法西洋式的诗,是否矫枉过正? ”其二是胡适、刘半农、钱玄 同等人对于传统戏曲的相关评价;有没有体现“中国戏曲”的“真精神”?
I民因嘴炙
I ^政学两界人和事
胡适的答复是:“鏐子君以评戏见称于时,为研究通俗文学之一人,其 赞成本社改良文学之主张,固意中事。但来书所云,亦有为本社同人所不 敢苟者。”
与胡适的求同存异、与人为善截然相反,钱玄同表现出的是恶言恶语的 嬉笑怒骂:“我所谓‘离奇’者,即指此‘一定之脸谱’而言;脸而有谱,且又一 定,实在觉得离奇得很。若云‘隐寓褒贬’,则尤为可笑。……这真和张家猪肆 记卍形于猪鬣,李家马坊烙圆印于马蹄一样的办法。哈哈!此即所谓中国旧戏 之‘真精神’乎? ”
刘半农的答复与钱玄同高度一致:“平时进了戏场,每见一大伙穿脏衣服 的,盘着辫子的,打花脸的,裸上体的跳虫们,挤在台上打个不止,衬着极喧闹 的锣鼓,总觉眼花缭乱,头昏欲晕。”
陈独秀虽然不同意张厚载的观点,却也难能可贵地表现出了愿意探讨下 去的理性态度:“尊论中国剧,根本谬点,乃在纯然囿于方隅,未能旷观域外 也。……演剧与歌曲,本是二事;适之先生所主张之‘废唱而归于说白’,及足 下所谓‘绝对的不可能’,皆愿闻其详。”
在《新青年》5卷1号中,钱玄同的“随感录十八”是专门攻击传统戏曲的: “两三个月以来,北京的戏剧忽然大流行昆曲;听说这位昆曲大家叫做韩世 昌。自从他来了,于是有一班人都说,‘好了 ’中国的戏剧进步了,文艺复兴的 时期到了。’我说,这真是梦话。中国的旧戏,请问在文学上的价值,能值几个 铜子?……吾友某君常说道,‘要中国有真戏,非把中国现在的戏馆全数封闭 不可。’我说这话真是不错。……如其要中国有真戏,这真戏自然是西洋派的 戏,决不是那‘脸谱’派的戏,要不把那扮不像人的人,说不像话的话全数扫 除,尽情推翻,真戏怎样能推行呢? ”
《新青年》5卷2号另有刘半农与钱玄同的来往通信《今之所谓“评剧家”》。 钱玄同在写给刘半农的回信中,先是借胡适的话语表明自己的态度:“适之常 说一句话,叫做‘不值得一驳’,这话很有道理。我现在仔细想来,老兄今年春 天打起精神答王敬轩的信,后来为了《灵学丛志》,百年老兄与我三个人又用
《新青年》时代的戏剧论争| 197
了气力去驳斥他,实在有点‘不值得’。“
接下来,钱玄同笔锋一转,反而以极端话语表白了对于胡适“前次答张繆 子信”的不认同:“我与适之的意见却有点反对。我们做《新青年》的文章,是给 纯洁的青年看的,决不求此辈‘赞成’。……我记得十年前上海某旬报中有一 篇文章,题目叫做《尊屁篇》,文章的内容,我是忘记了。但就这题目断章取义, 实在可以概括一班‘鹦鹉派读书人’的大见识大学问。”
在中华书局出版的《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保留有胡适写给钱玄同的一封 书信:
昨日公等丑诋宋春舫君之戏谈,别后即取《公言报》读之,觉此君所言(十 九日〉全与吾辈无异,且明言歌剧之影响远不如白话剧。吾因疑第一段(十七 日〉“歌剧之势力且驾文剧而上之”一语,必有误会处,因就宋君问之,宋君言 此所谓“势力”并非丨沾!!甜?^影响〉,本意作号召听者之能力,随笔写去,不图 有此误会也。适既亲得于宋君,故不敢不告,并望与仲甫兄观之。
适意吾辈不当骂人,乱骂人实在无益于事。宋君无论如何,他总算得一个 新派人物。其人作文太粗心则有之(此乃多作日报文字之过,且少年得志太早 之过〉,然不当把他骂出我们的大门去也。老兄以为然否?
至于老兄以为若我看得起张鏐子,老兄便要脱离《新青年》,也未免太生 气了。我以为这个人也受了多做日报文字和少年得意的流毒,故我颇想挽救 他,使他转为吾辈所用。若他真不可救,我也只好听他,也决不痛骂他的。②
这封信的落款处只有四个字:“适上,廿夜。”该书编者把写作日期认定为 1919年2月20日。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胡适书信集》又把写作日期认定为1919 年的“7、8月间”。此信的实际写作时间应该是1918年的8月20日。钱玄同收信 后,给胡适写了一封没有落款日期的回信:
我对于宋春舫,原没有什么恶感;不过先头听了你和蔡先生如此的恭维
I良国噶I
I ^政学两界人和事
他’而亲见其人,却是“碌碌”得很,因此不免把尊敬他的心理消灭许多罢了。
至于张厚载,则吾期期以为他的文章实在不足以污我《新青年》〖如其通 信,却是可以〉;并且我还要奉劝老兄一句话:老兄对于中国旧戏,很可以拿他 和林琴南的文章、南社的诗一样看待。老兄的思想,我原是很佩服的。然而我 却有一点不以为然之处:即对于千年积腐的旧社会,未免太同他周旋了。平日 对外的议论,很该旗帜鲜明,不必和那些腐臭的人去周旋。老兄可知道外面骂 胡适之的人很多吗?你无论如何敷衍他们,他们还是很骂你,又何必低首下 心,去受他们的气呢?我这是对于同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