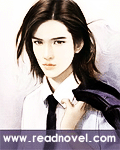���´Ҵ�-��16����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Ҹ��澯������������ֵ��ͤ�һ��������������һ���²裬���һָ���־��ʼ�����ҵ�����ȥȥ����һһ�������ǡ��������콻���������������һ��������ұ��ף����һؼҡ�
���ǵ��˳�ǬŪ�ͺ����Ľ���·�ڣ�������һ��б�¡��������ҵ���û�С���ָ�������һյ·�ƣ�˵��
�����߸˱ߵ���һ���ţ������ҵļҡ���
���˼��ſڣ�������״�����ˮ��̨���ϣ���ʼ���š�û�л�Ӧ�����������飬¥�ϲŴ����˸���������
��˭ѽ����
����ʾ���һش�
������ѽ����
�˸�˵���������죬��������ˡ���
��ĸ������������ô���Ż�����ȥ������һ���ˡ���
�˸���¥�ˣ�ľ���������¥��һֱ�õ�¥�£�����СŪ�������������������űߡ��˸��������ţ����ţ�����ס��صİ��ţ��������죬�������ɣ�
��ͬ־��������ô���£���
���ޣ���������������˵���������������״��˳�������ͷ���ӳ���ˤ�����ˡ����ǿ�������ɫ��̫�ã���Ҫ����ô�ص��ף�����·���ٳ�ʲô�£��Ͱ����ͻ����ˡ���
���ǣ�лл����лл����ͬ־����
������л�ˡ�ֻ����ôԶ��·����ô�صĻ���ô��������£���ô����ôС�ĺ���ȥ���أ���
�����Ǵ��˶�û�գ�û�취�����˸�����С�ġ�
���Ǻã����������Ժ�Ҫע�⣬����С���ӳ�Զ�š���
���ǣ��ǡ�����һ����һ��ע�⡣��
���ټ�����������
���ټ������˸����������������֡�
˵����ô��Ļ����˸�ʼ��û�д��ţ��Һ;���һֱվ�����⡣��������֮�˸��Ŵ���ţ������״�����ֱ��¥ȥ�ˡ��Ҹ��Ž��ң����ð��ţ����ϴ��ţ�˩�����š��һص�¥�������Դ��ߣ����Ӳ�֪���ǵڼ��η��������ˡ�
�˸��ص�¥�ϣ������ס�������һ��������ȥ�������Ȼ�����Ƶģ�
����û�������ɣ������ﻹ����ϡ���������ųɣ���
�ҵ�ȼú�͵ƣ�������������ϡ������Щ���ͣ��������ˡ�����һ����ˮ��ϴ�˳���Ľţ��ϴ�˯�ˡ���Ϊ����ƣ�ͣ��ܿ��˯���ˡ�
��ʱ��ûǮ��Ь���Ұ��춼�Ǵ��š�������˯ǰ��ϴ�ţ����Ͼ˸��Լ���ľ�忳�Ƴ�����ľ�죬�ϴ�˯������ϰ��һֱ���ֵ��ϳ��У�ѧУ������һ˫��ʿЬΪֹ��
�ڶ����峿�����Ծɷ�ɴ��
3
�ڽַ����������ѹ���£��˸�����ȥ��������ɽСѧ������У������Ӣ����У�����ҵ���ʦ�칫�ң������꼶��ʦҪ��������ݰ��ڿ�����ȯ�����ҽ������ײ��ԡ��������꣬�������֡�У���������������ҡ���Ϊ�Ѿ�����ѧ�ڣ�У�������ҵ�ѧ�ӷѡ��������꼶���˸��Բ����ҽ�ѧ�ӷѣ����α�������Ҳ��У����������
Ϊ�˲�������������ĸÿ���賿����룬���������ҵĴ��ߣ���ס�ҵĶ��䣬ʹ��ק���ң�����������ɴ����Ҫ���ĸ�Сʱ������һ��γɴֻ����Լ50�������ܳ��緹ȥ��ѧ�����硢�����ѧ���˿��سԷ�֮�⣬���Ƿ�ɴ���������پŵ�룬���ʮ��࣬�����ϴ����ڶ��������������
�Ҽ�û��ʱ����ϰ���Σ�Ҳû��ʱ������ҵ���������ҵ�����ڿμ�ĵ��ʱ�������ҵĹ��Σ�ȫ���Ͽ������������Ͽε�ʱ���Ҽ����ǵ����۾�������ʦ������©��һ��һ�Ρ����ԣ���ȫ���50��ͬѧ�У������ǰ��ڿ��ԡ���ĩ���ԣ��ҵijɼ������ڵڶ���������֮�䡣
��һ���賿����ĸ�Լ�˯����ͷ������������ʱ���Ѿ��ĵ���ˡ���������һ�����£�����ֻ�����ã�¶����˫�ȣ�ږ��Ƥ��Ь������ææ�����Ҵ��ߣ��ر�ʹ���ؾ��ҵĶ��䡣�ұ�ʹ���ˡ���Ȼ�����˯��һ��Сʱ������ƽʱȱ�߶�������˵����һСʱ��Ȼ�����������ԣ����䱻�������ۣ���Ȼ���ѷ��ѣ�˯�����ʡ����������˼�����Ƿ�������´�������ľ�죬���հ��յ���¥��
ľ��İ������Ѿ�ĸ�����ˡ����ڴ��ϴ��������ң�
����ľ�����ˣ����컹�봩ѽ����
�Ұ�ľ�����ˣ�����¥�ݵ���������ȥ��ɴ��
��һ������ϣ�����ɶ���Ѿ��˵��Թ�����ĸ�����ˣ��Թ����緹�����������ߡ�˵��������緹�ˡ�����ѧȥ�ɣ���
������������������ǡ����̡��þ˸��ṩ�ı�ë̺��������ҡ���һ����������ģ�������ææ��ѧ��
һ�����ң��Ҿ�ſ��������˯���ˡ���ʵ��û��˯�ţ�ֻ���ּ��ֶ����������Ѱ��ˡ���ʦ���ĿΣ��Ҷ����š���������������������������㡣ֻ����ʦ���ҵ�ͬ��˵��
�������ƺ�����ͬѧ��������˯�ˡ�ע�����Ρ���
ͬ�������Ҽ��Σ���ʵ�ڴ���������ֱ��������ſ���ˡ���ʦ���ٴ��ҵ�ͬ����˵�������˰ɣ��¿κ�����취����Ū���ҵİ칫��������
�¿κ�ͬѧ�Ƕ���ȥ�ˡ�ͬ���Ѿ���Ū���ң��Ҹ���һ�칫��ȥ��
�������µ�������Һ���˵������������ʱ������ϧ��������ײ����ڡ���ʦ���˽��ҵ������ֻ�����������⡱��������ѡ��
��ʦ���ҡ��Dz��Ǿ�ĸ�����ˡ������Dz�������û˯�á������Dz��ǽ������̫���ˡ���������ʵ����Dz���û���緹���������ڵ��˵�ͷ�����������ⶼ��ʵ�ʣ�����ֻ���ڶ����У�����ѡһ��
��ʦ��˵��û���緹�������ͳ�һǧԪ����ң������ҵ�ͬ����
��ȥ����ȥ���ӿڣ�����������ӻ�����Ҫ�ȵġ���
ͬ������Ǯ���ɿ��ܳ�ȥ����ʦ�ƹ�һ�����ӣ��������¡�˵��
��ЪЪ�ɣ����ض����˰��ӣ���Ҫ�Ͽ��أ���
�Ҹ����²��ã�ͬ���Ѿ�����������ܻ����ˡ���������ͷ�����ң��һ��������Ԫ������ʦ����ʦ˵��
��������������ӵ�����ô������ͷ����
���ҡ�����ͬ��������˼���������ӡ�
�ҽ�����ͷ��������ű�ˮ������ǡ���ʦ���һ���ɾ����־���ң����Ҳ����ٳԡ�������һ����ˮ�����������ӵ�����ȥ����ˮ�����ˣ��ٵݸ��ҡ����������ſ�ˮ��������ͷ����û���꣬�Ͽ�������ˡ���ʦ��ο�ң�
�������ż��������ԡ���ȥ�������ǵ�������ʦ�����������ȥ�ϿΡ�����ʦ���Ž��壬���������Ͽ�ȥ�ˡ�
һ�����磬��ʦ���������ĸ�ͬѧ��ֵ�����������������굽�ң���ƽʱ���˰��Сʱ�����ҵ�һ���ȸոտ���߸ߵ�ľ�ż�����ĸ���Ҵҵشӻ﷿�ϳ��������ظ���һ�ơ��ҵ������⣬�����ݺݵؿ���ˮ��̨���ϣ�����һ��������İ�����˺���ѷε�ʹ����������Ӣķ�����������еĻ�����뿪֯���������ŷ��ҡ�������������ҵĺ����ף������ֹ��ţ�
��������ܻ�̰��ġ�Ҳ��Ҫ������ô���ģ���
��ĸ��Ȼ��ŭδϢ���������£�
����������棬�Դ����ϡ����������������ӡ�����͵�����ɻȫ�ֵ�ѧ�����ؼ��ˣ�ֻ���㵽ʮ����Ż�����˵������Сʱ�����Ķ���Ұȥ�ˣ��������緹������Ҹɻ��
��Ӣķ�����ң�������ҵ�ʹ����������Ѫ�ˣ������������¯��ȡ��һЩ¯�ҷ��ϣ���Ȼֹס��Ѫ��������ʹ��Ȼû��ֹͣ����Ӣķ���Ҽ���ȡ����������Ҵ����﷿���ڷ�������һ�뷹�������ϵIJ��֣��������£������ҵļ��˵������ɣ������˾�ȥ�ɻ�Ժ����̰���ˡ�������Ӣķ����Ϊ����̰���ˣ���ԩ���Ͳ������ؼ����յ�ʱ���ˡ�
�Ҹո��ڷ���ǰ���£����뻹û����������ĸ��һ�������س�����������������������ﵹ���ƽ����ӺͲˣ����ϲ����ӣ������������ֵ�˵��
������ˣ���ɻ��͵���ͱ���Է�������Ҳ����ȥ��ѧ�ˣ���
��ʱ����ͷ���ε�����˯������ֻ������ǰһ�ڣ��·��Ѿ�����ҹ�����������Ǿ�����ǰ��˸����ʵ��֧�ֲ�ס�ˣ�һ֧�첲���ڷ����ϣ�ͷ�ͻ������ط�����������ĸ��Ȼ�������ģ���������������Ӣķ�������ң�Ȱο�ң�
������������������������ȥ��ɴ�ɣ������ֹ��������������ҵĶ��ߣ�����˵�������������¥����˯���ˣ�������ȥ�Է������𣿡�
��Ӣķ���Ͱ͵����ž�ĸ��һ����¥����������һ����ӣ���ĸ��������ȥ�ˡ���Ӣķ�����ң�������ŵ������﷿����Ϊ��ĸ�ķ������ͷ���ϣ���������һ�뷹�����ҳ���ȥ��ѧ��
���п��Ժ�ļ��죬�����ųɼ�������������ĸ�ķԸ������ɼ�������������ĸ��ʶ�֣������ҵijɼ�������Ů����Ӣķ����Ӣķ���˿�������95�֡�����98�֣���ʶ�ķ�������б����һ�����ߣ��ٿ����������д�š��������������е���֣����������������������������������
����������ʲô��˼������ĸ�ʡ�
����Ҳ�����������Ӣķʶ�����ޣ�������������Ȼ������ĸ�����ʲ���ʲô��������ɼ�����ȥ���ھ����塣��һ��˸����ڼң�����Ҳ�ò��ŷ���ô������ۡ�
�ھ����忴�ųɼ�������ԥ�˰��죬������ĥ�ţ���������������������������ʵ����û�������
��ĸ�����ҵ���ͻ�ƿڣ��ҵ��˳��������ɡ���һֻ�־�ס�ҵ��Ҷ�������һ·�ϵ������������þ˸��������ֻ���쳤���ӣ�˳���������ƣ�һ·����ȥ����ĸһ·ק���ң�һ·ߺ�ȣ�
�����ǿ�������ҿ����ģ���˵��������ˡ���桵ĺ��ģ�����������ѧ���顣���ǿ��������ǿ���������ĸ��һֻ�������ҵijɼ���������������ȥ��ѧ�����˸���û����������������ҿ�������ҿ����ģ���
���ڵ����ӡ�������ָָ��㡢��ͷ�Ӷ����������ǵ�����
������ɣ��⺢��ÿ�ο��Ե����ζ���ǰ���ѽ����
��˭˵�����أ���7����û��������
��������һ��û���𣿡���֪��˭����һ�䡣
����ѽ�������ǿ����ɼ�������һ������ġ��������ӵĴ�ɩ������ĸ���Ӿ�ĸ����ץ���ɼ�����������ײ����������´�½�Ƶģ�˵��
����ҿ�����ҿ������ⲻ��ȱ��һ�Ƴ�ʶû���𣿡�
����ѽ��ȱ��һ����ôƽ��ѽ����ƽ����һ�����治�ǿ����𣡡����˽�����͡�
��ʱ��ĸ�����ң��մ��þ˸��ҷ��ء������Ƿ��������ʣ���ĸ�е��ﻢ���¡�����æ�ſ����Ҷ�����֣����ң�
����ʶ������ôûȥ��������
��������˵�������û������ѧ�𣿡�
����һ�죿��
�������������ڼҷ�ɴ����һ�죬���ÿ���ʶѽ����
����Ϊʲô����˵����
�����ò��Ǹ���˵���ˣ���һ���ǿ��ԡ���
���ȣ�����������ӡ���������ô��������������ޣ�����ĸһ����Թ��һ�������˵��
4
һ̨֯�������꾰�ֲ��ã���������ά����ȥ������������Ϊһ��С��������������ĸ������Խ��Խ�����ˣ�ʱ����������������Թ�˸���
����19���������ң�û�й���һ������ӣ�����ԩ�ģ������Ҹ�����ô�ῴ���������С���ޣ���
ÿ�����ʱ�˸��͵�¥�����ǵķ��������̾������������
������û�ã����ҷ�Ͱ�������Ҳ��ã���˵���˸д������;����Ѿ����ѡ�������ɴ��ë����ӣ������Լ����Դ���žž���ô���ܷ���ɳ�Ƶ�������¥�µ��˶������������������Ǿ�ĸ�����ľ˸������������������������������ֹϢ�ˡ�����¥�·�ɴ��֨ѽѽ�ķij�ľ��ĥ�����������������Ƿ������������ĺ�����
�˸�����ĸ����ҽ���һЩ��Ǯ��������ȥ�����⡣��˵�����Ƥ���ܱ��ˣ�һ��Ǯ�����չ���������˵���������һ�����������˷�Ǯ����ȥ�̲����˷ѣ����ж����ɵ�ͷ���˸�ȥ��һ�����£�����˵�Ǿ�Ҫ�ؼ����ˡ���Ҷ��ܸ��ˡ�������ϰ��˴�Ǯ���ྰ�����ˡ�
�ھ˸���δ����֮ǰ����������һλ������������˭���ϰ���֮������ĸ����ͺ�����㡱����ĸ�����е�һͷ��ˮ����֪��ô���¡���ĸ����������ǻ����ͨ����ֻ������Ӣķ�����롣��Ӣķ��ȻҲ��̫����������ָ�ֻ��ŵĹ�ͨ�˰��죬��������һЩüĿ����������������ģ�
��������ʮ���꣬û�и�ĸ���˸������������ʶ�ġ��˸������������⣬��װ���ģ���Ȼ��Ҫ��ʮ���ˣ���Ȼ������档�����ڰ�æ��������Ȼί��������������¶ˮ���ޡ��˸�����ʱҲ������ͤ�����������еĹ��ӡ�����ֻ������ʱ�˲��ã�Ҫ��ȻȢ���������Ҳ��Ϊ���������Ů���䲻��ʮ����ɫ��ȴ�ȷ�������ö࣬�Ͼ���ֻ������һ�������ѽ��
С�����Լ�Ը����С���˸��Ͱ������ظ������ˡ��˸��Լ��ȶ���������ô�С��Ȼؼ�������������족��Ҫ�Ǿ�ĸ����ô���ԣ����Ϳ����ö���֮�ؿ����ظ��ˡ�
���š�������Ӣķ����̸�˺�һ���ӣ����ڲ�̸�ˡ���ĸ��æ�����ʣ�
����Ӣ�㣬������ô���£���
���ޣ����ϰ���ʶ��һλ���ѣ�������ġ�����Ӣķ������ʵش����
������������ͷ��Ȣ����С���Űɣ���
��ĸ�IJ²���Ȼû�д��������ѻ�Ů�˴ϻ۵ı��ԡ������Ͼ���������ͨ����������û��ʮ�ֵİ��ա��������������Ƕ�һ�������������DZ�Ҫ�ġ����������������С���䣬ˤ�������⣬��������Χ�۵���Ⱥ������˵��
���������ˣ������Ķ����Ķ�ȥ�ɣ�������Ҳ���������ġ���ȥ�����Ҽ��Ǹ�����������������������Ҫ�������ʣ����ˣ��ͱ�����ţ���
��Ӣķ��������Χ�۵���Ⱥ���Ƴ����ţ��Դ��˵��
����ȥ����ȥ����ʲô�ÿ��ģ��������ִ������š����к��µ��ˣ��ӵ������ȵ�դ���Ŀ�϶������ӡ��뿴�����������鷢չ�ľ����ͽ�֡�
��Ӣķ���Ź���ϸ�۵��֣������ij���˵��
�������������ᣬ������Ѱ�żҰɣ����ϰ����Ҵ��ڵģ��Ѿ���һ������ˡ���˵�Ҿ�Ҳ���ã�����������Ҳ�����кô��ġ������߰ɣ���
������ͷ����Ӣķ�����ţ�ʰ�����ڵ��ϵ����������������������ҲûҪ��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