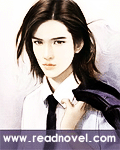岁月匆匆-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一天,吴家来了个远房亲戚。不知该称她表嫂,还是表婶,也许是我外婆的侄女儿什么的。称呼什么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这位高高的个子、粗壮的身子,有着和男人一样浑浊嗓音的亲戚,与“矮婆”却十分投缘。不知两人怎么商议,“矮婆”居然同意女儿跟这位亲戚一起到浙江去织布,而且和机修工胡舜训同在一个厂子里。
也是这位亲戚,为舜训和梅影到胡家做起红娘来。竟然是工夫不负有心人,水到渠成。
梅影的身材和容貌,以及她的突然来临,立即吸引了全厂的年轻人、中年人,和家有妻儿老小的半大老汉。他们一时停下手中活计,齐刷刷地向她投来注目礼。
“表嫂”与舜训比较熟悉,平时也常到胡家转转。虽然她并非专业的媒婆,但她会寻找适当的话题和谈话的时机,来引起胡老太太的注意。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她藉着去胡家还箩筐的机会,与胡老太太拉起家常:从工厂里新来一位漂亮的福州姑娘说起,拉到胡大公子的年岁、婚姻大事,慢慢勾起胡老太太的心事。
胡老太太年过五旬,已经到了喜欢“咸(闲)扯萝卜淡操心”的年龄,和“表嫂”言来语去,竟然十分默契。她不无心事地说:
“嗨,孩子大了。你说的这个福州姑娘,不知道能不能合我儿的心意?”
“没问题。这事儿我去说,一准能成。你就放一百个心吧!”
“表嫂”敢如此断言,当然心中有数。其实,梅影和舜训在她的撮合下,已经好上了。这事只瞒着胡老太太,将她蒙在鼓里。今天,“表嫂”就是来探探胡老太太的口风的。
吴梅影在此没有娘家,事情虽然能自己做主(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从”),也还要去信跟福州的母亲说说。这样一来二去,差不多和丈夫有一年多的认识过程。双方的长辈都已经同意,年轻人又十分满意,接着就择日成亲。“表嫂”自然是当仁不让的红娘和证婚人。
媳妇娶过来之后,胡老太太就发现,这是她这辈子所作的第二个错误决定。
第一个错误决定,是他当年选错了门,嫁到胡家来。原以为胡老先生是个读书人,将来科举及第,混个一官半职,夫尊妻荣,夫唱妇随。谁知清朝将亡,民国复兴,科举废除。胡老先生求学不成,报国无门,一气之下,一命呜呼,早早归西。胡太太少小青春,独伴孤灯。虽然胡家有点产业,家道也还殷实,进门后“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一些内外之事,均不用她操劳,使她渐渐养成一个不招人喜欢的身材,人前人后总受人白眼。丈夫中年去世,使自己失去了谈婚论嫁的第二次机会。他虽然无心为胡家立什么贞节牌坊,但也没有不立牌坊的机遇。只有一尺多高的观音瓷像,藉着沉闷的木鱼声和缭绕的青烟与她朝夕相伴。
第二个错误决定,就是轻易答应了儿子的这门亲事。
儿子的亲事,完全是被她自己耽误的。不然,这么殷实之家的公子,不会拖到三十岁还未娶妻生子。早几年,媒婆就像穿梭式的,来一个,去一个,胡老太太总是左挑鼻子,右挑眼。不是嫌姑娘家道不富裕,门不当,户不对;就是嫌人家长相逊色一些。现在倒好,二儿子也长成了,求学在外,还谈了女朋友,说是要准备结婚,而且连问都不问母亲同意不同意。俗话说,薯栽哪有倒插的道理。大儿子成婚的事,就成了燃眉之急。因此,她看到年龄相当,性格相仿的吴梅影,就动了心。旁观者更能看出其中的一点隐情:就是儿媳妇的娘家远隔千山万水,可以省去一笔厚重的聘礼,接下来就可以从从容容地为二儿子筹备婚事。
那么,既然成全了这段美满姻缘,为何又后悔了?
因为儿媳妇生得太俊,特别讨人喜欢。凡讨人喜欢的,别人也必喜欢。果然不出胡老太太所料,儿媳妇进门后不久,工厂里那些男人见了儿媳妇就瞠目结舌的传言,就陆陆续续地儿传入她的耳朵里。
“不妙!”她这样想。自己的儿子将来必定命丧在这个漂亮女人的手里。她要及早给儿子提个醒。
“王妈!”
“哎——”王妈总能随叫随到。这是她在女主人手下十几年调教的结果。同时,她也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当家里有人说话的时候,她总要尽量靠近说话人,竖起耳朵,在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偷偷听他们说话,猜测下一句将由何人接茬,说什么话,作什么决定。这样,结果就会被她猜中五七分,自然就能作出迅速的反应。
“去把大少爷唤来。”
“是。”王妈应声而去。
不一会儿,舜训来到母亲跟前,低头肃立,静听母亲吩咐。自从先父去世,好多年来,母亲操持这个家,对儿子来说,母亲代表着一种不容侵犯的尊严。在这个家里,母亲的一言一语,对任何人都不容置疑。
“妈,您唤我?”儿子说。
“嗯。”母亲依然吹纸媒,将燃着的纸媒对准水烟筒上的烟丝,像往常一样,先吞云吐雾一番,再接下来说她想说的话。此刻,藉着吸这一口烟的空隙,迅速打好了腹稿。
“妈提醒你,要注意你身边的女人。”
“您是说梅影?”儿子心里明白,除了梅影之外,在他身边,再没有其他年轻的女人,也不可能有其他年轻的女人。
“对,就是说她。”
“不是您让儿子娶她的吗?”儿子很少反驳过母亲,但今天的话题有点蹊跷,儿子才这么说。
“是妈让你娶的,但妈后悔了。”
“为什么?”
“她太漂亮,太招人了!”
“妈,你怎么这样说?她始终都规规矩矩的。打她一进厂门开始,从没有丝毫非份之想,也没有不规矩的事情发生。”
“妈已经听了许多传言,说她是人见人爱。”
“这也是她的过错吗?”儿子留神注视母亲,望着她那张本应有些皱纹,但却光滑平整的脸;虽然丰腴却并无弹性的面庞;纵然细白却并不招人喜欢的笑容。此刻,从这张脸上,你甚至分不清喜怒哀乐,仿佛刻板一样的没有变化。
“难道母亲吃醋了?”这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很快就被儿子否定。犯不着哇!一个是婆婆,一个是儿媳妇,上下两代人,吃哪门子醋啊?况且凭着母亲的威严,儿媳妇并不能损害她什么。
“正因为她招人喜爱,”母亲接着说,“我才提醒你,不要把小命栽在这个女人的手里。”
“妈,你这话孩儿越发不明白了。”儿子不服气,有那么严重吗?
“至少,你不要让她伤了元气,伤了你的身体。”母亲语气和缓了一些,“男人应以荣宗耀祖为己任,不应该沉溺于裙钗粉黛之间。”
“我明白了。”儿子这么说,也这么想。母亲是看到儿子与儿媳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地朝夕相处,心里有所羡慕和嫉妒。
“真明白了?”母亲追问。
“真明白了。”
“明白了就好。下去吧。”
话虽这么说,母亲对儿子还是不放心。她事后吩咐王妈,要和自己好好配合,时刻监视儿子、儿媳的一举一动,不要让它们超出自己所允许的界限和范围。
2
“谁叫胡舜训?”
两名黑衣警察荷枪实弹、穿堂入室,闯入胡府。王妈急忙赶出来招架。
“先生,长官,出什么事了?”
“有人告了你家大公子”警察甲说。
“我们家大公子犯什么法了?”王妈继续问。
“偷盗。”警察乙说。
“笑话!我们家有吃有喝的,什么也不缺,用得着去偷、去盗吗?再说,大公子一向为人忠厚老实,街坊邻里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他会偷盗吗?”王妈不服气,要与这两位不速之客论理。
“跟你说不清楚,”警察甲说,“快去把你们家大公子叫来。”
“谁在这里喝五唤六地?”胡老太太缓缓地从后堂出来,手里仍然拿着水烟壶和纸媒。
警察乙抢先回答:“胡老太太,是这样,有人告了你家大公子……”
“告他什么?”
“告他偷了织布厂的财物。”警察乙说。
“放他娘的狗屁!”
“是。”警察乙答非所问地说。
“给我退回去!让你们的徐局长来,我要亲自问问他。”
警察甲看来象是个小头目,说话有一定的底气。他阴阳怪气地说:
“不敢。当官的哪能听我们小当差的使唤?”
“你就说是我说的。”胡老太太不依不饶的。
警察甲:“即使是你说的,小的也不敢传。”
这时,大公子已从产房整衣出来。
“谁唤我?”
“这两位长官。”王妈说。
“什么事儿?”大公子说。
“有人告你偷盗。”警察乙说。
“谁这么狠毒?”大公子又问。
“不知道。”警察甲说。
“不知道,你们来干什么?”胡老太太逼问一句。
警察乙:“这哪是我们知道的。”
警察甲:“让大公子去警察局一趟吧,兴许能说清楚,很快就会回来的。”
警察乙附和道:“对,还是让大公子跟我们走一趟吧!”
双方僵持了一会儿。
“儿哪!一清早妈的右眼皮就跳得厉害。我寻思着要出事,果然不出所料,事情就出在这里。”母亲对儿子说。
“妈,我去去就回来,没影儿的事,说清楚就会回来的。”舜训没把问题看得太复杂,心如止水地安慰母亲。
“千万小心!”母亲说。
“孩儿知道了。”
三人正要动身,胡老太太扯住落在后面的警察乙,向他手里塞了一张纸币,低声问“说,谁使的坏?”
“还不是因为少奶奶长得太俊了。”
“果然如此。”胡老太太目送一行人离去,转身进入儿媳妇的房间,问“是你招惹人家啦?”
“没有呀。”儿媳妇说。
“没有,警察局怎么会来抓人?”
“都是周老板一厢情愿。”
“你没答应他什么?”
“没有。”
“这个畜牲!老色鬼!”
警察局局长办公室。
胡老太太对着和她一样肥胖的徐局长,秋颦一扫:
“徐局长,小儿的事,就这样被冤枉了?”
“我也是没办法。有人报案,我就得立案。”水桶局长似乎在卖关子。
“小儿可是你看着长大的。我们还是乡里乡亲呢!”胡老太太尽量与徐局长套近乎。其实也不用套近乎,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胡老太太年轻的时候,跟水桶局长同过学。要不是娘家作主,早嫁给了胡家,说不定,如今还当上局长夫人呢!
水桶:“我也想大公子是冤枉的。可是人家周老板有人证物证。”
胡老太太:“那肯定是栽赃陷害!”
水桶:“这就不好说了。我也没办法。”他双手一摊,表示无能为力。
胡老太太递过一只首饰盒,眉头一挑,嘴角一动,微微一笑,说:“办法总会是有的。”
水桶局长揭开首饰盒,眉毛眼睛动了动,仍不动声色,说:
“不过,这事不会很好办。周老板是一口咬定的。”
冬瓜婆婆对水桶局长:“你就不会动动脑筋?”
水桶:“脑筋是要动的。不过——,被周老板绘声绘色地几句话一说,我心里也痒痒的。”
冬瓜故作不解地:“痒痒什么?”
水桶:“就像当年总想见你一样,想会会你家大少奶奶。”
“无耻!”冬瓜气不打一处来,伸手去抓首饰盒,被水桶抢先一着,用臂肘将它划进抽屉里。
“谢谢了。”水桶不冷不热地说。
冬瓜气极,起身跺了跺脚:“一群土匪、流氓、地痞、无赖!”说罢扬长而去。
产房内。
梅影一只手臂搂着婴儿,另一只手臂拍着襁褓,嘴里哼着闽剧小调,给婴儿催眠。她端详着已经睡着的小脸蛋,心里油然而生一种自我的安慰与满足。
婆婆怒气冲冲地进了大门,大声呼喊:
“我早就说过,这女人一定是胡家的一个祸害。”
媳妇在产房里不敢吱声。这时候她说什么都没有用。丈夫被逮走了,因着自己天生带来的容貌。她一时听不到丈夫的安慰,体贴不到丈夫的温情,唯有婆婆的怒目和阿斥,时常展现在眼前,萦绕在耳际。她只能忍气吞声。眼下还在月子里,月子里的女人,无论身体和精神,都处在最怯懦、最虚浮的状态。经不得半点呕气,来不得一点伤怀。否则,会给后来的身体,带来终生的伤害。现在不能整衣出门,只能忍。忍吧,忍吧!满月以后再说。
好不容易挨过了三十天。
这一天一大早,梅影起身梳洗穿戴,给孩子喂饱奶,正准备将婴儿交托给王妈,动身出门。后院即传来婆婆呼喊王妈的嘶哑声。她患了感冒。
“王妈——”
“哎——,来了,来了。”
“去把少奶奶唤来。”
“噢。”
王妈走近产房,堵住梅影的去路,为难地说:
“少奶奶,奶奶唤你哩!”
“走吧!”梅影同情地说。
王妈双手接过婴儿;两人一起来到胡老太太面前。
“妈,您唤我?”梅影低声地说。
“一大早打算去哪里?”婆婆望着打扮整齐的儿媳妇,说。
“去警察局,看看孩儿他爸。”
“孩子他爸总是要看的。今天先别去吧!待会儿算命的张先生要来,给孩子定时起名。这是孩子满月后的头一件要紧事。”
“好吧!那我先回房去啦。”儿媳妇说。
“回吧!铁算张来了招呼你。”
铁算张戴一副圆圆镜片的深度老花眼镜。为了防止脱落,还在镜脚上系了一条细细的银链子。他在正厅王妈预先摆好的骨牌椅子上坐下,品着名茶,等待老奶奶、少奶奶的到来。
老奶奶来了,居中坐下,将铁算张隔在一边;另一边的空位置留给怀抱婴儿的儿媳妇梅影。
铁算张起身,靠近少奶奶,伸手去拨开襁褓的领口,意欲查看婴儿,却偷偷觊觎起少奶奶来。他从少奶奶姣好的面容顺势而下,通过粉颈,意欲再往深处探究,被少奶奶发觉,伸手扣紧领口。他不无失望地收回目光,才真正去端详婴儿稚嫩的面庞,又扯出婴儿的小手,对孩子的手纹、指纹琢磨一番。
“怎么样,这孩子的命理如何?”胡老太太急切地问。
“胡老太太,这话我不敢说。”铁算张故弄玄虚地,无非是想多敲点资费吧!
“不敢说也得说!你但说无妨。”
“好,那我就说了。这孙公子天性命硬,要尅父尅母的。”
这话说了等于没说。哪一家的孩子,如果不夭折,定然要长大成人,死在父母之后。可奶奶不这么看。她非常认真地问:
“有什么依据?”
“他一出生就不言不语,保持沉默……”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铁算张已经察觉到婴儿头部的烫伤了,瞎子摸到伤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