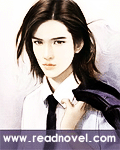岁月匆匆-第2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演中演出。他不但在厂区各车间之间表演,还参加厂际之间的交流,到港头工人俱乐部去演出。据说,他还向车间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呢!
有着以上这些因素,舅父爽快地答应了教导员的要求。在七月二日,到孤儿院办理了一应手续,将我领回了家。
以后的命运如何?有升学再造的机会等着我吗?请看第五章《金兰姐弟》。
第五章金兰姐弟
胡振铎考取福州第八中学。此时舅父不再经营织布作坊,改租地种菜了。当然,他得一边读书、一边挑水浇菜、卖菜。
一个孤儿,在学校享受免交学杂费、助学金,得到政府和老师的关怀。又结识了一个助人为乐的姐姐,使中学的生活丰富多彩。这其间,经历了1955年蒋帮对福州的大轰炸,目睹达道路繁华街区在顷刻之间夷为废墟。学校上课时间改为早晚两个时段,以避免人员的过度集中,减少危险。福建空军基地完善后,蒋帮飞机被堵截在沿海地带,福州平静了。学校恢复正常上课时间。
为了表达对前线解放军的感谢,学校发动同学给解放军叔叔写慰问信。胡振铎在姐姐的家里做作业(因为舅父家用不起电灯),想起给毛主席写信,得到姐姐的支持。1956年1月20日,中共中央秘书处办公室代表毛主席他老人家……
1
在孤儿院两年之后,回到舅父家里。舅父家的成员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91岁的祖奶奶去世了。姨姨也出嫁了。嫁给正对门的做伞骨的师傅。姨父也是自幼失去父母的孤儿,单身一人。他为人忠诚老实,是谁牵的红线,只有大人知道。
姨姨结婚那一天,舅父为我向孤儿院请了一天的假。让我回来给姨姨做“小舅子”。随着迎亲的唢呐、十番队伍,到拐角处姨丈的远房亲戚家里,迎娶新娘。权当那是姨姨的婆家。三亲六眷忙忙碌碌,中午在舅父家吃了便饭,接着操持晚宴。
如今的“小舅子”都有红包。红包的份量,从三五十元,涨到三五百元,甚至三、五千元。所以,没有“小舅子”的,就找自家的儿孙充任,并不存在实际意义上的“小舅子”。为的是不让红包肥水外流。当时那个年代,有没有红包,我不知道。即使有,对我也没用。只有九泉之下的舅父、舅母知道了。
午饭过后,我睡得昏昏晕晕,一次又一次想起来,又睡过去,一直到下午三点多钟。我急着要赶回孤儿院去,大人也不再留我,因为我的任务已经完成。再说,从横街步行走到下渡周厝巷,至少也要三个多小时。晚了怕赶不上吃晚饭,大人也没给我乘车的车费。
真正离开孤儿院,回到舅父家里并不惬意。舅父每个月56元固定工资,要负担全家七口,不太容易。后来联系租赁了达尝堂近二亩的废弃房宅地,垦荒种菜。我还在孤儿院的时候,大礼拜回来,也参加了垦荒。
说是垦荒,并非开垦腐熟的土地,而是从成堆成堆的瓦砾中,寻找那被遗忘的熟土。我回到家时,还有一小半的荒地没开出来。每天除了三点半起来,到园内的小池塘担水浇菜以外,就是继续开垦荒地。舅母用山锄开挖,每刨四五下,就要蹲下来,拣拾瓦砾。这样,一米宽、十二、三米长的菜畦,至少要四五天才能开好。可见它的不易。
达尝堂是富裕之家,对这片废弃地并不在意。到年底,去送租金的时候,我也跟了去。他们仅象征性地收了我们二十元人民币。这区区二十元,对他们如九牛一毛,可有可无。但对我们来说,却是一种承诺,一种应许,一种获得垦荒种植的契约和权利。
上午垦荒,到九、十点钟的时候,舅母会给我五分钱,让我去铸鐤湾买油炸芋粿。好大的一块,娘儿俩一人一半,足够充饥,可以干到十一点左右再回家。
我当时才十二岁,挑水的水桶是烂了底、经修桶师傅整修过的,比正常的水桶短了一截,打满水也只有七八十斤。孤儿院回来正值暑期、夏天,小池塘里的水渐渐干涸了,涌出来的泉水不够用,我们要到园北角去打井水。对于娇嫩的小白菜来说,清晨、傍晚给它浇灌清凉的井水,是再好不过的了。这样可以防止它因闷热而滋生蚜虫。但是,那么大的菜园子,每天要浇灌百十担井水,就十分劳累了。
我也帮助舅母掐空心菜或甘蓝菜。因为不知从哪里下手,常常遭到舅母的唠叨。还是那一句:“吃大猪的料,叫小猪的声音”。这句话一直闷在我的心里。到了星期日那一天,我对舅母说,让我去孤儿院玩一天。舅母答应了。
那一天,卖完了早市菜,吃完早饭,我去了孤儿院。在孤儿院吃过午饭,又吃过晚饭,其间与伙伴们玩得很开心。天色渐渐黑了,却没有回舅母家的意思。孤儿院里已经没有我睡觉的床位,我踟踟蹰蹰地到了昭英老师的房门口,眼里流着泪,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昭英老师问明情由,将我送到办公室,交给教导员。
教导员和颜悦色地开导我:“你刚刚回去,总会不习惯的,过一阵子就好了。况且,我们孤儿院没有设立初中部,也没有工厂什么的,可以让你学手艺。你现在还很小,应该回到舅父家去,复习功课,考上中学,继续学习。我们已经跟你的舅父说过了,以后有什么困难,政府还会帮助你们的。你舅父也向我们做了保证,今后一定好好待你。你放心吧!”
我没有什么话好说,只有沉默。教导员扶着我的肩膀,继续说:
“那就这么办吧!天色已经很晚了,我们派一个员工送你回家,就让李叔叔送送你吧!”
他转身呼唤李叔叔,李叔叔来了。教导员对他说:
“小李,天黑了,你送胡振铎回家吧!看他家里人有什么说法。你就多劝劝他们。”
“行,走吧。”李叔叔拥着我,走出了孤儿院的大门。
虽然我们搭乘了公共汽车,到家时,还是七点半以过了。大门早已闩上。敲门后,听到舅父从楼上下来的脚步声。大概他下班刚刚回来不久,才会有这么快的反应。
舅父打开门,见到我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正在疑惑,李叔叔撒了一个谎,说:
“振铎在孤儿院参加活动晚了,让我送他回来。”
舅父向李叔叔道了谢,径自上了楼。我随后关上门,进了屋,到楼下自己的床上,那是祖奶奶临终前睡过的苦竹编成的床。
我静静地躺在床上,很久很久,才迷迷糊糊入睡。
刻板的生活日复一日:清晨三点半起床,打水、挑水、浇菜,然后摘菜,挑着菜担子,和舅母一起,在菜园子附近走门串户地叫卖。卖完菜,回家吃早饭。早饭后,继续到菜园子里垦荒。中午回来,午饭、午休,下午三点半至四点,再去菜园子里,打水、挑水、浇菜,大约七点钟回家。吃完晚饭,已是七点半、八点光景。
舅母到斜对门的钟俤嫂家门口闲坐。钟俤嫂家正当交叉路口,人来人往,凑在一起,就谈天说地,王五马六。我也跟随舅母身边,听大人闲扯。
听了别人的议论,舅母对我半是玩笑、半是责备地说:
“很快就要升学考试了。人家的孩子一天忙到晚地复习功课。你倒好,从孤儿院回来,没见你翻过一回书。”
舅母说得轻巧,每天凌晨三点半起床,做了那么多的体力活,晚上八点才能安歇,对于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来说,哪有精力支持得了?
邻居们建议,让我去三山小学。参加补习班听课。舅母也同意。那时候的补习都是免费的。我去了两三次,都没有去见我的恩人许校长。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怎么那么糊涂呢?
临近考试的前两三天,依然是在钟俤嫂家门口,依然是晚上八点钟,舅母还是责备我:
“你不复习功课,要是考不上初中,我看你这张脸,得到菜园子的尿缸里去洗啰!”
对舅母所说的话,我只能似是而非,不必作答。因为,即使是去补习,也免不了清晨三点半起床,打水、挑水、浇菜……这些劳作。
我只能苦笑,心里的凄楚谁能知道?
考试那两天,没再让我起早干活。连续两场的考试虽然不觉得累,但也没什么好心情。我只是将能做的题都做了,做不来的题没做,一定考不出好成绩。能不能录取,只能听天由命了。
发榜的那一天,邻居的孩子早早就到福州八中去了。我去得略晚。
录取名单贴在传达室进去、旁边高高的墙上。密密麻麻地写了许多名字,不知道从哪里看起。还是邻居的一个小孩眼疾手快,伸手指着墙上,呼叫起来:
“喏,胡振铎,看见没有?”
我顺着他的手势望去,果然看见我的名字。虽然录取了,成绩却不太好。两科都在八十分上下。不过,总算录取了,这张臭脸,至少不用到尿缸去洗了。
注册的时候,班主任王淑英老师把我们初一甲班的同学,都集中在图书室里。她让大家靠墙围坐,先一个个站起来作自我介绍;接着做“击鼓传花”游戏。鼓点停了,手绢落在谁手里,谁就表演一个节目。学猫叫、狗叫也可以。
因为入学的新生很多,初一年段的六个班租用民房作教室。我们初一甲班的教室,从下操场出后门不远就到。上学时,我们都从铺前顶走。我们的教室是独间,在二楼。从教室门口的拐弯处,另有一架小梯子通上阳台。它是木板搭盖的,经不起重压,但若是三两个人在上面,倒是复习功课最好去处。这是菊英姐姐发现的。
菊英姐姐是个细心的女孩,却又带着几分男孩的好强性格。听说她在小学时,百米短跑曾以11秒4的优异成绩,获得全校第一名。攀竿、爬树,她也不让须眉。她还会针线活儿,她所背的书包,是她自己做的,用的手绢,也是自己绣的。她做手绢十分认真,我看得也十分仔细。她取一块白色或月白色府绸,剪成与手绢一般大小,在距离四边约一厘米处,抽出五六根纬纱,然后将布边用密密的针线封上。在抽纱的地方,每隔五、六根经线打一个结,使它形成四边皆有的镂空花边。在手绢的一角,绣上一朵菊花或荷花。一块细雅的手绢就算做成了。
在教室里,1号是贾端生,背后的9号是我,再背后的17号就是菊英姐姐。不知道是她对我的特别关爱,还是我无兄无姐,孤独一人,需要安抚。她对我总是特别严厉,我对她,象一只温顺的小羊,总是百依百顺。如果我做错了一件事,说错了一句话,只要她给我一个眼色,我就会立刻规矩起来。上课做小动作,她就会用铅笔的橡皮头,在我的脊梁上一点,给我提出警告。我立即端正姿势坐好。因此,老师从来没有发现我有不规矩的行为。
当时,新中国刚建立不久,许多失去学习机会的大孩子都来上学,因此,我们班里同学之间的年龄相差悬殊,最小的,前排几个,都只有十二、三岁;最大的,后排几个,有二十二、三岁的;菊英姐姐居中,自认为是我的大姐姐,对我有绝对的“监护权”。
当时,老师教课后喜欢小测验。那天上午有植物课,菊英姐姐提早上学。她从上杭路水巷边出来,特地绕道经过我家,时间才六点半,离八点上课,还有一个半小时。她先跟我的舅母说好,带我一起去教室的小阳台复习植物课。上一节课是有关植物的构造,我们复习了一遍又一遍,采取你问我答,我问你答的方式,把课题掌握的滚瓜烂熟。上课时间到了,萧文瑞老师果然不出所料,给我们十分钟小测。第二周试卷发下来了,我和菊英姐姐都得了98分。
同学们羡慕我们两个人的关系,调皮的同学在黑板上分别写了我们两个人的名字,并在其间划上了大大的等号。我心里想,只要菊英姐姐不嫌弃我,有个姐姐关照我,何乐而不为呢!
2
祖奶奶去世以后,我在厨房间占用了她的床位。祖奶奶79岁起由舅父赡养,活到91岁离开人世。接下来,祖父和祖母也不再另起炉灶。他们那二楼的前半部分,两个房间,也并入我们的“版图”。奶奶和大表妹在前屋住,爷爷住后屋。
奶奶的前屋我很少进去。偶尔进去,看到临窗的桌椅,床架、箱柜等家具,都是比较考究的。雕花镂刻,深红色的漆面,几十年过去了,仍光彩可鉴。左墙上张挂一副条幅,上书:“梅花百本鼻功德,茅屋三间心太平”。大概爷爷早已料到,他晚年会落到自告奋勇,给儿孙烧饭混口饭吃的地步;少壮时的辉煌,早已光阴不再,因此选择了这样一副条幅。
爷爷每天四点多钟起来,为全家九口人烧饭。并打出两份,端上楼去,与奶奶共同进餐。奶奶弄了一台手摇缝纫机,为老朋友缝制汉衣,挣点零花钱。她从不到楼下来和我们大家一起进餐。不知道她和舅父、舅母之间,心存什么介蒂,即使到爷爷72岁离开人世,她此后还有20多年的独居日子,仍然是独来独往。
奶奶的话,对我们虽然没有什么约束力。但有些话,还是很有道理的。比如我在扫地的时候,她会告诉我:“打扫木地板,要顺着板缝,才能将灰尘扫出来;擦拭桌面,也要顺着板缝,否则会将脏物塞进板缝里去。多人共餐,筷子夹菜要看准了再夹,夹到的菜肴,要取出来放在自己碗里,不要影响他人的卫生……”舅母也有舅母的规矩,我们园子里卖菜,除了现金收入以外,也赊账。赊欠多了,就让我去讨债。但是她却不让我对人说“讨”,而要说“借”。比如三嫂欠了我们的菜钱,让我去要。她就再三交代我要这样说:“三嫂啊,我舅母说,如果方便的话,菜钱跟你借一借。”还有,大人小孩都不许说粗话。这些规矩,整整影响了我一生的生活习惯。
垦荒任务完成以后,我们专心致志料理菜园。上下两片地,分种不同品种;同一块地,实行轮耕轮作。舅母卖菜比较粗放。我们的菜从来不注水不说,若是你亲自到园子里来买,舅母又正好在摘菜,她总是双手虎口一卡,就把菜给你。起先买菜的怀疑是不是够秤。舅母再去拿秤来称,结果只多不少。所以大家都放心买我们的菜。这样,每天都有现金收入,而且远远超过舅父的固定工资。因此,舅父上完班就往回赶,尽量为菜园子做些事。空心菜上季时,联系造纸厂食堂,为它提供掐好的菜,可以免去他们一些劳作。舅父还在园子的一角,用木板搭盖了一个简易猪圈,捉回一只小猪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