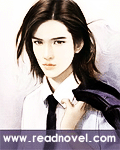岁月匆匆-第2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加工。先将原木经曳木机,从十几米底下的水坞拖上来,到电锯口下,下锯成60厘米左右的木段,经凹槽形的皮带运输机,送到去皮女工面前。女工们在沿皮带运输机一侧的加工架上,只要用短搭钩,就可以将木段拖到自己面前,去皮后,再将它推回皮带运输机,由它带到下一道工序——电斧那里。电斧师傅将木段劈成若干爿,让木节暴露出来,再由去节工人用小快斧除去木节。
松木木节富含松脂油,在抄纸的时候容易造成破洞。被挖出来的松木节是上好的引火材料,除了供应食堂外,有时还可以卖一些给工人。当然是机浆车间的工人啰。
我刚进纸厂,就在调木工段。起先和女工一起去除树皮,后来开挖木节。
3
党中央、国务院号召全国人民大办钢铁。村村寨寨、街道居委会,都要建立小土窑大炼钢铁。要让我国钢铁产量,从现有的东北、上海钢铁基地年产100多万吨;在两三年内达到1070万吨,赶上美国、超过英国。福州造纸厂,作为一个几千人的中型企业,当然也不例外。
厂部在礼堂召开了动员大会。决定在厂门口内河的对面空地,专门新建一个炼钢车间。人员由各车间抽调,也作为各车间对炼钢运动的支持。各车间为了保证制浆、抄纸任务的完成,将三班制改成两班制,每班12小时,以弥补人手的短缺。上班时间为每天的上午六时至下午六时,再从下午六时至次日上午六时。调木工段是手工操作,不宜连续作战12小时,就改为每天上两班,每班六小时。为了保证有足够的休息时间,车间决定所有男女工都不回家,用松、杉木板在工段旁边空地,搭盖两间通铺大房间,男女各一间。每间均可容纳一二十人休息。
各行各业都以自己的行动支援大炼钢铁。一到傍晚,厂门口一字儿摆开各种小吃、小点心,简直成了小食街。无论什么点心,每碗统一一角钱,不收粮票。对我们来说,工厂、车间的点心基本管饱,但还是有不少人要到这个“小食街”来换换口味。还有小货郎担,针头线脑的也送来了;新华书店也拉来了专车,在我们这里摆摊设点。后来联系厂工会,在楼下倒出一个空间,作为常驻纸厂的分店。
正在大家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我的脚掌弯被斧头砍伤了。初时还不觉得疼,直到冷风沁入皮内,才痛得呼叫师傅。师傅立即到隔壁机浆车间,把正在值班的舅父叫来。舅父找了一块布条来,将我的伤口扎紧,背起我就赶往厂医院急诊。医生给我清洗了创口,用羊肠线缝了几针,敷上消炎药,扎好绷带,由舅父背回我的宿舍。
大约一个多月,我都在养伤。起初的几天,三餐由舅父给我送饭,稍好一些,就自己拄着拐杖去食堂就餐。这段时间,我成了厂图书室和新华书店分店的常客。看了不少小说、戏剧、电影文学剧本。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暴风雨所诞生的》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作品;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海之歌》、《一本打开的书》等。还定阅了《电影文学》,零星购买了《中国电影》、《电影创作》等。
脚伤好了之后,仍旧回到调木工段。厂里各个食堂已开始实行饭菜一票制。就是凭一张票,供应一份菜(菜汤不收费)、饭量不限。到了午餐时候,全班组的饭票由我收齐,我挑着箩筐和汤桶,去食堂领取饭菜。为了测算平均每人每餐吃了多少饭菜汤,有人建议我将空担子过秤,吃完以后,再将吃过后余下的过秤,计算结果平均每人每餐消耗三斤食物。还有人特地在饭前称量了自己的体重,饭后再称一次,发现体重仅仅增加250克,怀疑所吃的食物到哪里去了。调皮的小伙子则说:“放屁放走了。”引得大家哄堂大笑,大婶、阿姨则掩嘴偷笑。
陈大婶对我说:“依俤,我给你介绍个妹妹好不好?”她一边说,一边将眼神瞟向在我右侧的小妹妹。她才十七岁,比我小两岁。这时候我又改作刨树皮工种,紧挨着陈大婶。这群女人仿佛拿我寻开心,需要跑腿的事儿,就“依俤,依俤”地呼唤我。反正我年纪轻轻,随叫随到。难得她们能够开开心心。此时她们在窃窃私笑。我也跟着傻傻地笑。
两次由厂部抽选人手参加的义务劳动补记在此:
一次是人造纤维厂基建工地的地面平整劳动。调木工段有电斧手加刘师傅和我等三四个。加刘师傅挑土,一次要两副担钩、两副土箕,挑起来快步如飞,结果扁担经受不了,断了两三跟。正在我们大家斗笑的时候,工地指挥部宣传报道的人来了,问我们有什么事迹需要报道的没有?大家七嘴八舌地嚷嚷开了。广播室的人要求我们写一篇稿件,大家公推我去。我跟到广播室,写了一段顺口溜交给他们,我刚回到工地,稿件就播出来了。
另一次是在现在的长途汽车站附近修“五一路”,干的是挖地基的活。还是加刘师傅一马当先。中午不休息,由厂部食堂负责送饭。
不久,我被调到化学制浆车间,到二楼的6#、7#打浆机台当学徒。由于我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学起来比较快,三个月后,就能独立操作了。与我的老师傅分班。我在甲班,师兄乙班,师傅丙班。
厂党委、团委号召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活动,车间与车间、机台对机台进行对口赛,操作员之间进行对手赛。这样一来,我和师傅、师兄就成了竞争对手。比赛的内容是:在符合规定的纤维长度和叩解度的条件下,班产量(干浆量)最多的为优胜。乙班师兄的成绩已经记录在台时记录本上了。我接手的是师傅遗留下来的半成品浆料。我查看了师傅两台机所装的干浆量,及它们已经运行的时间,和已达到的技术指标,认真分析需要再运行的最短时间。决定先加大下刀力度,解决它们的纤维长度,再回刀“细嚼慢咽”,解决叩解度。结果全程运行时间缩短了半个多小时。同时,在本班新装原料时,又加大浓度,使两台浆池的装浆量都超过了乙、丙两班。这样,我自然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胜过师傅和师兄,获得了优胜红旗。
厂团委差派几个青年工人,一路敲锣打鼓、燃放鞭炮,经过食堂、经过抄纸车间,一直来到我的机台旁,将一朵红花佩戴在我的胸前,将一张奖状递给我。我捧着奖状,回头注目车间一角的测验室,与我同班的上海姑娘小倪,此时正在对我会意地笑着。我应该感谢她。我所以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成绩,这里面也有她的一份功劳啊!
1958年初,厂里来了一批上海青年。他们被分配到各个车间。分到我们化学制浆车间检测室的两女一男,在福州人邵大姐的带领下,很快就掌握了半成品纸浆质量的检验技术,并能独立操作。小倪就是其中的一个。
检验室七个人,分成三个半班轮流倒换,与我们化浆车间的三班倒,产生剪刀差。因此,如果今天与小倪相聚同班,要过若干天以后,才能再次相聚。
小倪,十七岁,因小时候患了天花,大难不死,留下一脸的芝麻坑。车间里的工人并非出于恶意,爱戏称她“猫仔”(福州方言,与“麻子”谐音);久而久之;她也答应。但并不知道其中的含义。我却从来不这样称呼她,那样对人不尊重。她身材姣好,心灵手巧,轻言轻语,一天到晚嘴角总是带着笑容。
那一天我在洗衣房刷洗被单,小倪经过那里,看看只有三两个人,就走到我的面前,告诉我,中午她会来我宿舍,帮我缝被子。
其实,缝包被我早就会了。在家里,除了洗衣物以外,我的针线活比舅母强多了。在端生家学习小组的时候,女孩子都被会母的细密的针线折服了。她们围在会母身边,看她刺绣的枕套,啧啧称赞,对枕套四边的封口,以为是缝纫机干的活。我也跟在姐姐的身边,看了个仔仔细细。因此,舅母遇到需要缝缝补补的活,都交给我。
到了下午两点,我已经将干透的被面、被里收回来了。门外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正好,同宿舍的几个,上白班的上班去了,同班的也逛街去了,整间宿舍只剩我一个。我认定是小倪叩门,立即从上铺下来去开门,果然是她。她满脸带笑,芝麻坑也变成了花蕊。她手里带着缝被子的针和线,说:
“我把针线都带来了,怕你没准备。”
“谢谢你!”我深情地望着她,逼得她低下头去。
毕竟是上海人,在阁楼小空间住惯了,自然养成了许多应对小空间的本领。她不用在走廊上铺草席,就着下铺窄窄的单人床,将被里、棉絮、被面,折叠成一半一半,先缝一边,然后再缝另一半。很快,整床包被在她的巧手下缝好了。我自始至终都认认真真地看她操作,一床被子在她的手里就象摆弄小物件似的。缝好了,她咬断线头,将余下线尾的缝衣针别在胸前。她回过头来望着我。我也直直地盯住她。她羞涩地低下头,两手轻轻地搓着,似乎在想:“我有如此的缺陷,他还直直地盯住我,一定不会嫌弃我。”
我将叠好的被子递到上铺,仍立在她的身边。我拉起她的一只手,用另一只手抚摸她的手背,试探地说:
“倪,我们什么时候去看电影吧!”
“好吧!”
“什么时候?”
“你决定吧!”
我去台江的文艺剧院买了两张戏票,演的是闽剧《靖边记》。这出戏,到底演的是什么,我也不清楚,她就更不明白了。但我们能够如此紧密地坐在一起,让我始终拉着她的手,抚摸她的手背,心里感到十分的满足。既然看不懂,我们就提前回厂。正如相声演员马季说的,五十年代的人谈恋爱,是“各走一边”。我们怕路上遇上熟人,在万寿桥上就开始各走一边了。一个在桥东的人行道,一个在桥西的人行道。一直到厂区,也没有走在一起。虽然我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心却是始终在一起的。
我们在不同的倒班中,还时不时地会有相聚的机会。那一天晚班,我们又遇上了。车台前十分平静。小倪也只有一个人当班(另一个请假了)。忙完了活,我们紧紧地坐在一起,再没有人来打扰我们。只有头顶上的三五牌的名挂钟,在的达的达地计算我们平静的脉搏。我们在临门(其实是二楼的落地大窗)的方桌前坐下,将台时记录本的背面翻过来,各人取出自己的钢笔,你一句,我一句地交流心声。
我写:“前面游来一只大白鹅,”
她写:“后面的母鹅叫哥哥。”
我们彼此露出会心的笑,还交换了钢笔。
今天的岗位对手赛,正好我们又相聚了。而且又是夜班。我不停地调整打浆机的飞刀,需要即时了解纸浆质量的进展情况,那就要对纸浆进行多几次的测验。一般地说,在一个台时中,最多检测三到五次。今天,她却为我检测了不下十次。每一次我只要“哎”一声,她立即就过来取样,几分钟就能给出结果。为我节省台时立下汗马功劳。这时候,我胸前戴着大红花,手里拿着奖状,她一定看在眼里,乐在心里。所有的疲劳辛苦,都荡然无存了。从她躲避众人耳目,在检验室的一角,低头不语地偷笑的神态,我已经感觉到了她对我的真心。我以满怀感激的目光注视她,希望她能抬起头来,让我饱饱地看上一眼。但她一直不抬起头来。当别人在注意我时,我才收回眼神。
4
福州纸厂各个车间,都有定期出版的板报。化浆车间的板报栏立在通往食堂的大路旁。半月刊,每月1日、16日出版。因为所处的地段是大多数人必经之地,所以,刊头设计、文字抄写,以及文稿的内容,都特别引人注目。
板报的美术设计,由蒸球工段技工苏恩义负责。他爱好美术,功底较厚。每期都要画出不同的刊头。稿件的题头、题末的插图,都十分切题和精彩。文字则由我编辑和抄写。说是编辑,实际是从头到尾全部包办。因为,一线工人师傅虽有很多值得歌颂的模范事迹,但他们文化都偏低,都不会写稿。哪怕几句顺口溜都拿不出来。所以,每期出版前,我都要从采访、撰稿、编排,直到抄写在大白纸上,流水线作业全过程,一人担当。每期24个版面,最快也要忙乎三四天。到出版时间,工段长都会特批我们的假。我们就将广告色颜料、各种笔、纸,搬到大食堂里,占用一个角落,在那里忙着,有时还忙到深更半夜。
化浆车间的板报,无论从刊出的及时、版面的活泼、组稿的丰富、形式的新颖来看,在全厂都是名列前茅的。虽然没有这方面的单项竞赛,但只要从就餐、过路的工人经常在这里长时间驻足停留,就可以看出他们对刊物的评价。
厂里接纳了一批实习生,有的是退伍兵,有的是干部。他们是为苏联援建的项目之一——青州造纸厂作人事准备的。一个退伍的班长担任我们车间唯一一台精浆机的操作员。精浆机就设在检测室的隔壁。他在精浆机上的操作比我在打浆机早两个多月,已经十分娴熟,得心应手。安排在我这一班的退伍兵,是个山东人。他身体粗壮,但文化很低,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他来跟班当学徒,跟他说叩解度、纤维长度,根本听不懂,只能做些粗重的活。如:抬明矾或硫酸亚铁的大包装,将称好的明矾或硫酸亚铁倒入溶解桶里,加上水、通入蒸气,用小木桨将它们搅拌融化。在我所定的时间,再将这些溶液慢慢用勾桶打出来,加入纸浆池中等。除此之外,什么也不会做。我还是不能脱手离开。几个月时间,我是白当了一回“傅”。
与这些跟班学徒的退伍兵所不同的,化浆车间也来了一位管理干部。他是从广州抽调出来的,曾在广州纸厂见习一段时间,现在又来福州纸厂见习。
有一天,他突然召见我,还是在我当班的时间。我请示了曾焕祥工段长。他答应让我去,我的机台由他亲自代管。
我到了车间办公室,在工会主席引荐下认识了他。他姓周,我们就称他周干部吧!我们在会客室里一边品茶,一边聊天。广州人很看重饮茶。有人说,你去广州不要怕住不上旅社。你只要将预先带去的茶叶拿出来,与服务员一起品尝,准保你能住上。
他先作了简短的自我介绍,接着表达了渴望与我见面的想法。他说,他看了化浆车间的板报,觉得我们化浆车间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