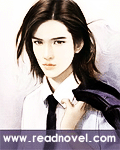岁月匆匆-第2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先作了简短的自我介绍,接着表达了渴望与我见面的想法。他说,他看了化浆车间的板报,觉得我们化浆车间真了不起,能出这么好的板报。为我们骄傲!他说他看了板报之后,就向工会主席打听,一直想和我见面,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
他从小品、相声、小说、戏剧……一直谈到电影。谈到最近放映的反特故事片《云雾山中》、《羊城暗哨》等。我们谈得津津有味。他提议与我合作,写一个反特主题的电影文学剧本。我欣然同意了。
正在我准备着手这一合作时,周干部调走了。接着,退伍兵学徒也随后离厂。后来才知道,这些变故是因为1959年赫鲁晓夫撤走苏联专家,青州纸厂下马所致。
1959年下半年,粮食恢复定量供应。随着粮食库存量的不断吃紧,粮食定量几乎是逐月减少。每个员工都发给一张粮卡,用于向食堂管理处购买饭票的登记。饭票、菜票从此分开,不再合二为一。原因是,在1958年的浮夸风中,鼓山公社原全国劳动模范曾“创造”了水稻亩产两万多斤的“卫星”,农业部门的秀才们用计算尺(当时的先进计算工具)算出,全市将有多少多少亿斤粮食可以入库。因此就有了《福州晚报》的元旦社论:《放开肚皮吃饱饭》和评论员的文章。厂矿企业、各行各业都吃大锅饭,居民户实行自报用量,已报的数量一定要买完。结果造成大量的浪费。纸厂食堂的背后建立一排猪栏,每餐吃不完的大米饭,倒进猪食槽里,连猪都吃腻了。再加大炼钢铁,使许多人不务正业,丢弃在地里的大量粮食没有及时入库……,所以,造成粮食供应的后续困难。到了1959年下半年,这一困难更加突出。为了解决问题,学校、工厂、企事业单位纷纷到农村圈地办“农场”。纸厂也在三叉街以南的农区划了一片地,挑选几个老农去种植蕃薯、青菜,同时也抽出一部分青年去作帮手。我和检验室的徐家驹也在其中。临行前,车间举行小型欢送晚会。我编了一段相声,和家驹同台演出。徐家驹是检验室中唯一的男同志,是和小倪从上海同来的伙伴。他写得一手独特的三角形的异体字。
5
1960年6月,闽北山区连降暴雨,山洪爆发,漂流的木材堵塞了万寿桥的桥洞;桥西与桥东的水位高低相差十几米。如不及时抢救,福州城区通往仓山的唯一一座大桥,将被强劲的洪水掀翻。情况十万分危急。市里组织了抢险队,主要由部队担当。任务是将堵塞的木头一根一根拉出来。没有什么机械设备可以使用,只能人工操作。听说这一场抢救中牺牲了五六个战士。
我们福州纸厂接到夜间巡逻和桥头警戒任务。我和抄纸车间的姑娘陈雄等二十多人被选。前后十天左右。具体工作是:晚班,负责巡逻从江边向西的沿岸木材垛头,发现偷盗,当场捉拿。巡逻沿观井路、麦园顶,至福州九中、人民公园……。这样从东到西地绕一圈,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一趟下来,在仓山桥头的教堂(或是银行)休息十来分钟,然后再进行第二次巡逻。我们这一班共有十五六人,只负责夜班。到天明八点交给白班。白班主要负责把守仓山桥头,向过往行人讲解大桥的危机,提醒行人注意安全,有序通过,不要拥挤……。一般天明后,行人就开始来来往往了。因此,我们在未交班之前,已经在执行白班的任务了。
陈雄一班姑娘胆子小,巡逻时喜欢扎堆,手电筒又都归她们。我们男孩子只好摸黑。特别是在福州九中那一段,很长一截没有路灯,她们就往你身边挤挤挨挨。我还真有一点想她。想她那天真活泼的模样。但任务完成之后,我们就没有再多见面了。有一次去抄纸车间还遇上她,只是简单地打个招呼:“哎,你好!”“你也好!”如此而已。
年轻人结交朋友应当慎之又慎,一次失足,将留下终生的悔恨。这是指绝大多数人说的。对我则另当别论。我觉得,即使因此贻误了我一辈子,使我终身屡遭坎坷,也不悔恨。因为不如此,就没有如此丰富多彩的故事发生。有人说:“苦难是金”。对我来说,一点也不过分。
调木工段电锯手严仁光,是浙江省平阳县人,挺聪明能干的小伙子。这一天,他突然来找我,取出一本过期的学生证,让我给他涂改就学日期。以便他弟弟在来往鹰潭、福州之间,可以继续享受半价火车票的优惠。减轻他生意中的车费负担。我觉得很为难。但经不起他软缠硬磨,只好用铅笔擦擦去原来的字样,用毛笔写上新的日期。
过了一阵子,严仁光被捕了,食堂里张贴了有关他的罪行的公告。罪名是:伪造证件、投机倒把(当时不允许做小生意)。
粮食供应更困难了,食堂从采购来的稻草中发现还有未脱尽的稻谷,不管实谷瘪谷,统统收集起来,洗净,用磨推过,加水沉淀,取出沉淀物,再加上纯米浆,做成黑褐色的米粿,按纯米粿应收粮票的一半收票出售,很受工人的欢迎。稻草中的遗谷毕竟有限,后来直接用稻草磨浆的沉淀物加米浆,蒸出来的米粿就更黑了。
这些办法虽然能解决部分人的饥饿,但毕竟数量不多。每天出笼时都要排队抢购,供不应求。此时我的每月粮食定量已降至35斤以下,正值青春成长期,显然不够维持长身体的需要。况且,每月工资28。50元,其中15元上交给舅父,自己只剩下13。50元。大锅饭时期还不成问题,现在可大难了。我在一台新建的打浆机旁的废纸堆里,发现了几张旧粮票,就捡了起来,居然还可以使用。又发现用牛皮纸印制的福州市一斤粮票的图案十分简单,就去寻找色度近似的纸,用毛笔、黑色钢笔,在宿舍无人的时候,偷偷地临摹仿造。我将它带到下渡的街道食堂去买熟食,找回来的真粮票攒起来,以备急需。这样一来,总共攒了有30多斤。
严仁光的案子没有牵涉到我,也没给我留下应有的教训。生活上的无助,使我看重自己的小聪明,一多半也是抱着侥幸的心理,再加上变造食堂的点心票等。我终于铤而走险,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那一天,我还在纸厂农场挑水浇菜。公安局的两个民警来到地里,跟负责人作了交代之后,将我带回厂保卫科。问了几句话之后,由保卫科的一个干事领着,搜查我的宿舍。保卫科干事从我的衣箱底搜出一些粮票,点了点,问我:
“这就是你换来的真粮票吗?”
我回答说:“是。”
“还给你了。”他把粮票又塞进箱底,和民警一起走了。
他们走了之后,我清点一下粮票,少了三张三斤的。心里直犯嘀咕,这不是明偷暗抢吗?
过了三两天,民警正式来将我带走,送到看守所,关了十五天。放回来一个多月,仓山公安分局正式将我逮捕,仓山检察院立案,法院判处我有期徒刑六个月。我宿舍里所有的书籍及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的来信和毛主席照片,都不知去向。
判刑后的第二天,谭干事带着号房钥匙,老态龙钟地来到我关押的那一间房,点名让我出来,将我送到东门水头劳改队改造。
在水头监房不到一星期,约有40名人犯被点名出场。由专职干部和武装带领,组成一个板车运输队。为劳改队联系业务,创造经济效益。对我们的报答是:提高粮食定量、放松强制管教。
我们这一批犯人,到水头村租用民房安营扎寨。由一位熟悉市区的老犯人,东奔西跑地联系搬运业务,并在每天清晨出车前,将提货单交到每部车头的手里。
我们三人一部硬轱轳木板车。一个当牛头,两个帮手。所干的都是一般搬运队不愿接的笨活、重活。运的都是大型的机器部件,厚重、大块的钢板等,由于收费低,活儿接连不断。装车的时候,我们往往几部车的人手一起合作,单部车是根本无力装车的。而且,无论是装车,还是途中,特别是上下坡,危险性都很大。有几次都险些出事故。对家在市区的人来说,这种相对自由的劳动改造,可以在白天很长一段时间里离开伙伴,偷偷回家与妻儿老小团聚。晚上11点归队,都不会追究。但对无家可归者,则不是什么很好的差事。因为,在他们的同伴去约会的时候,他们只能绻缩在街头,在厂区、在车站,独自伤怀。
这一段时间,虽然有每月60斤的定量,但油水太少,又干特别粗重的活,早出晚归,依然是饥饿难忍。有亲属的,借机到亲属家里取些钱粮来贴补。我虽然也回舅父家去,并不能得到什么帮助。有一个同伴,则趁中午休息的时间,衣衫褴褛的到味中味等饭店去,转一圈出来,然后向我们夸口,说他今天家里给了多少钱、多少粮票,刚刚在饭店吃了什么什么菜,一碗多少钱等等。真是苦中作乐!
当时,市面上物资特别匮乏,一碗清水海带汤一角钱,也要排队。在我们去火车站东站的路上,有人将桃树上割下的树胶,煮成酸辣汤,一碗也卖一角。虽然明知吃了对肠胃有害,还是有不少人争着买。但只能偷着卖,因为是“投机倒把”的“资本主义”行为。
六个月的刑期超过了几天,干部通知我回水头去。我领了释放证,带着简单的行李,没有人来接我,自个儿回舅父家去。当天上午,就去洋中派出所报了户口。所长找我谈了一席话,自然是改过自新、重新作人的话题。
我觉得,有些话似乎说得太晚,或者说得不是时候。对一个可塑性很大的年轻人,如果政府机关能出于父母疼爱子女的心,在他的生命的转折关口,给他必要的呵护与帮助,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悲剧发生。
1986年 4月,当我收到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的刑事改判判决书的时候,心情是十分复杂的。判决书说:
经复查认为:被告人胡振铎由于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在国家暂时困难时期,竟伪造粮票11张计42斤及伪造、涂改厂里的菜证等。原判所认定的事实属实,但视其情节显著轻微,尚未构成犯罪。据此,原判以伪造粮票案定罪科刑不当。现经研究决定,特改判如下:
一、撤销一九六一年三月六日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刑字第7号判决;
二、宣告胡振铎无罪。…………
判决书最后例行公事似的提出,如不服本判决,允许在十天之内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虽然,42斤粮票中还含有很大的水分,其中有十来斤是从废纸堆中得来的,并非伪造。但面对这一份晚点25年的判决书,上诉又有什么意义呢?
6
纸厂是回不去了。我开始出去打零工。先到横街巷的臭货师傅那里,学做泥水小工。每天早饭后,到他家去,在屏风后捣泥灰。这是学徒工的第一个关口,也是最苦最累的活。就是在石灰里加上纸屑作筋,喷上水,用脚踩、杵捣。任凭石灰腐蚀你的肌肤,要喷一次水,翻一遍灰,再踩、再捣,直到它成为柔韧的泥灰浆。每天早早地出去,晚晚地回来,还要忍受入不敷出的饥饿。
偶尔也有开心的时候,那就是单独跟随泥瓦匠去给雇主整修屋漏。那一次跟随弯俤师傅(其实他不叫这个名。因为领工资需要印章,他拣了这个章,就随了这个名,连臭货师傅都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去中亭街一家大房子修屋顶。我挑着一小担灰泥,大约四五十斤,跟随在师傅背后。到了雇主家,我跟着师傅上了屋顶。他坐在屋脊上,开始悠悠地抽他的竹烟斗。师傅不忙乎,我作小工的也乐意在屋顶上陪他闲坐。竹烟斗比纸烟费时间,这是他的工作所需要的,就是俗话说的“磨洋工”。他告诉我,这家的活儿顶多半天工夫,但我们要拿他三天的工钱(他每天三元六角,我每天八角)。唯一的办法就是磨时间。磨时间还要不让主人发觉出来,那就是在屋顶上,迅速找到屋漏的关键所在,但不急于接近它。舍近求远地从不漏雨的地方入手,随时往地面扔几块瓦片,好的坏的都扔(因为屋主根本不会到屋顶来,他们也不敢来),造成一些响动,让东家以为我们正在忙乎。到了接近中午,东家看看我们还没有下楼,就给我们备了午餐。再弄一些响声,东家就招呼我们吃午饭了。主人好饭好菜招待我们。我们也不能让他“失望”。吃饱喝足,立即上屋顶,假装工紧,使东家以为工夫很难。有时,东家还会送卷烟给师傅。到了师傅认为可以收工的时候,再忙它小半个小时,在关键处抹几把泥灰,就下了屋顶,回到地上。东家还向我们千恩万谢。我们心里窃窃自喜地凯旋而归。
当时,社会闲散人员寻工,都归居民委员会管理。任何单位、个人,需要雇用杂工,都跟居民委员会联系,工日、工价,都由他们双方决定。做工的,必须由工头开出工资表,交居委会审批,由居委会开出发票,向雇用单位或个人收款,扣除管理费后,交给工头,再由工头凭工资表盖章发给个人。
小工生活持续两个多月。在福州大学基建工地,因为体力虚弱,经不起烈日暴晒,我突然头昏目暗,天旋地转。同伴将我扶持到大榕树下的自来水水龙头边。我打开水龙头,闭起眼睛,在冷水下一阵子猛冲,才清醒过来。
舅父在白马桥附近,联系到用棉纱加工鱼网线的活儿。他比照他人的绞纱机,自己设计制作了一部。我从此在家里足不出户2开始干这个活儿。有时赶工期,从清晨六点开工,要忙到晚上十一、十二点。家里伙食不好,粮食不够吃,要买高价的薯米来添补。舅父每天抓了两把薯米在一只黑色的陶罐里,送到横街巷的食堂去蒸。一连吃了几餐,再加上劳累过度,竟引起躬身屈腰、止不住的咳嗽。虽然吐出血丝,也没有请医用药、调理和休息,只是支撑着。那时年轻,有什么病,扛一扛就过去了;却不知它给后来的身体留下隐患。
时光真快,大表弟也上高中了。他的学校在十五中,就是现今长途汽车站的位置。他从小有腿疾,这么远的路上学很困难。每天清晨、傍晚,都由我背着他来回接送。后来稍好一些,自己学会骑自行车,再不用我接送了。
7
趁着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台湾的蒋帮蠢蠢欲动,狂妄叫嚣要反攻大陆,打回老家去。政府决定在福建修建多条国防公路。
一九六二年七、八月间,居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