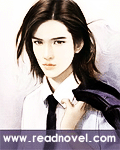岁月匆匆-第3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床单、被褥,都是新的。你放心睡吧!我走了。”
我睡到半夜十一点钟左右,门外传来多人说话的声音。有人急促地敲门:
“开门,开门,快开门!”
我打开门,看见这气势汹汹的一群人,不知出了什么事。就问:
“什么事?”
“什么事?小张呢?”
“走啦。”
“走啦?事情办完啦?”说话的是张英的舅父,人高马大,要说打架,我完全不是他的对手。在他身边,那个矮小龌龊的人,估计就是告密者。
这是怎么回事?我不明白。他们肯定是误会了,以为我正在和新媳妇寻欢呢!所以急急忙忙从山漈伐木场,十多公里急行军,赶来“捉奸”的。
“事情办完了。她回去了。”我以为他们所指的,是张英在城里该办的事办完了。
这句话正好给他们作了把柄,“舅父”一巴掌打在我的脸上。
“你怎么打人呢?”我伸手抚摸被打疼的脸,“我是说,小张来城里办完事,回山漈去了。她在这里遇上我,见我等车辛苦,把房间钥匙借给我,让我在这里住半宿。她还交代我,把钥匙带到青州去,亲手交给文贵兄。”
“小张她什么时候回山漈的?”舅父问。
“天黑之前,五点多钟。”
“我们怎么没碰见她?”舅父问身边的人,“你们看见了吗?”
“唉,唉,我好象在山漈场看见她了。”告密者突然觉得自己好心办了错事,结结巴巴地说。
“在哪里看见她?”
“在,在小杂货铺门口。对,真是她。”
“好你个臭小子,把我们几个折腾到这里来,谎报军情。看我们回去怎么收拾你!”舅父气极了,对我说,“把钥匙交给我吧。火车也快到了,锁上门,没你的事了。走吧!”
我穿好衣服,离开林业家属区,还未忘了那新被新褥里的温馨气息。
张英夫妇都是山东人,新近在青州火车站的工棚结婚。虽然她的长相并不吸引人,但因和她丈夫的年纪悬殊十几岁,可能有些不情愿,所以,见到我们年轻人,总喜欢接近。这就引起他们老乡的疑心。本来是一件很正常的借房用房之事,被歪曲成奸情苟合了。十几年以后,我从劳改农场平反回来,在一个边远的林区养路班遇到她的丈夫杨文贵。他热情地领我到他的家去,见过他的妻子和孩子。孩子都很大了。我在他们家喝了水,没答应留下来吃午饭,也没提起那段不太愉快的往事。他因为严重摔伤,对往事好象不太记起了。他的妻子,显然老多了。无情岁月,岁月无情,这是任何人都抗拒不了的自然规律。
我是不是要在这山区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呢?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呢?请看第八章《燃情岁月》。
第八章燃情岁月
工作固定了,生活稳定了。胡振铎正当风华正茂的年月。是该成家立业了。但没有长辈的维护,谈何容易?几个对象都被人干预而化为泡影。在热心人的帮助下,终于娶妻生子。生得一个女儿……
女儿在文化大革命的种种口号声中诞生,经受了“枪林弹雨”的洗礼,当然新家庭的生活是幸福美满的。但是……
1
从青州到潩洲的林区公路,由于人手多,将三百多人分成十二个班组,每班组25—28人。沿线工地几乎全部展开。收工的时候,从最远的工地一路集结下来,人头挤挤,蔚为壮观。
在山上指挥部路边,设立一排黑板,每月出版一期黑板报。组稿由福清人、工会干事陈自义负责。他将黑板取下一块,安放在他单人宿舍的黑板架子上,写写擦擦,两三天了,还未见一篇完整的稿子写在上面。我好奇地进屋看了看,他又放下粉笔,回到临窗的办公桌前,写写划划。看样子陈干事似乎很辛苦。我正要出去,被他叫住了。
“小胡,你会不会写粉笔字?”
“会一点。”
“能帮我把这篇稿子抄完吗?”
“我没时间。”我不喜欢他那种张扬的风度。记得一次我和思生一起路过他的房前,被他招呼进去(因为我们都说福州话),他先是拿出《闽北报》上刊登的、一篇不足十平方厘米的小文章,向我们吹嘘一番。我听着就觉得恶心。我此番进他的房间,本意是要看他笑话的,却被他缠住了。
“没时间?我可以跟杨队长说说,让你抽出两三天的工夫来帮我。你愿意吗?”
“你自己决定吧!”说完我就走了,根本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果然,第二天,杨队长派人通知我,让我去找他。杨队长告诉我,队里要召开第二届职工代表大会,让我抽出几天时间,帮助陈干事准备材料。
这样一来,我只好去帮陈干事抄稿子了。那篇稿子不一会儿就抄完了。他就象难产的妇女一样,再也拿不出新的稿子,我只好等。
吃晚饭的时候,我和小萧、思生谈起陈干事。包打听小萧早有定论:他是一个师范生,毕业后分配到山漈伐木场。在老家已经有了对象,还未成婚。虽然陈干事比我们年长几岁,但他很会打扮,头发油光可鉴。经常喜欢混入粉黛之间。所以,所谓的对象、未婚妻,无论在他自己,或是对方,都是一个未定数。
陈干事将写得半半拉拉的稿子扔在桌子上,时间已是晚间十点多了。好象写不下去了,黑板报又赶着出,我催他出稿,他就将一堆有关职工代表大会的材料扔给我,让我去整理。他早已阿欠连天,急着上床睡了。我花了一个晚上时间,连摘编、带抄写,将四块黑板都弄好了。天色已经大明。我放下手里的活儿,走出门外,张开双臂,伸了伸懒腰,总务武为己也从隔壁、他的房间兼卧室出来,和我一样张臂伸腰,对我说:
“小胡,我们都赚了一个晚上。”
“你也加班通宵吗?”
“是啊!我正在筹划职工代表大会的伙食安排,赶制一份报告给党支部、工程队审批呢!”
“是吗?”
这时,簇琴从她的住处出来,上厕所去,路过这里。她向我微笑招呼。返回时,绕道来到陈干事的宿舍,认真地望着黑板架上刚写好的黑板报,不由赞叹道:
“胡老师,这黑板报是你抄写的吗?”
“啊。”
“一个晚上写到天亮?”
“你怎么知道的?”
“刚才,你不是在跟老武说‘赚了一个晚上’吗?”
“这丫头!你真会‘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哪!”
不久,陈思生离开了我们,被调到沙县水南的林业汽车运输队去。他过去有一点钳工基础,到那里去学修车,也在那里成婚安家。
职代会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我仍回班组去。
有一天中午收工时,簇琴和小吴两人抬着一根弯弯的、被火烧焦了树皮的木头,经过我们的工地。我们的班长也招呼大家收工。这时候,小吴打头,急急忙忙赶到我面前,向我招呼一声:“小胡”,立即将一张折叠得严严实实的字条塞进我的手里,然后若无其事地继续走去。
小吴他们再精明,也瞒不过我身边的人。有两个山东大哥立即靠近我,向我打起马虎:
“胡——”他们总是用轻轻的语调,这样亲切友好地称呼我,“谁给你的信,快打开来看看。”
“什么信,那有什么信?”我将字条塞进裤袋,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
“胡,你这小子,你当俺们都是瞎子啊!”
两个山东大哥假装要搜我的裤袋,我急了:
“就是有信,也不能给你们看。”
“这不就结了。不叫看,俺们当然不看了。可你不能骗俺们哪!”
我的脸,早就红到脖子根了。我急急忙忙扛起锄头,赶紧回到自己所住的工棚去。我躺到床上,从裤袋里取出那封信。我当然知道那是簇琴写的。我小心翼翼地打开它。那是一张32开的小学生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我想一定是从她弟弟那里得来的。只见那上面用清秀的字迹写着:
胡老师:
您好!
我再不能和你交朋友了。我爸爸妈妈已经觉察到了。他们都反对我们来往。我很为难。希望你不要灰心丧志,好好工作,将来一定会有比我更好的姑娘跟你的。因为你是个好同志。
祝
平安!
你的学生
张簇琴 上
1965年8月
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
从此以后,她不再喊我“胡老师”,见了面照样和我打招呼,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好象我们之间,根本就不曾发生过什么事。只是对我的称呼改了,唤我“叔叔”。
我心里那个气呀,无法表达。我心想,你这个老古董,什么书记?年轻人交往有什么可指责的。我要写一封信,质问质问你。信写好了。趁着夜色,我穿过轨道,爬上山顶,来到他的窗前。他正在窗前的灯光下做着什么。我唤一声:“张书记”,他推开窗户,还没有看清我是谁,我就将信递给他,溜走了。自然是没有回音,永远也不会得到他的答复。
2
两个月后,我们三班的工地往里延伸,住处也迁移到临近青州纸厂桥头、铁路线旁边的一座闲置的民房里。三开间的民房让我们整修一番,变得十分合适。左开间打十几张床;右开间隔成三个单间,第一间为总务兼保管间,第二间作我们的仓库,第三间门向北开,作女工小郭的寝室(虽然她丈夫不在我们班组);在小郭寝室的门前,搭上雨盖,支两口大灶,作为班组的伙房。小郭夫妇的小灶也支在这里。正厅打六张床,我就在正厅安歇。正厅以北、与伙房平行的是天井,便于采光。
小郭和她的丈夫老赵喜得贵子。小家伙虎头虎脑的,很逗人喜爱。小郭产假期间,从山东老家,将老赵同父异母的妹妹叫来,给嫂子看孩子,兼做一些家务活。
休息日,小郭在家,小赵有机会和我一起上山去拾榛子,就是一种很小的野生栗子。我把拾来的榛子都交给小赵,由她煮熟了,分给大家吃。小赵另外给我留了一小包,用她的小手帕包着,带在身上。那天,她和哥哥嫂嫂、我们大家一起去青州造纸厂毛竹搭盖的临时礼堂看电影。她找机会把榛子塞在我的怀里。
青州造纸厂是前苏联斯大林手里,援建我们中国的163项大型项目之一,完全是按照国家级企业来筹建的。1956年动工,已经建了部分车间、连接青州火车站的专用铁路、青州铁路桥及三陵柱形的塔式招待所,和一些前期的造纸设备。1959年,赫鲁晓夫上台后,大肆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祸及对中国的援建项目。将所有苏联专家都撤走,项目设计图纸也一并带走。我国因此在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又遭受一次大劫难,独自承受巨大的经济损失。1965年,在经过几年的阵痛之后,我国自行设计的复建方案推出,青州造纸厂重新上马。一批工程队又在工地活跃起来。其中就有小萧儿时的玩伴,他未来的小舅子潘威也在内。
小萧已经不和我同一班组,但他经常去青州造纸厂,都要路过我们住处。给我们带来纸厂最新的文化活动信息。这一天周日去看慰问演出,也是小萧送来的消息。
山东是老根据地,经济不发达,群众的生活比较苦。据说在一次中央木材调剂会上,山东提出,中央分配的木材不够用。我们福建的叶飞则说,我们有的是木材,只是缺少人手去砍伐。双方因此达成协议,中央除按计划拨给山东的木材外,由福建另行支援若干。这部分木材,则由山东出人,来帮助福建砍伐。于是就有了一大批山东农民背井离乡来到福建山区。沙县等地为此筹建了若干大型的伐木场,老赵他们都是1958年前后来到福建的采伐工。
小赵正名叫田凤,是老赵的继母所生。她还有一个姐姐,和老赵是同胞手足。
小赵除了看孩子、做家务以外,都在家里,什么地方也不去。我自从收了她的礼物之后,心里燃起对她的同情。据说,她的生母在赵家地位不太好,因此小赵来这里并不十分情愿。虽然她才十七岁,也想早日寻个能够和自己合心合意的人,过上一辈子。这样,我们就有了共同的心愿。
这一天,我身子有点不舒服,请假休息在家。工棚里除我和小赵以外,再无旁人。她抱着侄儿,到我的床上来玩,不经意被小侄儿拉下一泡屎。她十分紧张,脸色都变青了,怕我责备她。但我根本没有责备她的意念。我帮她扶着侄儿,由她来收拾秽物。她给孩子换了裤子,又用湿布擦拭了我的草席,一切恢复如初。我说:
“你紧张什么?谁不会有孩子,哪家的孩子不会弄脏床铺呢!”
她给了我深情的一瞥,让我感到由衷的温馨。
这段时间我的心情特别地好,一有空就练习唱歌。那时候练歌没有辅助设备,没有收音机、录放音机、VCD,只能看着歌谱,一句一句地练熟,然后再配上歌词。当时流行的歌曲也不少,都是纯情的,曲调优美、豪情奔放。如马玉涛演唱的《马儿啊,你慢些走》、《洪湖水,浪打浪》、《红珊瑚》、《看天下劳苦大众都解放》、《刘三姐》、《红岩》等等。我练了一首新歌,就在工地上,边挑土边背诵歌词,慢慢积累下来,会唱的歌越来越多。因此,我一上工,工地里就热闹了。我是从出工唱到收工,口也不干,人也不累。简直成了基建队不费电的功放设备。哪一天在工地上听不到我的歌声,一定是我这台“设备”出故障了。第二天必有人问我:“为什么昨天没有来?”
我虽然不是正式的记工员,在月底结帐的时候,班长却叫我去结算工资。因为我的手头比较麻利。我最怕返工,所以特别认真细致。我取来每月的工程结算单后,从累计工分、工分单价、每人应得,到制成工资表,一次性完成,只须半天时间,而别人要开二到三天的杂工。
这个月,我做好工资表,到青州山顶指挥部找林会计核对。这个山漈来的会计十分了得,他能双手打算盘。工资表交给他,他两只手拨拉两台算盘,十多分钟后,只要两台算盘上的数据相同,就算准确了。我的工资表核对完,已是午饭时间,去出纳小杨会计处领款是下午的事了。这时我路过三个单身女工的宿舍,就是总务老武住处以西的第三间。那里住着簇琴、小杨和小李。这一天两个上沙县去了,只有小李在。
小李出来迎接我,招呼我进屋里坐坐,我就顺水推舟进了屋。小李随手把门栓闩上。
小李是老李妻子前夫的女儿。老李黑黑瘦瘦,高高的个儿,虽然早年在支前民工队伍中入了党,却一直没有娶到媳妇。1958年来福建以后,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