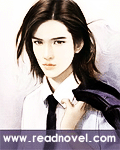岁月匆匆-第3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人家难堪。
说起这两个男人、一个女人之间的情谊,是绝对上好的。他们都是浙江平阳人。从一起做民工,转到成为林业工人,都在一起。阿兰十分漂亮,虽然已经三十好几了,仍然风韵犹存、很吸引人。见了她容貌的男人都会议论,女人也不例外。他们每天三餐都在一起吃饭。一男一女俩孩子好象共有的。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当然,别人的妻子总是别人的,沾不到一块。谁知就这么一次,走火了!还不知道事情有没有办成?
这件事之后,金春特别警惕。以下就是我要补充的第三件事。
平时,我到小妖怪家坐久了,金春就站在平房的东头,向西高声呼叫。等我回到房门口,她立即退进门里,拿起门后的短木棒,指着我的鼻梁说:
“说,拉什么呱去了?是不是看上狐狸精了?那福州娘们儿,又会唱、又会跳的,你心里痒痒啦!”
我无可奈何,只好尽力安抚。下午上工的时候,小萧特地问我怎么回事。我如此如此的告诉了他。他说:“看我的。你只要好好配合就行了。”
第二天正好是星期日。小萧一大早到青州造纸厂去,买回猪肉、韭菜、面粉、佐料,放回宿舍,就过来找金春:
“嫂子,帮帮忙。”小萧那亦诙亦谐的样子,让金春半信半疑。
“帮什么忙?”
“帮忙包饺子啊!”
“你老婆不会吗?”
“你不知道吗?福州女孩子只会唱歌、跳舞,哪会做包子、包饺子?你帮帮忙,不然我买回来的肉都要臭了。”
“好吧!”金春把孩子递给我,说,“你前头走吧!”
金春去了有一个多小时,回来了。对我说:
“这小妖怪今天请什么客,买了一大堆肉、五斤面粉,非得我帮他包完,弄到现在才歇手,累死我了!”她一边说,一边甩手臂,活动筋骨。
金春伸手要接孩子:“来,华儿,吃吃奶。”
我将孩子交给她。趁着金春背转身的工夫,小萧在平房的西头向我打手势。意思是让我不要生火做饭。
不一会儿,小萧又来了,嘻皮笑脸地:
“胡大嫂,多谢你了。你帮忙还要帮到底,把饺子煮了。”
“煮饺子也不会?待锅里的水开了,扔下去就是了。再开了,添点凉水,让水止沸,再开了,再加凉水,如此三次,饺子就熟了。”
“哎呀,你说了一大套,我记也记不住。还是老师傅亲自出马,指点指点吧!我们俩口子正等得焦急呢!”
“我也要做饭哪!”
“让胡大哥做吧!你只管帮我们下饺子。”
饺子煮好了一锅,金春回来了,疑惑地问:
“怎么还没生火?”
小萧随后追过来:“生什么火,我那边饺子还吃不完呢!”
“你不是要请客吗?”金春说。
“就是请你们呀!”
金春总算明白了:“噢,原来是你们两个合伙蒙俺哪!俺不去!”
我和小萧推的推,拉的拉,把金春弄到小萧的房间里,在小桌子边坐下。小萧的妻子是幼儿园的老师,没有脾气,笑着脸对金春说:
“来,小徐,一起吃。这是你煮的第一锅饺子。我再去煮第二锅。你们先吃吧!”说着,她就到房前杉树皮搭盖的小厨房里。
金春不放心,跟随出去:“你会煮吗?还是我来吧!”
两个女人把饺子都下好了,回到桌旁。小萧打开一瓶地产的玉露酒,给每个人斟上小半碗,就开始他今天的话题。
“小徐,你看我的老婆漂亮吗?”
“大城市里的人,细皮嫩肉的,自然漂亮了。”
“所以啊,这么漂亮的女人,我自己还疼不够呢,能让小胡沾便宜吗?”说着,他搂住妻子的脖子,就要亲嘴。妻子推开他:
“别没正经的。吃,吃饺子。喝酒。”
一场误会就这样化解了。
擦枪走火事件发生之后,朋友们都为当事人老韩的婚事操起心来。老韩四十多岁年纪,矮矮的个子,相貌不太佳,要给他物色对象确实不容易。好在山东、安徽有的是受穷的家庭。为了改变生活条件,牺牲个把女儿,也不会太难。后来,安徽回乡看家的,给他带来一个28岁的大姑娘。这姑娘臃臃肿肿,个子比老韩高出半个头,相貌也不用提起,好在是个女人。是个女人都能做男人的妻子。他们班组为俩口子举行了简单的婚礼。谁知洞房之夜刚过没几天,就出了一件事:那天一大早,老韩家的从房间里跑出来,顺着斜坡下到小溪边,坐在洗衣石板上,双脚泡进水洼里,上下扑腾,溅起一串串水花,嘴里大喊大叫:
“我要死了,我不活了。我要跳河了!”
人们好奇地披衣出门,看她就在食堂边上的水洼里捣动双脚,那浅浅的流水,就是整个人躺下去,也淹不死人。娘们儿、媳妇报以嘻笑,仍旧回房去了。老韩则站在平房边、公路护坡的高处,大声咋呼:
“让她跳。跳啊!怎么不跳啊?淹死了才好呢!”
这场大姑娘清晨跳河的短剧,在人们未正式起床之前,收不到预期的效果,草草收场了。
我们工地一直往正地延伸,从三工区我们的住处到新的路段,有五公里。我们不再盖工棚、不再搬家,开始实行每天一班制。中午派人去食堂挑饭,这活儿一般都是我担当。每个人都有自己饭盒的编号,我必须用纸张记下来。如果忘了带纸张,就摘一片芋头叶子,掐根短木棒,在叶子上划字。
在这段工地还有一段插曲,就是安徽的大龄青年杨富贵,三十六岁还未娶妻。大姑嫲嫲被他央求不过,从山东给他介绍一个对象,二十六岁,为他们操办了喜事。因为小王出门在外,会和山东老乡问好请安,杨富贵疑心重重,甚至请假在家里守护妻子。发现妻子与老乡说过话,立即将小王拉进房里,要她脱下裤子给他检查,是否有别的男人留下的印记。这对夫妻闹了几个月,终于不欢而散。听说小王回山东后,忧郁难耐,加上心脏病,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8
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金春因为担惊受怕,回山东老家去了。
正地工地结束以后,我们三班28人先行搬到高桥杉口去。暂时住在农民家里。每天上山砍伐毛竹、杉木。搭盖工棚。为后续班组打前站。
三个多月后,我实在忍不住寂寞,一封又一封信地催她回来。1969年8月2日,已经担任杉口伐木场副场长的她二叔让人捎信来,说金春领着孩子回来了。我从村子里赶出去接她。到村子的第二天,就分娩了。大约是一路的火车、汽车,长途劳顿所致吧。刚出生的是个男孩,房东老婆婆接的生。也许是生锈的剪刀没处理好,得了破伤风,牙关紧咬,手脚发颤。我们在老百姓家里也没有主张。
过两天,我们在村头风水树对面河边的工棚盖好了。为了减少对村民的叨扰,我们一个班先搬离村庄,到新工棚住。新生儿也带过来。当时只有我们一个班在这里,没有随队的医生。我们俩都年轻,不知道该怎么办,眼睁睁地看着孩子抽风六天,就死去了。安徽的吴华有帮忙,用一只新土箕装着,到后山上找个地方埋了。一条小小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
过了几天,我们正在农民的晒谷场上集中,准备上工。一只下山到溪边饮水的山麂,被山上放羊的小孩一轰,竟越过溪流,闯到晒谷场来。晒谷场的四周有竹篱笆围着,我们一群人分开围堵,老百姓见了也来参加。山麂一跳一蹦,想跳出篱笆,没有成功。它突然钻进一个农民的胯下,没逮着,被我们工人逮住了。农民说,他们也出了力,该分一份给他们。我们不会宰杀,请农民中会宰杀的将山麂杀白了,分半胴给他们,让村民们分享。我们的半胴,由炊事员老梁烹煮了一大锅,每个人都分得一小碗,味道香嫩极了。俗话说的一点也不错:山里好吃麂、鹿、獐;海里好吃鱼翅、马鲛、鲳。
大队长老王(现在称村长)只生一个女儿,二十八岁了还未出嫁。一是因为相貌一般般,二是他们要招上门女婿,还没找到适合的。这一天,老王大办宴席,请村里、村外的亲朋好友,为女儿举行隆重的婚礼,把我们全班组都请去。我们每人都包了五元的红包作为贺礼。在酒席未开始之前,自然是闯新房。老王女儿的新房在当时确实十分气派,真是应有尽有。在楼下正厅,收礼包的桌子上,摆着一张四开的大红纸,密密麻麻地写了许多毛笔小楷字。原来那是男女双方签订的合约。
合约规定:男×;×;×;自愿入贅王家为婿,婚后若生育若干子女,当依长次划分归属。即女方为长,男方为次。比如生得两男两女,即第一男(长男)依女姓,姓王;第二男(次男)依男姓,姓方。女儿亦是。若生得多男多女,亦依此类推。为免除日后纠纷,特立合约为据。…………
当时还没有强调计划生育,但如此滑稽的文笔也只有乡村的老学究写得出来。赴一次宴,长一回见识。
新盖了三座大工棚及医务室和伙房。接着,大队人马陆续搬过来了。此时基建队已相应缩编,原来在伐木场的,大部分到新建的伐木场去,愿意留在基建队的,可以留下。去的人多是图个吃住稳定,基建队则要时常流动,搬来搬去。
我们靠溪边的这一座草棚,隔成几个单间,每一间住一户,小伙房则在各自房间外面的空地自行搭盖。我和印尼归侨肖医生合盖一间,当中隔开。三餐做饭菜,可以互相串门。这天清晨,肖医生用煤油炉煮了一碗兴化粉,隔着竹编的墙壁招呼我女儿。我们穿好衣裳,抱着女儿到她的房间去。肖医生弄只精巧的小碗,拨出一些兴化粉,对华儿说:
“华华,叫一声阿姨,这米粉就归你了。”
华儿并不理睬,也不叫。肖医生试了几次,华儿根本不感兴趣。肖医生只好委曲求全:
“好了,好了。你也不用喊我阿姨了。兴化粉还是给你吧!”说着就把碗递给华儿,华儿还是不接。
金春说:“肖阿姨才煮这么一点米粉,华华就不吃了。要不然阿姨就不够吃了。”
“我三餐都吃得很少的。你看,”她取出一只很小的饭盒,“我吃米饭,只蒸一两米,有时候还吃不完呢!今天实在是煮得太多了。不给华华吃,也是浪费了。”
金春接过米粉,对华儿说:“华儿吃吧!阿姨给你的。说谢谢阿姨。”
华儿不说。肖医生说:“算了,算了。别难为她了。”
刚抱着孩子走到门口,华儿突然回转身来,对肖医生说:
“谢谢肖阿姨!”喜得肖医生追出门来,抱着华儿的脸,狠狠地亲了一口:
“华儿真乖!”
9
过了1970年的元旦,全县的林业系统进行大改编,把伐木场、林场、贮木场改编为营,基建队改为连,班组为排,统统纳入福建生产建设兵团编制。沙县林业局称为24团。团部就设在林业局内。
遵照上头的指示,全团上下都开垦荒山,似乎就要发生什么重大变故。我们杉口附近的山头几乎象理光头似的开了个遍。元旦也不放假,人人上山开荒。不知从哪里弄来了几头牛,让铁匠老陈打造了牛鼻栓。那天中午,我们正在休息,两个人就在我们家门外,将牛鼻栓弄得叮噹作响。金春心慌地说:
“莫不是来人捉拿你了?你听,是不是手铐的响声?”
“不会吧?”
“我出去看看?”
我默许了。一会儿金春回来,和衣上床:
“是牛鼻栓。吓了我一跳。”
那天中午,金春要包水饺,到伙房老梁那里分了一些肉和韭菜,把放在食堂的空饭盒也取回来。她一个人在家里忙着。收午工的时候,我路过伙房,被老梁叫住:
“小胡,你还蒸了一盒饭呢!”
“没有呀!我们中午包饺子呀。”
“你自己看看,这174号的饭盒是你的吧?”
“还真是的。谁送来的?”
“你女儿。”
“这丫头。晚上只好炒饭吃了。”
我刚刚到家,金春就问我:“怎么没跟华儿一起回来?”
“没见着她呀!”
“我让她去找你啦!”
我刚刚出去,孩子回家了。我没找着,又回过来,却听见孩子对她妈说:
“妈妈,爸爸不见啦!”
“胡扯,爸爸不是在你背后吗?”
华儿转过身来,高兴地抱住我的双腿,我把她抱起来,亲她:
“你去找爸爸啦?”
“嗯。”
“没找着,是吗?”
“嗯。”
“爸爸和你走岔路啦!爸爸永远和华华在一起,是吧?”
“是的。我要永远和爸爸在一起。我爱爸爸!”
毛主席说:“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我们这些被批斗过的,都列入另类。有的隔离,有的扣发工资,每人每月只给十五元生活费,带家属的,每个家属每月七元。我也被隔离,白天可以一家人过,晚上要和妻子分开住。我被指令到另一坐空房里过夜。安徽的小三子是基干民兵,那一晚是他值班。晚饭后,他到我的房间门口。对我们说:
“小胡,你听好了。今晚是我值班。你可要老老实实地到你该去的地方去过夜,不要影响我们贫下中农的小徐休息。否则,我对你不客气!”他说完,围着整个工区绕了一圈,最后又到我们门前,再大声地交代一句:“记住了?”然后小声,“我睡觉去了。”
我知道,小三子的言外之音是:“放心在一起睡吧!我不会再查班了。”
那一晚我们确实睡得放心,整座大棚只住我们夫妻俩。其他人都因为编制改变,搬走了。待华儿睡着之后,我跟妻子着着实实地风了一把,结婚三年多来,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看到妻子进入高潮的状况。
1970年5月28日。清晨。杉口伐木场来了三四个人,到基建队通知大家停工,集合整队到场部(即营部)开会。其中一个来到我家。为了不打草惊蛇,轻描淡写地告诉金春,让我也去参加。
我和大家一起到了场部,即被两个民兵挟持到一间小伙房去,并看守着。不久,金春抱着孩子,哭哭啼啼地赶来,她二婶把她接进屋。
一会儿,大会开始。看守我的将我押解到会场。平时和我还算要好的山东人崔俊法上台发言。当然不是他写的稿子。他那点不到小学毕业的文化,是写不出这种发言稿的。接着是喊口号:
“打倒刘少奇孝子贤孙胡振铎!”
“打倒现行反革命胡振铎!”
“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会议结束,我被戴上手铐,送到场门口等在哪里的木材车旁。车上已经有不少搭便车进城的男女。我戴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