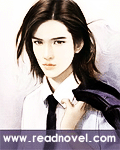���´Ҵ�-��5����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ɫ����
��Ƶ�С�������ɻ�ת���������������Ӵ�����һ�����������⡣�������ţ�Ҫĸ�ױ���������ȥ̽������Ĵ��⡣
��ʱ�����Ǵ�ĩ�ij�ʱ�ڣ�Զɽ�����İ֮�䣬��������������ũ������и��ݡ�
��һ����������ɽˮ����Сƽԭ����ɽ��ˮ֮�䣬�г���һ֧������˳����Ұ���и���������һ�������ɽ�£�һ����ֳ�����Ϫ�ߡ�
����ʱ�֣��г�ͣ�¡����ﲢû�г�վ�����еĹ�������߸ߵ�·�ӵ��������DZ�����������ͬһ����ׯ��
�г������еĴ��Ŷ������ˣ��³��������������IJ���һ����������к��ʿ����ɢ�����������ԵĻ����ϡ�һ������յ����ij��ᱻ��ͷ�����ˡ�ȥ�����֪����
���ִ��Ϻš�
һǧ����ʿ���ܿ���������վ����λ�þۼ����гɶ���һ�ŵij�����
ʦ�����Ÿ�ͷ��������������ǰ��������ҲԾ����������ƥս������������������Ķ��飬˳���������۵���·����Զ���Ĵ�ׯ�н���
����һ����������ͱ�֮����һ��������һ���������ã��ɶ������ཻ����������·���ߵĿտ�����ȷ��˵����������������dzɶ����ν��ӣ����dzɳ����ν��ӡ����ֵ����ʣ��Ǵ��������á������������ϣ����š��ݱ������������·�����õ���ǽ����Ȼ���ˡ��ݱ������Ķ�Χǽ�����ֿ��ֳ���ǽ�棬��Ϳд��������Ĺ���������������š��ݱ������Ķ��棬���ܼ������ղ�������˵�ġ��ݱ�����������������ȴ����ڽ̻�����ij����������������˲��ӵ��ݱ�������ÿ�����ʱ��һ��ǧ��ֻռ��СС��һ�������㣬����㳡����ʹ��������ǧ�ˣ�Ҳ���Ǵ´����ࡣ����������ѡ���˴�פ������������֮�ʡ�
���ٺͼ��������������ˡ�ʿ����Ҳ�Ѱ����������Ǵ�ס�ڴ����ײ�ďh�Ȼ��᷿��һ����ס�ں�Ժ����һɫ�Ĵ���̣��̵��ϸ���ĸɵ��ݡ����Ǵ�ũ�������������ġ�
����㳡��ʦ���İ칫�Һ;��ң����ڴ��������Ҳ��h�ȵ��᷿�����������żҾ졪������÷Ӱĸ�ӣ�ס�ڽ��������Ҳ�����������ţ�����������ұߵı��ţ�����խխ�������ͨ�����˴������ţ�����գ����Ϸ��ݣ���ֱ�ӵ���¥ʦ����ס����
�����ٷ����ҵ��ſڣ���һƬɹ�ȳ�������ɹ�ȳ���������̨�ף��Ǵ������Ĺ�����������������ܽ������õ����š�
��һ�죬�����������ʡ���ٹ���Լ�š�ʮ���ӹ⾰��ʦ���ô��������������������ס��������Ʒ����̸��
ʦ���������ϵܣ���ô���ѵ��ú�������������
�����٣���ʦ���������̾��Ͳ��ش��Ҿ��˰ɣ���
ʦ�������ȣ����뵽�Ķ�ȥ�ˣ��ҽ�����Ҫ��������������Ů��ѧ�����أ�����ת���������������С��������
�������������С�����ٸϵ���
ʦ������С������ȥ����̫̫������ү��������
���ǡ���
�����С����ȥ���ã���̫̫�������������ˡ������̫̫��������÷Ӱ����˵��·ң֪�������վü����ġ�����ʦ������˵Ĵ���£��վ����飬�����ٺ�÷Ӱ���ڳ��˷��ޡ�
ʦ��������̫̫���������÷������˼���С�ˣ������Ƿ���С�ۣ�˳����������������ѧ���¡��㲻�����ɣ���
��̫̫����ʦ��������ĸ�ӵľ������ˣ����ǻ����Ա����أ���ô˵���ⲻ�����أ���
ʦ����ͷ��Ц��˵�������������£���������˵����
��̫̫���£��Ѻ����������ߡ�
ʦ���������ֵ�������û�۸���ɣ���
��̫̫���������ᡣ��
ʦ����������ͺá�����Ҳ���ҡ���Ҫ�Ǹ��۸��㣬��������ң���һ�������������
÷Ӱ��������������һЦ����ллʦ������
ʦ�������ֳ����̣���������С�ˣ�����Բ�����롣÷Ӱ�����������������͵����������ߣ�
������������Űְ֣�����ȥ�����������֡���
���ˣ����������������������ǵ�С�£�һ����ͺ��ˡ���
ʦ�������÷���æȥ�ɣ���̫̫���������һ��л�Ҫ˵����
÷Ӱ����ʦ����ʲô�Ը�����
ʦ������ʲôʦ����ʦ���ģ��Ҹ����ϵ��ǿ�ͷ�ݰ��ֵܣ��dz���������Ī��֮���������ͽ��Ҵ�磬�ҽ�����á�����һ���˲�˵���һ����㿴�в��У���
÷Ӱ����ʦ����ô�������ǣ����в��еĵ�����лл��硣��
ʦ��������Ͷ��ˡ������������Ҿ��������ɶ����ˡ��㿴����ֻ�����µ�����ĸ���������Ҷ�ʮ���꣬Ҳû����һ�а�Ů�ġ�������������Ը�ⲻԸ�����ҵĸɶ��ӣ���
÷Ӱ����С������ȥ����������ȥ�ݼ��ɵ�����
����������߽�ʦ�����ߣ�����Ľ���һ�������ɵ�����
����������ʦ�����˼��ˣ�����������С�֣��������ڻ���������������ʺ��ϥ���ϣ����������ɵ�����
�������˸ɵ�������գ�����������ա�ʦ������ÿ�����Ц��
�������˲˺;ƽ������ʣ�����˵־�գ��Dz���ʰ����Ԫ��������ô���ģ���
ʦ�������Ƚ�Ԫ���������ģ����ã���˵�Dz��ǰ�����
��̫̫Ц��¶�ݣ�ĬĬ�������ת������̫̫��
����̫̫����˵��־�ս���ʰ��ʲô����������
÷Ӱ�������˻�����ʦ�����ɣ���
���ˣ���־�գ����˵ѽ����
ʦ�������ҽ�����ʰ�˸�������������̫̫�����ã������������ɶ��ӡ��Ҹɶ��������ҵ�����գ��������ҵ�����ա���˵���IJ�����ѽ�������������Ⱥ����ģ���
���ˣ������𣿰�ѽ�ɶ��ӣ������������������Ҳ��һ�ס���
÷Ӱ����������ȥ��ȥ�����裬Ҫ����һ�㡣��
�����ܵ��������ߣ����˫�ۣ���ס���������������IJ��ӣ��ݺݵ����˷��˵�����գ�����������գ������Ȱȵ�������
ʦ�������ð���������������ɶ��ӡ��ղ����ɵ���ֻ������ģ���ô������裬�ͰȰȵ����أ���
���ˣ��������ɶ��ӣ����������ø���Ҳ�����㡣����������������˫�գ����ĵ�˵��������ɵ����Dz�һ����Ե�ֺ��¡��ɣ���
�������ͷ��
�����������Ż���Ц�
ʦ�����������٣�������㵽��������֧ȡ���ٿ�����͵���·�ϵ��߳ǹ���Сѧȥ�����Ľ����������������˵�������Dz��ӵ�һ�����⡣Ȼ�����Dz��Ӿ������������Ů�����ѧ���£��������������顣��
�����٣����á������ȥ�졣��
ʦ��������ʲô���أ����˷���ȥ�ɣ���
�����٣���Ҳ�С���
ʦ������һ�����ӣ�������˵��
�������ɶ��ӣ����������ס�ˣ��Ժ����ϸɵ��ҳԷ����ɵ��Աߵ����ӣ��������λ�á���ס�ˣ���
����������ס�ˡ���
���磬�����ٵ���·�ϵ��߳ǹ���Сѧ�������˾�����Ů��ѧ������
3
��������·������Сѧһ�꼶��
���꼶ʱ��ѧУΪ�˱�����·�Ա�ѧ���İ�ȫ�������������˷�У���Ӵˣ����ǿ��Ծ͵���ѧ�ˡ�������ѧ�������Ϊ���þ����ҼҶ��棬������ǰ��ɹ��ƺ���ǡ�
һ��ʢ�ĵ�ҹ��������һ��ҹ�������꣬�ŵ�����ֱ��ĸ�Ļ����ꡣ�ڶ���������С������������û��ͣЪ����˼��������������ݵļ�Ъ�������˶��ܵ��߸ߵ���··���ϣ�ȥ��������Ȼ�������������е��˻��������£�ֱ�ӵ�������ȥ������Ҳ����ĸ��ǣ�����֣����������ֻ�����ջ����ʢ����̥��������Ȼ��ȱ�첲���ȣ�������������бб���㵹��ľ���£����й����ڵصġ���Ŀ��������ͷ�������켣��һƬ���������֮�С����������ף���ȥ�������α��Ӻϼ�ƽ������ż����ô����סһҹ֮���������Ϯ�أ�
��ѧ��ʱ�䵽�ˡ������ؼң������������ѧȥ�ˡ�
��һ���������Ρ�л��ʦһ�����ң����Ͻ�̨�����½̰�������ҵ��������������ȥ�ַ�����л��ʦ���ֱߣ���������������ҵ��������ʼ������ҵ���ϵ����ֵ�����
�������졣��
������
����������
����������ң���������սս�����ص�����ض�ʮ�����ߵ�����̨������л��ʦ�ĸ�ǰ����ʦȡ���ҵ���ҵ�����������ĵط���ָ�����ң�
����һ�ζ�������ġ�������ô����һ�������������⣿��
�ҿ��˿��Լ�����ҵ������Ĵ��ˡ������������ݡ��ҵ���ͷ���������������
л��ʦ������������������������ߣ����չ�������һ�����һ�£���һֻ��ץס��������֣������ķ���������һ���ţ����������������ֱ����Ĵ�����ֱ�ˡ���˵��
�����㳤�����ԣ���
�����е�ͷƤ���飬������ҧ��л��ʦ�߸߾�������Ѿ������ˡ���ô�������ˣ����룬������û��ɣ���ô�����Ӷ����Ƶģ�û����ʹ�ĸо�ѽ���ޣ����ˡ���ʦ˵��Ҫ���ҳ������ԣ�����������Ҫ��Ŀ�ġ����ڴ�����أ�ֻ��һ����ʽ�������л��ʦ�����Ŵ�ĸһ���ij���л��ʦ��
л��ʦ����һ�꼶�ļ�����ʦ����һ�أ�ͬѧ�Ǵ�ܣ�����ײ���ˣ���Ѫֱ����л��ʦ���������쵽���Լ������ң���������մ���俪ˮ������ֹѪ���������������������Ž�״�����С������Ϣ����ѧ�ؼң����迴���ұǿ������Ŵ�Ѫ˿����������������ף�ץס�Ҿʹ���һ���ӣ������ҽ�л��ʦ���������ҵ��¡��ڶ��죬�����ũ�������һ���Ӽ�������������ȥѧУ����л��ʦ��
�¿��ˡ�����ͬѧӵ��������ǵ���ʱС������һ��ͬѧ���ң�
�������죬����۲��ۣ���
��û�лش�Ҳ���ûش������Һ�л��ʦ֮������ܣ����ܸ��߱��ˡ��Ǹ�ͬѧ�����ӽ��ң�˵��
�������죬���и����飬��մʪ�ķ���Ԥ�Ⱥ���ͿĨ�������ϣ����˴�Ҳ�������ۡ��������Ժ�������ԡ���
�����Ժ�����Ҫ��Զ��ס���̰��Ľ�ѵ��
��һ�죬��Լ�˼�λͬѧ�������ӵ����ż�ȥ������ɽ�����˵���Ϸ���ҴӰְֵij�����͵�����沼�Ƶķ��ţ��ֱ�д�ϸ�λͬѧ�����֣����Լ�Ҳд��һ�档�ִ�����������������Һ첼������������һ����������졣��һ�죬�ְֺ�����һ�����Ӧ�ꡣ�ҴӴ����ݵذ�����Щ�£�����һ������ͣ���������ͷ�ĵط����������ģ�һ��Сսʿ�������������أ��ڻ��Ӵ����£���ɽ����������һ���������ʹ�켫�ˡ������ɻ������Źܷ���һֱ����ɫ�����Żص��ҡ�
���Ҹո�̤�����ţ�ӭ���ҵ���Ȼ��һ���ڷ�����ķ��ͬ���ھӵ�Ȱ���£������ٰ��˼����ȴ���ʦ�����ҵ���ҵ��Ȼ�����ˣ���������л��ʦ�Ľ�߽�ѵ��
�������е���֦��ͬ���ھӴ��������ˡ������Բ������ĵذ����ң�
���ط�ȥ���ط�ȥ�������������㡣��
�ŵ��Ҷ��ڴ����ı��Ҽ����衣������������������ǰ���������ӣ������Ʋ����ҵ����ᣬ��ο�ң�˵��
�����������¡�������Ļ�����ط�ȥ�ɣ����������������ء���������һ�����ˡ���
���㬵��߽����ţ����һ�߶�ߵ�ľ�ż������������������ϣ��ſ�˫�ۣ����ҽ������ڻ�����۵ء������µ���ˮ�������ҵ�����ϡ���̧��ͷ����������������ˮģ������������ûڼ��ˡ��ұ�������IJ��ӣ�˵��
�����裬���Ժ���Ҳ�����ˡ���
���š���������������ȡ��ë������Ԥ�ȱ���ˮ�������մˮš��һ�ѣ����Ҳ��˰�����Ȼ��ӵ�����ң�˵����������Ҫ��������˵�����ܿ���ܼ��������������������𣿡�
���裬��������ʲô���ӣ�������һ���ÿ��𣿡�
�������ӣ���ô������Ѱ�����أ���
������Ѱ���ģ�������ĺܺÿ�����
��˭˵�ģ���
���˼Ҷ���ô˵����
�����Ǹ������С���𣿡�
����Ҳ˵��������˵����Ҫ�ǵ��˹٣�Ȣ����ҲҪȢ������ô�ÿ��ġ���
����С�ӣ���Ҫ������������˵�ְ�Ҫ��������
���裬����ô��ô�����أ�������˵����ġ������ҿɺ��ˣ��ϰ������ң�����ү����ү�غ��ţ�����ȥ���أ���
����Ҳ��˵������ġ�����ģ����˺�������Ĵ����ѵġ���
��лл���裡��
�ְֺ�����Ҫȥ�߳��أ����������ͬ�С������سǣ�����һ���ſ��Źҡ��ķ��ı������ӵĵ���ʱ���ϰ�ӹ�̨�Q�ҴҸϳ�����
����Ӵ����λ�����������𣿡������˫�֣�������ס�ְֵ��֣�������˵������λ������̫̫������С��ү�ɣ���
�ְ�һ㶣������ǡ�����
���ޣ�������������ע���ʱ�����Ǽ�����ġ���
�����������������ˡ��������ϰ塣��
�����ǣ��������¡��ҳ��Ƕ��ڿ�����ģ�ǰ�ߴ����Ǻ����ģ���������Ҳ�����������ǰ��������ģ���
���������ⶼ�����������Դ��ġ����Ǿ��ٵ���ŮҲ��������ѧ���
���ϰ������ҵ��֣����˹�̨��ȡ����īֽ�⣬��պ��īˮ��ë�ʽ����ң�˵��
������С��ү��дд������֡���
��̧ͷ�����ְ֡����裬���ǹ����ң�
��д�ɣ���
�ҽӹ�ë�ʣ���ֽ�Ϲ���������д���Լ������֣�
�������졣��
���ã��ã�д����ã�СС��ͣ���д����ô���������������һ����ͬ���죬��ͬ���졣��
���ϰ�ӳ�����ȡ���屾ʮ������С��д�ֱ������к��ݱʡ���ī����̨���ð�װֽ����������ݵ�ĸ�����
������������ү�����Ԥף��ү���ճɲģ�Ϊ��Ч������
����лл���ϰ岮������ĸ��˵��
��лл���ϰ岮������
����ԣ������ϰ����ḧ���ҵ�ͷ��������л������л�������˸��ְ֣߰�����������ȡ����
�ְֺ���������ϰ����������һ�������ֵ����Ժ���鿪�Σ����Ǻ����ϰ�û���ټ��档
���߳��ػ�Ӫ�أ�������ҽе���ǰ��Ҫ�Ҹ�����дһ���š���˵��
���ְ֡����������д���š��㶼�϶��꼶�ˣ��벻�������˵���仰����
���롣��
���Ǻá���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