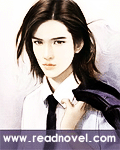���´Ҵ�-��6����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ػ�Ӫ�أ�������ҽе���ǰ��Ҫ�Ҹ�����дһ���š���˵��
���ְ֡����������д���š��㶼�϶��꼶�ˣ��벻�������˵���仰����
���롣��
���Ǻá���Ҳ������д����ɣ�����������һ��װ���ŷ⣬�ĵ�����ȥ����
���裬���ſ�����д���ţ�һ����ܸ��˰ɣ���
�����ǵ�Ȼ�ˡ�������վ���������������ø��ң�˵�������ˣ����������ˣ���д�Űɣ�д�������迴���������һ�ġ���
�����ó������������ᣬ��������ȥ����ʼ������Ь�ס�����Ь��������������ˣ���������������С�������������������һ����ÿ����ˡ��ѹְְ���ô����������û����������������������ܡ�
����������ǰ����ʼд�ţ�
�װ������ţ�
������
�ҽ����죬С��������������������Ѿ��϶��꼶�ˡ����ְ֡�����˵�����Dz��Ӻܿ��Ҫȥ�����ˡ����˸��ݣ�����һ��ȥ��������Ҫ��ౣ�����壬�����ǻ�����
ף��
�������٣�
��������������쾴��
�л������ʮ�������¡�����������
�����м������Ҳ���д��������ġ��O���֣����ٵġ��ۡ��֣���ǰ���Ƿ���ģ��ʻ��ܶ࣬���������д�ϵġ�
4
���ã�����һ·���¡��ҵ�Сѧ���꼶��ѧ�ڣ����ڸ������ֳ��ع���Сѧ�ϵģ���û����ĩ���ԣ����ְ���ˡ�
��һ�������ʱ���и����̸����Ǽ�����һ�����ӵ���Ʒ�������������¥������Ķ����ϡ�������ҡ��δ���������ӣ��²�����װ��ʲô�óԵĶ������������裺
�����裬��������Ķ����ó��𣿡�
���貢����������æ�������ң����һ�Ų�ֽ���۳ɶ룬�����ҵ��죬ʹ��һ����˵��
��С���Ӳ�Ҫ���죡��
�Ҳ��������ˡ������Ҳ�֪����������װ�ģ����Һ�С�õġ����ס���Ʒ�����ǻ������첼������������֮�࣬Ҳ��һЩ��ʳ�ĸ�㣬������Ȼ�Ǹ��ҳ��ˣ�����ʱ�������ܳԣ�������˵��
���˼��죬��λ���̾�������һ�������СŮ����˵�����Ҽ�į�����������õġ�
���꼶��ѧ�ڣ�����ȫ�ҵ��˸��ݡ�
�����ֳǵ�ʱ�����ǻ�������ס����������ס������һ�Ҷ����ľ�巿������ס��¥�ϡ����������ĵ��Ƹߣ����Ǵ���ıߴ�����ĿԶ�������Կ���Զ��ɽ�ϵĵ���⣬����ҹɫ�����ʱ�������������������裬����ʲô����������ң�������̿ʦ����ɽ�ϣ���ȼ̿Ҥ���ľ��ľ��ȼ�շ����Ĺ⡣���ںڰ����ر���������ʵ����Ҳ���ţ�ֻ�DZ�ǿ�ҵ�����ѹס�ˡ�
����ߴ���עĿԶ����Ҳ�������Ÿ��ݵķ��������������Űɣ��������豧���ң�̽ͷ���⣬����ӵ��ݶ��������ǵĽ��¡��������裺
����̿ʦ��һ��������ɣ���
����˵�أ���
����������һ�������ࡣ����Ҫ�ȿ��������������һ��һ�εģ�Ȼ�������ƿ�����������Ҥ������Ͽڣ���ȼ�𣬺ü����Ϩ���ˣ�Ҫ��Ҥ��עˮ���£���Ȼ��Ҥ�ţ�ȡ��ľ̿��������װ¨�����̵꣬����������ǡ�����ֻҪ����Ǯ�����ˣ���㰡����
���������㳤���ˡ�ʦ����̿���������̣��㶼�����ˡ���
���ǵĶ���һ·������������걡���ƽ������Ҳ���ǴӸ��������£���ˮ·���︣�ݵġ���Լ����1949���ġ����·ݣ����ǵĴ��ӴӸ��ݵ��º�·С����ͷ�ǰ���һ·��ֱ��ˮ������·�����dz���Ȫ�ĵط��������д�ǰվ��Ϊ����Ԥ����ס����
�ְֽ����Ǵ�������·һ�ҽ������б���棬��һ�Ҹ�ԣ������һ�䷿����䷿�ǴӴ��Ž�ȥ�������ұߵ��᷿����Լ�ж�ʮƽ���ף���Ϊ����ʮ�ֿ����������һ�Ŵ���ǽ�ǰ������Ӻ�Ƥ�䣬�մ���һ��СԲ����һ���Ŀ��ˣ������������š�������������䴦������һ��С���ӣ�����ú��¯���������ǵij�����
����һ���˰��ٺ��Ժְ֡���������Һ����ã�ȥ�������š�
����ס�����ùã��˳ư˹ã��ļ��������Ȼ���˶���һŮ��һ��ȥ����һ�����ˣ�һ��Զ���㽭�����Ǽ������ۣ��Żص����ݣ�Ҳδ�ܾ�һ��Т�ģ����ԣ�ֻ���ùã��������ŵ�ֶŮ������������������
���ǿ������ŵ�ʱ�����Ѿ��Բ��ڴ����������������ˡ��������ݵñ����ε��������㿴�˲��ҽӽ����ְֽ����������ŵĴ��ߣ����豧�����ã�������˵��
���裬�����������������Ů�������������ң��������������š���
��һ�߳���������½����ܵ�Զ�����ţ��������ؽ������������š���
���ҵ������У����ŵ���ò��һ�����������ġ������������ݹ����������ʵ�ڲ��ҿ�����������һ��һ�ε����ң���������ǿ������Ŀݸɵ�С�֣������ҵ��֡����ų���������ţ��õ͵ü���������������������˵��
������������أ��������ҿ�������ģ����������棬�ԡ�������һ��һ�ڵش��Ŵ������ְ֡���������˶���������˵�������ջ����֣��ְֽ����Ǹ���Ҵ�ϡ�����ҡ��ҡ����������ã����������ţ����þ����۵ؿ���������
�����ڰ˹üҳԵ��緹���˹ø�������һ��С��������������ӣ�˵�����������ǵģ��������˸��Ļ����ġ�
����������ȥ��̨���������˸��������衣������һ������������һŮ��ز��������ֻʣ�¶���һŮ�����費֪��ô˵�����������ڻ���˵��
����˵������������ʺһ�����ס������ã�һ����ֻ��һ��������ǿ������ȥ����
�Ӷ�����һ���û���죬���Ǿ�ȥ�����ű�ɥ��������ɥ�µ����������˸����������ٴμ��档
һ�����ʵ����ӣ��ְ�������ȥ���Ŷ��������ɵ������衣��һ���������ģ������ǵ����鶼�ܺá������Ŷ������ǵ�һ�����ӽ�ȥ��Զ�����Ǹɵ���������¼ҡ������ڿ����������ΰ���ϺȾơ������ȵ����죬���������Ŀ������ӣ�����ȥʮ����ˬ������������û�л���ȥ�������ǡ������ݺ�ͽ���һ�Ρ�
��������������ְֶ������ؼҡ��ƺ������æ����һ�죬�ְ�����������ŵ������������Ϸ������еķ��ţ��˿�ľ�ذ壬ȡ��һֻ�Ͳ���������������һЩ��ǹ�ӵ��������ڰ����ϣ��Ը߷���������̨������ǹ�ӵ��ijɶ�ǹ�ӵ��������Ĺ����ӵ�װ����ǹ��ٶ��ӵ�Ȧ��ת�˼�ת���������⣬��ǹ���������ǹ�ס���������һ�ԣ���ɫ�����š����ƺ��Ѿ��Ӱְֹ�������ͽ��ŵı����У����������֮�����ˡ��ְֳ�ȥ�ˣ�û�л������緹����һҹ������������������ʱ������˯���ˣ����þ�����˵�ˡ��Ұ�ҹ�������ְֺ������������ĵ�˵������������Ѿ�˵�˺ܾúܾá����跢�������ˣ�ֹͣ��˵������������С�㡣��С�������ϴ�����װ˯���ˡ������ֿ�ʼ˵������������ʱ���ְ־ͳ�ȥ�ˣ��Ӵ�û���ٻ�����
��һ��ʱ����û��ѧ��
5
1949��8��17�գ����ݽ���ˡ����ã������յ��ְִ����ż������ţ��ֹ��˲��ã�����Ҳ����ˣ�������û���յ��ְֵ����ţ�Ҳû��˿������������Ϣ���ְֺ���������꣬����������û�а��һ���죬û�к��һ����������һ�����С�Ķ��������ߣ�����֮����ʲô���£�����üĿ���飬������ҹ������߽�����Ļ��ύ̸��
��һ�죬����������ڴ��أ��þõط��Ŵ���������ɬ��ʧ��������ң����������ã����˺�����������û��˯�⡣����������������˯�ˣ��Ų������¡��ڶ����緹��������¯��ź�������Ʋ���ľ̿��¯���ϼܺ�С�������������ϴ�õ���ˮ��Ȼ���ң�
������������Ҫȥ�˹üң���������������������Ѿ������������������ˮ��ľ̿���㿴����Ժķķ��ʼ�շ��ˣ����û���ȼ�Ʋ�������������ɿ��̿��ˮ���ˣ��������ӽ�һ������Ҫ���������ף�Ҳ��Ҫ����������������������ˣ��к�����һ��ԡ������緹��˯����һ��Ҫ�������չ˺ã��������𣿡�
�������ˡ���
��ʵ������ͻ����ˡ���һ�꣬�Ҳ����꣬�������ֳǣ����û�û�����Ǽҡ��ְ֡��������Ӧ�꣬Ҳ��������С¯��������Ʋ���ľ̿���ס�ˮ��Ȼ����ɿ�磬�����ԣ�������˵���Ѿ����ᳵ��·�ˣ���Ϊ���Ѿ������ˡ�
��������������飬˵��ȥ����֯����Ǯ���������ǡ�
����ÿ����������������������ص��ȣ����ѵ��ϴ����ò�������������ֱ������ҧ��������̾Ϣ�����úܿ�˯���ˡ��Ҳ�֪�����������ܼ��������ʹ�࣬���ɻ��У�Ҳ������˯���ˡ�
�ж��ټ��ѣ��������Լ����ţ�Ҳ������˵���������������С������˵��Ҳ��˵���кü��أ������۾������������ң�������ֹ��ֻ�ǽ���§���ң������ҵĺ�����˯ȥ��������ģ������������ž��ʹ�࣬��ȴ��˯���š������ڣ�Ϊʲô���ܿ�쳤��Ϊ����ֵ�һЩʹ����dz��أ�
����õ��ǽ�����������ˮ�ײ���һ�֡���Ϊȱ��Ӫ����ʹˮ���ۼ���С�ȶ����£�������ȥ�������֪��ĸ����������һ˫���ȣ�ÿ�컹Ҫ��ǧ����εز�̤֯������̤�塣�¹�����Ҫ����ææ�ظϻؼң��������շ���ϴ�¡���������ĸ�ף�˭������ô��ǿ��������
ĸ������ˣ������е�һ��ò����������·����Լ��Է��������Ͳˡ������Ҵ��������⣬˳����ʮ����̨����ȥ�����ǹ����IJ˵��ȥ��ũ��Ҫ�����ཷ�����磬���ཷ�õ����ı⣬���ڹ���ɼ�������һ��ϸ�Σ�������ζǺ��������������˶��̲�ס���ԣ���Ȼ����������顣���߽��������飬���ڽ������Щ���������͵��·��ˡ�
����ʵ��֧�ֲ�ס�ˣ��ͽ������С�֣��������淢�⡢��������С�ȶ�������ظ�������������ʹ����������ʹ�ࡢ�������ε������ң��ƺ���˵��
�����Ӱ�����ʲôʱ����ܳ����أ���
����ù�꼾�ڡ�
���յı���ʹ�쾮�������ˡ����᷿��IJ˵����������
�⼸�죬����û�г�ȥ֯�����������ܴ��������������Dz��������ˣ�����������֧�ֲ�ס�ˡ���֮����Ъ�ڼ�����貢�����ţ����ó���IJ������ұ�֯������������ɫ�����ţ��Ⱥÿ��������ã�ϵ�������·����������Ļ��
���������¸���ͣ�Ĵ��꣬�ҵ���������ë��д�˼���С������������ү������Ϊʲô�´��꣡��
�´����ð����쾮���ˣ����ϳ���ȥ�ˣ�ũ���IJ˵�Ҳ����ˮ�Ҳ������Ҫ�����ཷ�������ˡ��Ұ������ӽ��쾮������������ˮ�н��ݡ�Ư����������ˮ��ת�˼���Ȧ��������������ˮ����ʧȥ����Ӱ������������ү�����ˡ�
�죬�Ծ����������ģ��꣬û��ͣЪ����˼���������˺ü��죬�Ž������硣��ͷ�ӱ�������������������������ء��ӷ��������ϣ�����¶�����⡣��ũ���ˮ������ȥ�����С��һƬ������ʱ������������ó�ȥ�ˡ�˵��ȥ�˹üҡ����˰�������������ˣ��������˼����㣬�в�������С����̶��⣬��������Եġ����еóԣ����е��档���費�ڼҵ�ʱ��������������������ϲ�����С������������������ڿ����������ε��̶��⣬�����ģ��ɺó��ˣ�һ��ֻ��һ��Ǯ�����ǽ��죬��һ��Ҳ����ҵ���Ȥ����Ϊ����û�л��������ƿ��������̶��⣬�������ĵ�������Ҫ���ã�
���裬�Ҳ�Ҫ�̶��⣬��Ҫ���ã���Ҫ���á��������Ū�Ķ�ȥ�ˣ���
���費����ֻ��һ�����������ᡣ��ʹ��ҡ��������ֱۣ���������ش�
�����Dz��ǰ��������ˣ�˵����
���������������ߵ������Ƶģ��������¡���ֻ�ǽ����ر�ס�ң�ʲôҲû˵���������ˮ�����ҵ����ϣ������������£��Ҳ������ˡ����ſ�˫�ۣ�ſ������˫���ϣ�ί����˵��
�����裬�Ҳ�Ҫ�����ˣ���Ҫ�̶��⣬��Ҫ�̶��⡭�����ҵĻ�����ô��������û��һ�㰲ο����ķ������Ҿ�Ȼ����Խ��ԽС��С���Լ�˯���ˡ�
6
���˼��죬������ʰ�˼��������˷�������һ�����������ó��������͵�������ȥ��
�����ڱ������һ�������ﰲ���¼ҡ�
�����������ϣ��ֶ��������֣��м��ɱ��Ŵ�ͨ�����������������ż����û�С����ߵĽṹһ�£������ϴ��Ž�����Կ�����쾮���쾮���������á��쾮���������ź��쾮֮�䣬�ɏh�ȹ�ͨ��ż�������ڣ���ڱ����Ǻ��úͺ��쾮�����쾮�����������᷿��
�����������ó��˹����ij���������ʮ��̨֯�����������������֯����
֯������ı���ס�Ź����Ĺ�����Ա������ĸ���ڸ���������ס��
�����Ѿ�û�к��С���������һ�ӽ�ž��������á����ö�ռ���������������Ϊ����һƥ�������ˣ��ں�����ɱ����͵����ȥ�ۿ���ֱ��������ҲŻ�����
�ֹ���һ��ʱ�䣬���ӳ����ˣ�����һ��������Ͱ��̣�����ÿ��һ�����һ������Dz�������������á����á��h�ȶ�ռ���ˣ������Ƕ���ďh��Ҳ�������һ����������ڸ�����Ԯ����־Ը�����Ʒ�����硣��������������峿�������������Ϻܳ��հ࣬����ֻ�Ǽ��Ҵҵس���һ�ٷ���û����Ϣ��ÿ����ˡ�һֱ��������ɲų��ߡ�
�ֵ�ù�꼾�ڣ������������ŵ��Ҷ����������ߡ�����������֯���İ���Ц��˵��
�����������������Ķ�����ȥҲû�ã�����ĸר�Ҳ������ĺ��ӣ����ǻ���������Ķ������ͳ�����˦��Ұ��ȥ����
����˵����˿ֲ����Ҹ��Ӻ����ˣ�������ץס����ĺ��½š�
�ҵĽ��ţ�Ӱ��������Ĺ��������谲ο�ң�
�����̶�����ġ�����İɡ�ȥ��С������ɣ���
С���������ܵĺ��ӣ������춼�ڳ������������һ���档������綼��ѧȥ�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