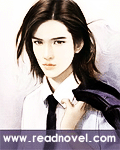岁月匆匆-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小妹妹是主管的孩子,她天天都在厂子里,经常和我一起玩。她姐姐和哥哥都上学去了,只有她最小,正好和我作伴。
我又回到小妹妹身边。小妹妹领我到右厢房她的住处,从抽屉里取出带着许多小黑点的白纸。对我说:
“这是蚕卵。我姐姐说,当它们听见春天的雷声以后,就会咬破卵壳,一个又一个钻出来,讨桑叶吃呢!”
又是一声炸雷。我们两人、四只眼睛,紧紧盯住蚕卵,果然有一两只黑黑的小虫子在爬动了,接着一个又一个地出来了。小妹妹撕下一小块纸,把它搓成尖尖的纸捻,用纸捻的尖头部分,去挑蚕宝宝,把它们挑起放入纸盒里。小妹妹拉起我的手,出了后门的围墙,找到了一棵矮矮的桑树,飞快地采了十几片细嫩的桑叶,冒雨跑回来。我们用手掌抹去桑叶上的水珠,又用草纸将水分吸干,然后放进盒子里,用纸捻将蚕宝宝挑到叶面上。
“小妹妹,你怎么对养蚕这么熟悉啊?”
我羡慕她的精明能干。她告诉我说是她姐姐教的。还答应我,等她姐姐回来,向姐姐要一些蚕宝宝送给我。
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有一个女人吊死在大庙前西侧的林子里。第二天天未大亮,月亮仍高高地挂在天上,厂子里的人和就近村子里的人,都围集在庙南的空地上,远远地望着吊死的女人,各种各样的议论都有。
有人说,吊死鬼是会跟着月亮走的。今天的月亮依然当空,这女鬼会不会是昨晚从别处“走”来的?我这样想。我紧紧扯住妈妈的衣襟,身子半掩在妈妈的身后,脑袋伸出去偷看,生怕吊死鬼会走过来抓住我。
过了一阵子,看热闹的人陆陆续续走了。我和妈妈也回工厂去。
不知道是不是吊死鬼带来的晦气,工厂支撑不下去了。过了几天,我们全厂都搬家了。新厂比老厂扩大了三四倍,就是在大庙东北角一段路程的祠堂里。新厂除了增加几台织布机外,还有二十几台织毛巾机。门外更有一大片毛绒绒的草地,成了晾晒毛巾的好地方。
织好的毛巾要一条条剪下,在两头的布质上印上文字,就是毛巾的品牌和工厂名称。师傅预先用绛红或大红颜料调成色水,用软软的阔毛刷,在盘子里沾上色水,往木刻的印版上刷(要掌握分寸,色水少了,印不清晰;色水多了,会洇开,图案模糊),然后将印版翻过来,在毛巾两头的留白处用力一摁,就成了。叔叔们将印好的毛巾送到草地上去晾晒,使色水深深渗入棉纱中,不容易褪色。我喜欢跟在叔叔们的后面,跑来跑去,还能搭上帮手。没事的时候,就跟小妹妹在柔柔的绿“地毯”上转圈子奔跑,赤裸裸的双脚在草地上磨蹭。累了,就往地上一躺,眯缝起双眼,仰望蔚蓝蔚蓝的天空,望着被轻风吹动、变幻无常的白云,和小妹妹相依在一起,仿佛就是一对小夫妻。
工厂里设有大伙房,大木桶似的圆蒸笼,可以装下许多坛坛罐罐。妈妈找了一只油漆铁罐,洗刷干净了,请人用粗铁丝安了一个提手,每天少放米、多放水,蒸一桶烂烂的稀饭,就着我们在大伙房捡来的花菜底座、剥开腌制的菜心。中午开饭的时候,妈妈领我去了几次伙房,以后就让我自己去把饭取回来。
为了多织几梭子,多挣点钱,妈妈总是很快就吃完饭,不休息,继续织布。这段时间,我就跟在大孩子后面,看他们在祠堂边废弃成荒园的空厝地里,攀梯登高去掏墙洞里的小麻雀。被掏出来的小麻雀还羽翼未丰,不会飞,它们叽叽叫着,等待母亲喂食。虽然我们也给它们喂米饭,但它们并不领情。正当我们犹豫不决,是放回墙洞,还是拿走喂养的时候,小麻雀的父母回来了。它们先飞进窝里,将食物放下,立即出来寻找孩子。它们上上下下围着我们盘旋,高声叫唤它们的孩子。我们最后决定,把小麻雀放回去。老麻雀看到孩子回来了,夫妻双双探出洞口,望着我们离去,才放了心。
工厂里来了一位指导员,他用两张大白纸抄了一首歌,在休息的时间,由他来教唱。题目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宗华作词,罗宗贤作曲。是鼓动青年参军,支援抗美援朝的。歌词如下:
从东北,到西南,
从沙漠,到海边,
愤怒的声音响成一片,
热血的青年奋起参战,
全国各民族的人民
快起来,起来,
起来,起来,起来!
抗击美帝,支援朝鲜,
为保卫祖国的独立而战!
抗击美帝,支援朝鲜,
为保卫世界的和平而战!
决不能让那侵略者的血爪,
沾污了祖国美丽的河山。
把侵略的野兽,
消灭在我们的门前。
支援了朝鲜的人民,
也就是保卫祖国的安全。
支援了朝鲜的人民,
也就是保卫祖国的安全!
在北门外的织布、毛巾混合工厂,没有多长时间,也许是工厂重组,也许是倒闭。总之,我们母子又一次搬家。母亲从此离开相伴她大半生的木制的织布机。
7
这回是搬到鼓西路去,母亲被政府安置在福州印刷厂作捡纸工。
我们就在印刷厂附近的一座大院里,租赁一间房。隔壁住一个七十岁左右的老太婆。这座大院大概是富人家被分的家产。各家产一间,住着六七户人家。吵吵嚷嚷倒象是菜市场。
我们的生活总算安定了下来。妈妈跟厂里请了假,带我到鼓楼中心小学报名插班入学。
妈妈不是技术工,所做的工种很轻,只是将同一号码、不同颜色纸张印制的发票,按一二三四联的顺序,一本一本地捡好,交给装订工去装订。工资自然不多,生活并不宽裕。
我们每天中午提了一只铝锅,到郑老伯那里去打饭。这是厂里的规矩,凡本厂职工,中午都免费供饭。郑老伯为照顾我们母子,总是将铝锅装得满满的,够我们母子一日三餐吃的。从我们所住的大院后门出去,经一条二米宽的巷道,往北走百十步,就是印刷厂的后门,紧挨着就是伙房。
我们住房的隔壁邻居,就是先前提起过的老太太,她独身过日子,几乎没有儿孙来看望她。她的房间窄窄长长,仅仅打上一张床,床沿的空处还不足半米了。在我们两家的门口,也就是后门的进口处,有一块几平方米的空处,被人堆满柴草。再进去,就是唯一可以采光的天井了。由于住户多,采光少,整座大院显得昏昏暗暗。
在我不上学、妈妈去上班的时候,老奶奶就把我召唤到她的小空间去,给我看石版印刷的大开本连环画。书里画了罪人在十八层地狱遭受种种刑罚的凄惨状况。老奶奶指着画面,一幅幅给我讲解:我们人死了以后,先要经过奈何桥,然后到阎王那里,阎王指出你在世上所犯的过错,由判官来审判你,对你进行应得的处罚。处罚的手段惨不忍睹,有抱火柱,下油锅,上刀山,下火海,还有的被用大锯从头部至下身一劈两半……。总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老奶奶对人生的总结。她要我牢牢记在心里。为人在世,不可作伤害别人的事情。老奶奶的讲解,使我对她存有几分敬意、几分畏惧。
不知道老奶奶是靠什么过日子,也不知道她靠什么来支付房租。她一个人无依无靠,孤独困苦。只有我能和她作个伴,和她说几句话。每当我到她房间里,她都十分开心。她时常在后门的巷子里,借着有限的阳光,晾晒大米饭。晒干了就收集在小瓮子里。她曾经打开瓮子,教导我要怎样爱惜粮食,不可浪费,否则会遭天谴雷劈。我们以后都把吃不完的干饭送给她,她就用晾干的米饭泡开水充饥。
1950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妈妈凌晨两点多就将我叫起来,到印刷厂汇合,和叔叔、阿姨们一齐整队去体育场,参加示威游行。三点半前我们到了指定地点,接着开始发馒头,每人两个。我也是游行队伍的一员,虽然只是妈妈牵着我,也分给我一份。这是起早发的点心。
整三点半,大会开始,主题是反对美帝国主义武装日本、霸占台湾。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骚扰我国东北。为我们刚刚建立的共和国示威壮胆!。四点正,游行正式开始,群众一路高呼口号。妈妈和叔叔、阿姨们,人手一只彩色标语旗。妈妈的一只手紧紧地拉住我,生怕我在人群中丢失。高音喇叭播放《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歌》等即时歌曲,鼓舞着人们昂首挺胸、阔步前进。群情激奋,歌声嘹亮。一首歌这样唱道:
反对武装日本,
反对武装日本。
日本必须走向民主,
亚洲必须走向和平。
美帝国主义要武装日本,
我们坚决不答应!
接着高喊口号:
美帝国主义从朝鲜滚出去!
美帝国主义从亚洲滚出去!
反对美帝!
解放台湾!
游行示威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六点左右我们回到家。上午休息,下午照常上班。
我的学校在省博物馆的南面,与博物馆相距很近。当时的博物馆都是免费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进去参观。我们在中午放学以后,约了几个同学,一起去参观。博物馆里有大型动物的标本,如老虎、狮子、驼鸟等;也有小动物,如蝴蝶、蝗虫等;还有养在生理盐水里的婴儿胚胎,从十几天到几个月的都有。各种动物、植物的标本,给我们的课本补充了实物的形象,同学们都很爱去。
我每天上学,都要经过鼓楼的城门。当时,高大的城墙还在。紧紧倚靠城墙的背面,是搭盖的大市场。城墙南是五只石刻的大狮子,中间一只最大,左右两旁各两只,略小。
我们放学时,也会去攀爬石狮的背,中间一只大狮子不容易爬上去,所以我只能爬两旁略小的狮子。爬上石狮,昂首挺胸,仿佛是已经脚踏青云,正要出征的勇士,何等威风。我们男孩子都以能爬上石狮为荣。当然,能爬上当中的大狮子则更威风。对连小狮子都爬不上去的小男孩,我们则耻笑他们。
城墙靠着石狮的两边,各开一道门,人们进进出出都要经过这两道门。至于何时拆迁市场,移走石狮,打掉城墙,因为我离开鼓楼就不得而知了。
有一天,学校在礼堂里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大会,四年级林而流同学上台,介绍他怎样机智勇敢迷惑敌人,抓住一个准备在柴火堆上放火的蒋帮特务的事迹:那一天下午,林而流同学放学回家,因为有事,时间拖晚了。当他走到一个在路边堆满松木柴片的柴炭店附近,忽然发现一个人在柴火堆旁边鬼鬼祟祟。他就紧紧跟踪,到了有人的地方大喊“抓特务”。在大人们的帮助下,抓到了这个企图放火的特务,交给了派出所。在人证物证面前,特务不得不供认了犯罪事实。市人民政府为了表彰林而流同学和我们学校,发文命名林而流同学为“模范学生”,将我们的学校改名为“模范小学”。全校师生都为我们有这样优秀的学生和同学,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会后响起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因为很长时间居无定所,我都休学在家,现在恢复上学,却不会背“乘法口诀”。这一天上午的最后一节课是算术,老师点名让我和几个同学留下,背颂“乘法口诀”,待会儿老师要来复查,会背的先回家。
大约十二点多了,算术老师来了,几个同学都顺利过关,回家了。只剩下我最后一个,但是我还是不会背。老师生气了。说:
“尹振铎,你平时的作业都不错,为什么不会背‘乘法口诀’呢?”
“我背不来,也不喜欢背。”
“那好,老师给你出两道乘法题,你要是能够很快做出来,我就放你回家。”
“好吧!”
“听好了。第一道题:19×;9=?”
“171。”
“你是怎么算出来的?”
“20×;9=180;180…9=171。”
“第二道题:15×;16=?”
“240。”
“回去吧!”
“老师,再见!”
“再见。”我刚走到教室门口,听见老师在对另一个老师说,“这个同学的思路,和一般同学不一样。”
妈妈已经卧病在床几天了,大小便都拉在床上。邻居闻到臭味来看了看,有人去印刷厂通报。厂工会主席带了人来,给妈妈换洗了床单和身上的衣裳。
这几天,我仍旧拿着铝锅到郑伯伯那里去打饭。吃了饭上学,放学早早回来,陪着妈妈。可是我一个小男孩,什么都不会帮妈妈做。看着妈妈时醒时昏,不知该怎么办才好。过了两天,厂里联系到二舅父、二舅母,将妈妈的事情作了交代。舅母再次换洗了妈妈的床单和身上的衣裳。雇了一辆人力车,将妈妈接到她家去。
我仍然在鼓楼继续上学。
没妈的日子里,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是惆怅,是失落?小孩子的感情有这么复杂吗?我只觉得,晚上一个人睡觉,总是睁大眼睛望着天花板,隔壁老奶奶描述的各种地狱酷刑,历历在目,好久好久才能入眠。
天明起来,又是打饭、吃饭、上学、回家。到了放午学,很不愿意立即回家,就漫无目的地在就近的街上徜徉。几个小孩在人行道上滚弹珠,我就驻足呆立一旁,作“业余裁判”。直到孩子们被大人一个个叫走,我才拖着沉重的双腿,慢慢地回家。
那时候还没有《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歌,要是有,我一定会一天到晚地唱的。我记得有一首歌,叫作《月亮在哪里》,我在数着脚步回家的时候,就是伴着这个曲调的节奏走的。
树上小鸟啼,江畔花影移,
我的妈妈,你如今在哪里?
当然,后一句是我自己加上去的。我也知道,妈妈就在南台横街横街巷十橺角。我记得去的路,虽然妈妈只带我去过两回。但是,她现在怎么样了呢?
有妈妈的时候,不知道珍惜;没妈妈的时候,才想起妈妈。这就是世人的常态。我一个不满十岁的男孩,又怎么能脱俗呢?
二舅母又到城里来了。说是妈妈病危,瞪着眼睛,口里不住地呼喊我的名字。舅父母怕妈妈的时日不多,特地来接我出去。
舅母到处找我,我仍在大街上蹓跶,快到午后一点才回家。舅母把我大骂一通,邻居们也在帮腔,骂得我抬不起头来。
舅母将我们简单的行李拢了拢,雇了车,就要把我带走。邻居大婶、大嫂你一言,我一语,尽是对我的指责:
“这孩子越来越野了,阿妗(舅妈)要好好管教管教他!”
“成天不在家,都在外面瞎混混,别让他上学了。”
“对,弄个竹篮子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