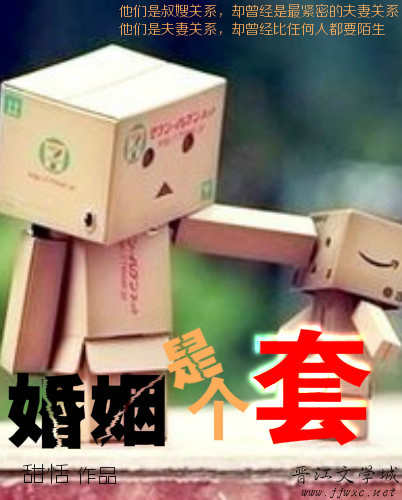连环套-第4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张铁虎见春宝还是铁青着脸,也害了怕,咕咚往春宝面前一跪,说道:“师兄,你消消气吧!都怪我不好,要打要骂都行,你可别丢下我们不管哪!”丁猛也觉得有点儿不对,咧着大嘴说:“怪我没听清楚,要打你就打我,反正不能放你走。你要走了,谁管饭哪?”
一句话把春宝逗乐了。他把二人搀起来说:“我不怕别的,就怕给咱师父找麻烦。你们想想,党鹏飞有权有势,能完的了吗?再说,咱还有咱的事,五月初五以前一定要赶到泰山,这可好,还能走的了吗?”
石宽道:“我看没关系,党鹏飞知道咱们是谁?现在咱们就走,他上哪儿找去?”李大成点点头说:“有理,有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咱们赶紧上路吧!”
富春宝一想,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他叫众人动手,在路边刨了个大坑,把十四具尸体草草掩埋,这才离开此地,奔泰山而去。所幸的是,身后无人追赶。他们一口气跑出二十多里,这才把脚步放缓。春宝看看天色将晚,便决定找个地方住下。这里山丘很多,重重叠叠,连绵不断,看样子一直通到泰山。在山丘下有个小村庄,零零散散,也就有十几户人家。春宝头前引路,不多时来到村里。紧对着路口,就是一家店房。面前挂着罗圈幌子,一块木制的招牌随风摇动,上写“招商老店”四字。
春宝招呼了一下几位兄弟,先迈步走进店房。房子挺大,迎着门是栏柜,有一人站在后边,正在品茶。此人四十多岁,面如蟹盖,大连鬓胡子,一对猫眼,五短身材,肚子突起,一对肉包子眼睛叽哩咕噜乱转;头戴逍遥巾,身穿灰布长衫,挽着白袖头。看样子不是账房先生,就是掌柜。有个伙计打扮的人,正趴到柜台上跟他说什么。
春宝他们一进来,这二人就不言语了。伙计转过身子,赶快笑着迎上来问:“五位大爷,要住店吗?”春宝说:“嗯。有干净房间吗?”那伙计连忙说:“有,有,包您满意。”丁猛也问道:“住不住是小事,有吃的没有?”伙计笑着说:“我们这儿又是店房,又是饭馆,煎、炒、烹、炸,什么好吃喝都有。”丁猛急着说:“好啦,快点做,快点做!都要把我饿死了!”石宽一听,气得够呛,在他后腰上狠狠捻了一把,傻子这才不言语了。那伙计说:“几位里边请。”
说罢,他在前带路,把小弟兄们让进后院。春宝一看,四处是石头砌的院墙,正房三间,地是沙石地,院子挺宽绰,房间也很整洁。进房后,伙计赶快让坐,往两边一指说:“这是一明两暗的房子,这是客室,两边是卧室。有个十位八位的也能住得下,您看行吗?”春宝到里间看了两眼,被褥都很干净,便对伙计说:“不错,就住到这儿了。”伙计退出去,不多时提来一桶净水。小哥五个洗了脸,烫了脚。伙计把废水拎走,又泡上茶来。春宝道:“我这位兄弟饿了,你们有现成的饭菜吗?”那伙计道:“熟食有酱牛肉,酱豆腐、馒头、花卷、大火烧,还有糖麻花,咸鸭蛋、五香豆腐丝。”春宝道:“挺好,每样来一盘,我们就吃这个。”那伙计说声:“好嘞!”便退了出去。
李大成凑近春宝说:“我发现柜台里坐的那个人不像是好东西。”春宝笑道:“怎见得?”李大成挠着脑袋说:“我也说不准,看着他就别扭。”丁猛道:“别光说人家!人家看你还别扭呢!”
这时,门外脚步声响,伙计双手端着大托盘走了进来,足足摆了一桌子,然后又端来两壶酒,放下五只酒杯。春宝说:“天怪热的,不喝酒。”伙计笑道:“大爷,这个酒您是非喝不可。”
春宝一愣,问道:“为什么?”伙计道:“原因有三:一,这种酒是我们本地的特产,叫‘蜜里香’,又清香,又甜美,凡是到我们这儿来的客人,没有不喝的;二,这种酒不上头,不误事,喝下去又解渴,既舒服,又解乏,甭提多美了;三,咱们招商老店还有个规矩:凡是初次来的客人,必敬酒两壶,白喝不要钱。为什么呢?这叫拉主顾,希望您下次再来。”
石宽笑道:“这么说,我们也只好领情喽!”伙计笑着直点头,给他们每人都满了一杯。果然不假,这酒往外一倒,香气四溢,沁人肺腑。别说会喝酒的,既使不会喝的,也会垂涎三尺。丁猛一口把酒喝干,吧嗒吧嗒嘴说:“好酒,真是好酒,又甜又香!我再来两杯。”伙计又给他满上,傻小子一扬脖子又喝干了。石宽也喝了一杯,果然不错。他笑着说:“伙计,再来两壶,我喝上瘾了。”春宝本来就贪杯,只是出门在外,又是当师兄的,处处都得检点一些。他一看石宽喝得如此香甜,也就控制不住了,一口气连干三杯,觉得十分舒服。张铁虎、李大成见师兄都敞开喝了,还有什么可顾忌的,他俩频频举杯,也喝了起来。一眨眼,四壶、六壶、八壶都喝干了。哥五个往桌上一趴,谁也动不了啦。为什么?原来他们中了蒙汗药!
那个伙计走进房,看了几眼,又用手推推几个人,放声大笑:“小子们,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看你们还往哪儿跑?”他把手指伸到嘴里,吱一打口哨,伏兵四起,闯进房来,把五小紧紧地绑了。
书中代言,这地方叫靠山屯,乃是皇粮庄的一个点,专做黑道上的买卖,挣了钱,算是打手们的外快,出了事有党鹏飞顶着。这小子不但借收皇粮为名,抢男霸女、压榨百姓,还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这里的头目名叫猫头鹰孙拐,就是坐在柜台后面的那个家伙。副头领就是这个伙计,名叫铁画眉孙连。他们手下,还有十几个帮凶;有的掌勺,有的在面案上干活,有的管采买,有的赶车,还有的四处踩盘子,通风报信。总而言之,连一个好人也没有。
踩盘子的这个小子名叫飞毛腿李谷。他过响到皇粮庄去办事,正遇上黑三挨打、金面瘟神佟豹大败而归。黑三和佟豹一看死了那么多人,逃跑的那个张氏也没抓回来,庄主非生气不可。铁画眉孙连献了一计:放长线钓大鱼,想办法把他们稳住,争取一网打尽。黑三大喜,暗中派人监视着五小,一看他们奔靠山屯那个方向去了,赶快叫飞毛腿李谷绕小路回去报信,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五个人溜掉。他和佟豹回庄调动人马,及时接应。
飞毛腿李谷回到靠山屯,对两个头头一说,当下就做好了准备。他们的办法是,尽量用软招智取,实在不行,就用武力解决。于是,他们把人都埋伏好了。五小毕竟涉世不深,经验不足,中了人家的蒙汗药。
再说铁画眉孙连和猫头鹰孙拐,把五小拿住,欣喜若狂,立刻派李谷去皇粮庄报信。李谷刚出靠山屯,迎面正遇上黑三和佟豹领人往这儿来。李谷边跑边喊:“抓住了,都拿住了!”黑三一听,长吁了一口气,急切地问道:“人在哪里?”李谷答道:“都在店里,听候三爷发落。”
黑三一招手,率领众人走进靠山屯,不多时闯进招商老店。铁画眉和猫头鹰赶快迎出来,把黑三让进后院,又令人把店门关闭,派出卡哨。黑三往院里看了一眼,就见五小躺在地上,口吐白沫,五官抽搐。孙拐解释说:“他们喝了蒙汗药酒,用冷水一喷就能解了。”黑三道:“先别解!这几个小子的得很。就这样押回庄去,交庄主发落。”
铁画眉立刻派人套好车,把五小及兵刃扔到车上,起身回庄。铁画眉孙连随车同行。猫头鹰孙拐仍然留在店里,照顾生意。黑三和佟豹监押着车辆,径直赶奔皇粮庄。
天刚擦黑,已经看见庄门上的风灯了。黑三紧催老板:“快,快点儿!”老板把马鞭晃了两晃,眨眼就来到护庄河前。佟豹冲着庄门喊道:“开门!放吊桥!”庄客问道:“谁呀?”黑三答道:“我,佟豹,黑三!”庄客道:“哟,三爷回来了,佟师父也回来了!快放吊桥!”庄丁们一纹辘辘把,九尺宽、半尺厚、两丈八尺多长的柳木吊桥咣当当放下来了。庄门吱呀呀大开,灯光闪动,人影摇摇,有人接了出来。
黑三,佟豹押着车上了吊桥,从北门进了皇粮庄。他们把车赶到党鹏飞的宅第前,只见灯光明亮,守卫重重,府门敞开着。黑三叫车停住,令人把五小从车上抬下来,连同兵刃都架进府中。他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和佟豹并肩走进前厅,对内当差说:“请您禀报庄主大人,就说我们有急事求见。”
内当差转身去了。约有片刻工夫,八名俊童分为左右,接着有人咳嗽一声,党鹏飞迈步走了进来。黑三和佟豹单腿打千儿,低头迎接。党鹏飞往金漆高交椅上一坐,头枕到靠背上,官气十足地问:“有话说吧!”
黑三和佟豹同时答应了一声“嗻;”,互相看看,佟豹示意让黑三说话。黑三往前挪了两步,哈着腰,奴颜婢膝地说:“奴才回大爷的话。”于是,黑三把以往的经过讲了一遍。党鹏飞听罢气得把桌子啪一拍,厉声喝道:“饭桶!可恶!你们太他娘的蠢了!”
黑三、佟豹吓得直哆嗦,齐声应道:“是,奴才们该死。”党鹏飞骂了一阵之后,又问道:“你说的这五个小子是谁?叫什么名?哪儿来的?”黑三说:“这……这个,奴才还没来得及问。”党鹏飞又问:“人在那儿?”黑三答道:“都放在院子里了,听候大爷的发落。”党鹏飞下令道:“带上来!”
黑三和佟豹应声退到外边,把头上的冷汗抹掉,吩咐庄丁提桶凉水来。铁画眉接过水桶,用凉水往五小头上泼去。时间不大,哥五个就先后清醒过来了。富春宝睁开眼睛,觉着不对劲儿。他身子一晃,才知道被绑了。他叫道:“啊,这是怎么回事?”忽听身边有人狞笑。春宝借着灯光看了好一阵儿,才认出是黑三,还有店里那个伙计。再看那哥四个,一霎时他全明白了,真是追悔莫及。紧接着石宽、张铁虎、李大成都醒了过来,纷纷惊呼道:“哎,这是怎么回事?”
黑三冷笑道:“三爷要扒你们的皮!小子们,叫你们多管闲事!这就是尔等硬充英雄的下场!起来,别他娘的装蒜!”庄丁们手舞皮鞭,劈头盖脸就打,把哥几个打得直皱眉。最后醒过来的是丁猛。他把眼睁开,往左右看看。啪一鞭子正抽到他脑袋上。庄丁喊道:“起来!”咣咣又是几脚,傻英雄晃里晃荡地站起来,连拨浪脑袋带眨眼睛,瓮声瓮气地说:“别闹!这是干啥!”黑三喝道:“谁和你闹了?少装疯卖傻!来人,快把他们带进大厅!”
庄丁们应声挥拳抬腿,连拖带拽,把五个人押进厅房。到这阵儿,哥几个才真正清醒过来。他们借着刺眼的灯光,定睛瞧看,只见这座厅房十分宽大,油漆彩绘,光彩映人。迎门有一张红木雕花条桌,后边放一把乌木漆金靠背椅。再往后是八扇屏风,屏风上画着泰山八景。八个眉目清秀的俊童,垂手站在两边。左右有两溜椅子和茶几,却空无人坐。在大厅两侧,站着几十名庄客和打手,手里都提着木棒、皮鞭,一个个横眉立目,气势汹汹。大厅的藻井上,吊着一盏玻璃灯,四周有立灯和壁灯,照得人连眼都难睁。
他们往正中央的椅子上一看,坐着一人,头戴亮纱软帽,脑门上镶着一颗珍珠,大如算盘子,光芒四射。这个人身穿团花马褂,内衬大缎子长袍。一张冬瓜脸,又灰又黑,又青又紫;三角眼,大鹰勾鼻子;一张蛤蟆嘴,嘴角耷拉着;鼻子下边留着燕尾八字胡,长可过寸;两颗大门牙龇在唇外,真是其凶无比,令人作呕。别看他模样不怎么着,架子可够足的:头枕到靠背上,两只三角眼眯缝着,双手搭在桌案上,手指上的宝石戒子闪闪放光。这就叫狗尿苔不济—;—;可长到金銮殿上了。打手们吆喝道:“跪下!跪下!”众家丁又按又压,小哥五个说什么也不跪。
党鹏飞双眉紧锁,冲打手们一摆手,他们才不咋唬了,乖乖地退在两旁。党鹏飞把眉毛一挑,官气十足地问:“尔等是什么人?受谁的主使与本大爷作对?难道你们吃了熊心,咽了豹胆?莫非没长耳朵,打听打听大爷是谁?”庄客们连喊带叫道:“说!大爷问你们话呢?快说!快说!”一个个狗仗人势,十足的奴才相。
春宝一听这人的口气,再看看这种架势,就断定他是东霸天了。他有心报真名,又一想不行,不能给师父找麻烦,干脆拿他开开心吧!春宝想到这里,不慌不忙、似笑非笑地说:“你就是东霸天党鹏飞吧!嗯?”庄客们怒道:“大胆!我们大爷的官印,也是你随便叫的吗?打他!打他!”众庄客一阵狂吠。
春宝毫不理会,只管往下说:“你是爷,我们哥五个也是爷;你叫东霸天,大爷我叫独霸天。用不着谁唆使,爷儿们专管人间不平之事,也专门对付像你这样的人!你敢把爷儿们怎么样?”石宽插嘴道:“党鹏飞,要论耍人,你可差得多了!爷儿们是在大海里游逛,你小子只配在痰桶里扎猛子。在爷儿们面前哪有你的份儿?”丁猛大叫道:“你是孙子,耷拉孙儿;我们是爷爷,你的祖太爷!”张铁虎用膀又撞了一下丁猛,不满意地说:“我才不干呢!谁要他这样的孙子,给老祖宗丢人现眼找挨骂!”
党鹏飞的脸一下变成了猪肝,气得浑身战抖,手脚冰凉,吼叫道:“放肆!大胆!不知死的狂徒,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我割了你们的舌头,碾碎你们的骨头!来人,把他们吊到院里,狠狠地给我打!”
庄丁们齐声应道:“嗻;!”说着七手八脚便往上一拥,把弟兄五个拖到当院。早有人把立桩、横杠和吊环备好,不容分说,把们们吊了起来。
党鹏飞令人把椅子搬到廊下,往那一坐,指挥着动刑。皮鞭啪啪啪飞舞,像狂风暴雨般地落到五位小兄弟身上。春宝紧闭双眼,舌头尖儿顶住上牙膛,丹田用力,运用气功。他这样做,为的是增加抵抗力,减轻点痛苦。石宽也用了同样方法。他早会气功,只是不那么精通罢了。丁猛皮糙肉厚,练的是金钟罩、铁布衫、只要他运上气,比谁都来劲儿。只见他紧闭双眼,呼呼地睡着了。苦就苦到张铁虎和李大成身上了。他俩一不会气功,二不会横练儿,只好咬着牙硬挺。皮鞭像带牙的毒蛇,撕破了他们的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