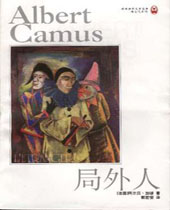崇祯大败局-第1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二人想跑腿已直不起,不一刻就捅成了马蜂窝,毙于狱中。
次日子时前后,黄宗羲正在客栈灯下看书,忽听楼下有叫门声,黄宗羲本未在意,不想来人却叩响了自己房门。开门看,并不认得。
那人也不等主人让,就闪进来,关上门。
不等主人开口,先说道:“公子不必紧张,在下不是歹人,我乃令尊昔日同僚。公子可知道李实?”
黄宗羲腾地站起:“就是那个诬陷家父的老太监?”
“是他,但他并未诬陷令尊啊!”
“屁话!他一纸奏折将家父等七人送进地狱,此时想自己迈过鬼门关?哼!先问问我饶过饶不过!”
“公子别急,坐下听在下细说端详。”他不等主人让座也坐下,“令尊在家赋闲时喜爱游湖,李实任苏州织造时也常去游湖,不想一来二去有了传闻,说令尊想效仿前朝刘一清联络张永除刘瑾故事,欲借李实之手除掉魏忠贤。还不是因为令尊与李实有泛湖之交嘛。”
武宗朝时,大太监刘瑾擅权贪婪,排陷异己,并谋夺朝,京营提督军务杨一清,与监军太监张永共谋,张永向武宗密奏刘瑾十七件不法情事及反叛形迹,刘瑾被逮,家中抄出金银数百万两并伪玺、玉带,被处凌迟。
“糊弄鬼呐!在苏州时,李实确曾登门求见,不过是附庸风雅之举,但家父并不肯见,何来泛湖之交?”
“见与不见,传言已起呀!那还躲得过东厂的耳朵?魏忠贤立刻派人往江南暗中查访。恰巧李实的司房正在京城办事,得知了这个消息,不及向李实禀告,先带着厚礼跑去崔呈秀处求助。崔呈秀正琢磨如何向东林开刀呢,一听之下大喜,给那司房出了个主意,以李实之名,奏令尊等人一本。那司房进京公干,正好带着盖了李实印的空印本,当下崔呈秀代写了奏疏,呈了进去。确非李实所为呀,他都不知呀!”说完这番话,就怀中掏出一张银票,“李实虽未实谋令尊,但具其名,不为无过。这是三千金,以补其过,只望公子勿再追究。”
黄宗羲一抬手将银票挥落地上:“我父冤魂只值三千金?哼!大堂上见!滚!”又将银票捡起,将那人推出门外,扔出银票,“嘭”地摔上门。
'1'官府限令吏役办事,如果不能按期完成,就打板子以示警惩,叫做追比。
第十章 抓阄选拔内阁大臣
枚卜阁臣
钦安殿是大内供神之所,供奉着玄武大帝。
崇祯身着皮弁服,率百官向玄武大帝行了礼。执事捧上金盘,盘中盛着十二粒红蜡丸,就是廷推的十二名阁臣候选之人,将名姓做成纸团,用蜡封住。执事将蜡丸一股脑倒入金瓯,崇祯先默祷了半刻工夫,祈求天佑神助,给他谋国良材,然后焚香肃拜,便伸银筷入瓯,一番搅动后随手取出一粒,再搅动一番取一粒,先后取出五粒。
崇祯打开第一粒,里面是张红纸条,崇祯刚想细看,一阵风吹来,把纸条卷走,遍寻不见,无奈之下,不再打开另四粒,转交给执事拆封。执事逐一唱出名字:李标、钱龙锡、来宗道、杨景辰。
崇祯听了,轻轻叹息一声,默了一刻,才道:“黄阁佬屡疏请辞,年纪不饶人啊,朕心也是不忍,就准了吧。李标、钱龙锡、来宗道、杨景辰四人入阁辅朕。元治为首辅,即日视事。”
黄立极顿感浑身一阵轻松,李国却骤然紧张起来。尽管这是个人人觊觎的位置,但如今可不是太平盛世,内忧外患乱到不可收拾,新皇帝又是如此了得,还是个不留情面的,责任太过重大,况且自己是魏忠贤同乡,受魏提携才入阁,一为首辅,就到了风口浪尖了。妥为预后,还是人多商量着办事好,于是出班奏道:“陛下信赖,敢不竭尽驽马,只是如今百废待兴,诸务庞杂,事关重大,以臣几人之力,恐有负圣托。俗语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恳望陛下破常例,增阁臣,集思广益,庶可有慰圣虑。”
崇祯想想也是,这年头事出百端,头绪繁乱,人少了也是难考虑周全:“卿言有理,再掣二人吧。”
执事官捧过金瓯,崇祯起身离座,复拣出两粒红丸。执事官接过破开展读,是周道登、刘鸿训二人。
崇祯道:“李标、刘鸿训已为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其余四人并封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
六人齐刷刷出班跪谢,起身后,杨景辰道:“陛下,黄宗羲闯牢杀人案该如何处置?”
“什么?”崇祯睁大眼,“他杀人了?杀谁了?”
“杀了两名狱吏。”
“他为何要杀狱吏?”
杨景辰嗫嚅半天没说出子丑寅卯。
李标心中明白,杨景辰出此一问,是因为他与阉党也有干系。如果崇祯处置黄宗羲,则东林必有收敛,自己或可不受牵连。但正因他与阉党有染,所以便不好回答“为何要杀狱吏”。
李标便道:“叶咨、颜文仲二狱吏是毒杀东林七君子的刽子手,黄宗羲是为父报仇。”
“谁是东林七君子?”
“东林有前六君子和后七君子。天启五年,魏忠贤逮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六人下狱,刑死于狱中,时称前六君子。天启六年,魏忠贤再逮高攀龙、周顺昌、周起元、缪昌期、李应升、周宗建、黄尊素七人,高攀龙投水死,六人刑死狱中,时称后七君子。”
“嗯,都是硬骨啊。朕听说了黄宗羲大堂之上锥刺许显纯、崔应元,不知他竟杀了人。昨日接通政司转呈的黄宗羲折子,说李实将人向他行贿三千金。一个太监竟有三千金私房,不是阉党是什么?阉党就是国之大蠹!”说到这崇祯低头不语了,心下掂量,一介书生闯禁地、杀职吏,按律当斩。但处置了黄宗羲,东林必气馁,彻查逆案便成虚文。左右思量,还是以当前情势为重,拨乱反正,重塑绝对皇权才是固本之策,便道,“六君子、七君子受祸之酷,天下掩耳侧目。黄宗羲为父报仇,是为孝子,情亦可悯。处置这样的人,有违朕以孝治天下的初衷。二狱吏虽然受人指使,毕竟血债累累,不问了,摆驾吧。”
李标斜眼看杨景辰,已有些作色了。
众臣陆续走出,施凤来刚一抬脚,一张纸条从袍下飘出,施凤来赶忙捡起,展开一看,上写着“王祚远”,施凤来轻摇摇头道:“命该如此!”就揣入袖中。百官退出后,崇祯便怀揣着这六张红纸条,带着王承恩直去了午门五凤楼。
五凤楼是宫中“厌胜”之所,供奉着永乐皇帝朱棣“靖难”和五次亲征蒙古用过的“赤缨”、“玉勒”、“驼鞍”和刀枪旌旗,被视为神物,有消除一切不祥之力,用作“镇物”。
崇祯将六人姓名摊开于镇物之下,又向先祖默祷一番,只见那折页瑟瑟抖动,崇祯心下轻松了不少。
徐时泰回到翰林院进了屋就坐下捯气儿。众人见他这般模样,就围拢了来:“怎的了,龙颜不悦了?”
“那倒不是,”徐时泰端起茶一口灌下,“唉”了一声,“今日日讲,本该讲《帝鉴图说》,可皇上给改了,要讲《通鉴》!我毫无准备,如何能讲!只好回答不曾准备,不敢虚应漫对。皇上要我准备,明日要讲。皇上总是突发奇想,真是应付不来!”
“谁叫你是翰林院侍讲?还是多准备几样吧!既然没讲,怎么去了这么久?”
“皇上今日心绪大坏,上午接陕西巡按御史吴焕奏疏,陕西府谷县王嘉胤、安塞马贼高迎祥先后率众造反,延安卫柳树涧的犯卒张献忠领米脂十八寨起兵,白水王子顺攻打蒲城、韩城,清涧王佐挂在宜川造反。皇上叹息不已,问我可有善策。”
“是啊,听说王二已与王嘉胤部会合,有众五六千人,聚集在了延庆的黄龙山。”
“还有什么杨六郎、不沾泥。高迎祥自号闯王,张献忠自号八大王,又称‘黄虎’。”
“还不止这些,还有汉南王大梁、阶州周大旺、宜川飞山虎、大红狼、苗美、洛川王虎、黑煞神、延川王和尚、混天王、庆阳韩朝宰。全陕无宁土了!”众人七嘴八舌,把自己听说的都端出来。
孙之獬问徐时泰:“你怎么回皇上的?”
“我说容臣细想,明日禀报。”
“蠢材,你那脑壳除了之乎者也、子曰诗云便想不出别的。”
倪元璐道:“他能有什么办法?陕西连年大旱,草木枯焦,乡民争食山间蓬草,蓬草食尽,剥树皮而食,树皮又尽,掘山中石块而食,官府却仍严加催科,只好相聚为盗。反贼中还有叛卒、逃卒、驿卒,乃是因卒饷逐年拖欠,士卒稽饷而哗,亡命山谷,倡饥民为乱。”
“皇上也是如此说。皇上还提起一事,南京兵部武选司主事别如纶为《三朝要典》上疏,说许显纯辈捏造杨涟、左光斗等的所谓供词都载于《要典》,崔呈秀的疏文也赫然列于篇末,与圣意相背,应该删削,以重定是非。皇上问我有何想法。我怎知圣意背是不背?只好说全凭圣裁。皇上说,虽书中人品不同,议论各异,孔子云,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朕仰承谟烈,俯察品流,存此书以定君臣父子之衡,有何相背?别如纶妄言,姑不问。”
“别如纶拍皇上马屁拍马腿儿上了,活该!落个不问,算他万幸!”孙之獬愤愤地说。
“——我看不然。”倪元璐诡秘一笑,“既是‘有何相背’,皇上又何必私下问臣下?既是妄言,又为何不问?”
徐时泰瞪着倪元璐:“你是说——”
“皇上如无想法,不会主动咨问,只是别如纶没说在点儿上。《要典》乃先帝钦定,说与当今皇上心思相背,岂不是说皇上有背先帝?”
“你有何根据?”孙之獬逼前一步。
那日上朝,倪元璐公开指斥阉党,是认为如果有人朝堂之上首指群奸,便有可能一呼百应,皇上才好动作,他愿意当这出头榫子,但看来今日这些臣子已经没有杨涟之辈了。听孙之獬这一问,倪元璐伸出三指:“清除逆党,必走三步。一杀魏阉去其势,二定逆案去其人,三毁《要典》去其论。当今天子是个大智大睿的圣主明君,处处看得透彻,并且先人一步。但《要典》前有先帝御制序,皇上是投鼠忌器,所以要投石问路,试探舆情。”
“胡说八道!”孙之獬勃然大怒!
倪元璐鄙夷地看了他一眼,转头对徐时泰接着道:“只有拿《三朝要典》开刀,才能拨翳舆论、澄澈公理、清明政治、恢复史貌,永绝后患。《要典》对梃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三案颠倒是非,加罪东林,一举剿灭。不翻三案,一是不能打开思想桎梏、铲除阉党遗迹;二是史墨长存,后人如何评说?但去林中盗易,去衣冠盗难;去身外盗易,去心中盗难。《要典》编纂官员众多,阻力当不在小,又有先帝御制序,若不能一鼓而毁,徒乱人意,局面必多窒碍,这才是使圣上颇费犹疑之处,必须谋定而后动呵。”
孙之獬气得浑身乱抖:“你、你大逆不道,不忠不孝,无君无父,无臣子样,无——”
“无耻之尤!”倪元璐也怒了,“你是魏忠贤的孝子贤孙!”
“我把你这奸佞小人——”孙之獬说着就要抬胳膊抡腿。
“二位二位,”徐时泰看两人就有拳脚相向的架势,忙起身立于二人之间,“本不关二位事,何必衅起阋墙?”孙之獬“哼”了一声,一甩袖走了。徐时泰转向倪元璐:“既如此,该如何表态?”
“如何表态?上疏!焚了那《三朝要典》!”
“啊?毁《要典》?”
“对!……《要典》功罪不明,邪正颠倒,邪说横行,不毁不能正视听!”
阉党哭殿
崇祯刚放下笔,听见外面有人号啕大哭,崇祯侧耳细听,隐隐听见那人边哭边诉,说什么“先帝的御制序岂可投之于火?于祖考则失孝,于熹庙则失友。陛下于熹宗同枝继立,曾北面事之,何必如此忍心狠手……”崇祯勃然大怒,问道:“王承恩,外面谁在哭?”
王承恩跑进来,道:“是翰林院侍讲孙之獬在东阁外哭呢。”
文华殿与内阁只一墙之隔,内阁设此本就是为皇上招呼方便。
“为什么?”
“他说倪元璐给皇上上书了,劝皇上毁《要典》,居心险恶。”
崇祯冷静下来。他接到倪元璐的《公议自存私书当毁》的奏疏便一口气看完了,击案而起:“朕无顾忧了!”但再看下面就来气了,来宗道代皇上票拟的谕旨写道:“所请关系重大,着礼部会同史馆诸臣详议具奏。”崇祯提笔批道“听朕独断行”,随后就接到杨维垣的疏奏,斥责倪元璐“词臣持论甚谬,生心害政可虞!”
倪元璐、孙之獬都在翰林院供职,看法便如此悬殊,朝臣中便不知是倪元璐多,还是孙之獬多了。
“叫李国、来宗道来。”崇祯吩咐道。王承恩颠儿颠儿出去,打个哈欠的工夫二人就进来了。崇祯问道:“孙之獬为《要典》事跑到你那儿哭闹?”
“是,他就是力言《要典》不可毁。”李国道。
“你怎么说?”
“臣当下斥责了他,他就大哭起来,提出罹疾在身,不能供职,请准其归家调养。”
崇祯想了想道:“依你们看,倪元璐与孙之獬,谁有道理?”
二人互相看看,来宗道说:“臣以为,取其中者。”
“何谓取其中者?”
“《要典》可删改而非毁。”
崇祯脸色一暗,把此事搁过:“大奸既除,你们看当今第一要务是什么?”
李国想都没想,道:“回陛下,臣以为是边事。”
崇祯点头道:“朕是要一意边事了。辽东经略王之臣有劳无功,朕看不可再用,你们看何人可继任?”
“臣以为孙承宗可用。”李国道。
崇祯眼睛一亮:“孙承宗?朕知道。经略蓟辽四年,拓地四百里,屯垦五千顷,岁入十五万。”
“陛下真是胸藏经纬。当年孙承宗因柳河之败受阉党弹劾,周道登曾保奏,查核过孙承宗边功:修建大城九座,堡四十五座,立车营十二,水营五,火营二,前锋后劲营八,练兵十一万,造甲胄、弓矢、炮石、渠答、火器、卤盾之具合数百万,是统帅之才。”
崇祯边听边点头,脸上阴转晴:“知道了,你们去吧。”
李国犹豫了一下:“陛下,吏科都给事中沈惟炳有奏,”说着从袖中抽出一份奏牍,见崇祯在注意听,便读道,“旧例,阁臣会推应集九卿科道各官商议,由吏部将公议名册报皇上定夺。如果先期不谋之众人,临事乃出其独见,难免以私损公。臣以为以后会推应限定期限,将吏部所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