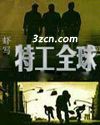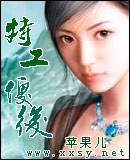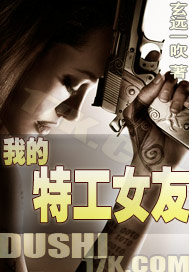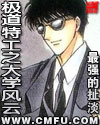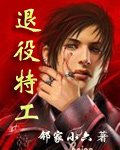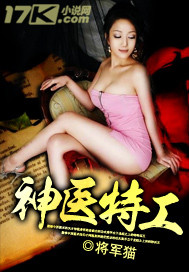红色国际特工 作者:张晓宏 许文龙-第2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王方当时只当是缪勒尔在开玩笑,不料后来,这位情报专家真的去了中国,王方不仅成了他的导游,还成了他的助手。
王方在接受训练时也有别于其他学员,他接受的训练更多是无线电通讯、绘图、情报传递。也就是说,案头工作多了一点。然而,王方自己却不敢掉以轻心,他努力学习爆破、刺杀、射击技术,格斗训练也格外卖力气,有一次他竟接连摔倒了二名蒙古学员,令对手大吃一惊。每天清晨,他总是一个人围着操场跑步。同学们问他为何给自己加大运动量,他总是笑呵呵地告诉大家,是在练脚力。后来,王方的这种练习真的派上了用场。
一天,杜曼宁将王方带到一间地下室里。这间地下室里的每一面墙上都一排排地挂满了钥匙,少说也有成千上万把,都分别编上了号码。他告诉王方,情报局技术处得到或秘密复制了许多国家的办公室、旅馆和私人住宅的钥匙,每一把都编了号。多年来,他们就是用这种办法进入敌国各地的房舍里的。
“说不定什么时候其中一把钥匙就会派上用场。” 杜曼宁向王方解释说。王方被他的这一收藏杰作惊呆了。
“首先必须记住,要进别人的房间,撬锁是万不得已的最后一招。” 杜曼宁在他的讲座中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样说的。“要想不刮伤漆就把锁撬开是完全不可能的。受过训练的情报人员一眼就能看出来,他会知道有人进过房间了。你们应该做的是搞到一把钥匙。这有两种办法:一个办法是测量锁的尺寸,另一个办法是复制一把钥匙。”
杜曼宁对如何撬开各种各样的锁做了示范。波马牌锁是一种主要装在珠宝保险柜上的锁,其锁栓是穿过锁簧活动的,最难撬开。匠布牌锁虽然是号称无法撬开的铁将军,可它在杜曼宁手里却变成了儿戏。
“你们以后会经常跟这种锁打交道的。”
他从堆在柜子上的耶鲁牌机械锁中拣了一把来给王方们做具体的撬锁示范。他解释说,耶鲁锁有一系列销栓,排在锁眼内的不同位置上。钥匙伸进锁内,其齿把锁眼内的销栓顶上去后,才能转动。杜曼宁拿出一根铁丝,铁丝的一端有钩子。他把铁丝插进锁眼内,然后开始平稳而有节奏地捅着。
“先捅第一个销栓,”他的手腕时而紧张,时而放松,“直到它伸进一个回进去的地方,你就知道捅开了一个销栓。”
他那双大手宛如音乐会上一个手握琴弓的小提琴演奏家的手,紧张地挥动着,一个接一个的销栓被捅开了。
“在没有捅开所有的销栓之前,必须保持压力。”他转动手中的铁丝,耶鲁锁立即弹开了。“这下你就可以进屋了。当然,进了房间以后,你要干什么,那是你的事了,我可管不着。” 杜曼宁风趣地补充道。
杜曼宁对他从什么地方学来的这些撬锁专门知识从不透露一丝口风。此后多年,王方一直带着杜曼宁为他亲自制作的一根铁丝和撬锁工具。
1934年2月,王方等人结束了为期两个月的培训,准备启程返回国内。临行前,杜曼宁来到他们中间交待任务。
杜曼宁对王方说道:“之所以这样急就让你们回国,主要是因为那里的工作需要你们。”
王方问道:“杜曼宁同志,我们将如何开展工作呢?是按以前的组织办法去做吗?”
“不,你们要有所变动,”杜曼宁说,“你们将会有新的领导人,他将带领着你们开始一种全新的工作方法:你们回去以后,先在哈尔滨待命,不久就会有人去找你们接头。”杜曼宁说完将一张一美元的钞票交给他。
“记住上面的号码,当另一个人拿一张号码相邻的美钞时,他就是你们的联络员。”杜曼宁晃了晃手中的美元,“要绝对相信此人!”
王方收好美元,向杜曼宁敬了一个军礼。
迎着刺骨的寒风,王方和两名同志踏上了返回东北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快车。
一星期以后,王方等人仍旧从扎赉诺尔越境,回到了北满。
尽管预备学校是很隐蔽的,但仍被经验丰富的张逸仙发觉了。一天,他悄悄对杨奠坤说:“你知道么,在咱们附近还有一所情报学校。”
杨奠坤吃惊地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张逸仙告诉他:“有一次上爆破课,我看见从东面树林的别墅出了一群穿便服的中国人。”
4月,紧张的学习生活结束了。学校举行了一个毕业仪式,杀了一头猪聚餐。第三期学员用苏、中、蒙三国文字写了一条大幅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把餐厅装饰起来,佳肴摆了一桌子。下午四点,几位情报部的同志来了,他们簇拥着身穿便服的别尔津,来到席间就坐。别尔津坐在主位上,首先讲话。
别尔津用富有感染力的声音说道:“亲爱的同志们,你们结束了紧张的学习生活,就要回到各自的祖国,战斗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最前沿。随着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危险越来越近。到那时,你们将发挥你们的作用,你们所学的所有内容都会派上用场。实践将会证明,你们是革命队伍中的精英。”
别尔津的讲话赢得了学员热烈的掌声。
张逸仙代表学员讲话,他用纯熟的俄语庄严地说:“我们在这里接受特殊的培训,为的是更好地打击敌人。面对领导和关心我们的同志们,我代表全体学员只想说一句话,那就是:一切要用行动来表现,我们愿以将来的努力代替一切语言的表白!”
最后,别尔津同志和大家碰杯共进午宴。到了傍晚,大家酒醉饭饱;一齐唱起“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第二天,蒙古同志都回国了。第三期学员的六位中国同志,写了一份工作“誓愿书”,表明自己的决心。其中大意有三点:
1、我们用百分之百的努力去工作。
2、绝对服从命令遵守纪律。
3、无论遭受任何危险,也不说出组织秘密。
誓愿书交给缪勒尔后便没了动静,主管学员派遣分配的杜曼宁将军也没有来找他们。
大家开始焦虑不安,只有杨奠坤一个人很沉住气,他知道他们将干什么。
三天后,杨奠坤被别尔津召见。
别尔津还是像以往那样走到他的面前,双手搭在他的肩上向后一仰,盯着他的脸。
“瞧,你多么年轻,未来的世界是你们的。我老了,有些事可能无法完成,就靠你们了。”
杨奠坤能感觉到别尔津有些伤感,但他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别尔津同志,我就要回国了,请您指示。” 杨奠坤站在那里,平静地注视着他所尊敬、爱戴的首长和老师。
别尔津从保险柜里取出两张五元的美钞,把其中一张递给杨奠坤,说:“这不是你的经费,这是联络暗号。你回国后,有人会跟你接头,你会拿到另一张做交换,要记住这两张钞票的号码。你可以像信任我一样信任他。要坚信他是我派去的可靠人。”
杨奠坤接过钞票并熟记了号码。然后他问道:“戈比旦行动何时实施?”
“到时你会知道的。”别尔津平静地说。
临出发前一天,缪勒尔和杜曼宁来看望三期的中国学员,大家在室内合影留念。
然后,杜曼宁把大家分别叫到楼上,很详细地作了一次登记。
六名中国学员分成两组,杨奠坤带一组先出发,张逸仙带一组六小时以后出发。
校内的工作人员,高喊着“努力”将他们送出了学校大门。缪勒尔和鲁迪分别送他们去车站。当送到张逸仙时,缪勒尔送给他八盒香烟。当然,这不是普通的香烟,而是八盒“黑索今”炸药。鲁迪拉着张逸仙的手说:“古斯达夫,我的好朋友,让我们共同努力吧!将来你在下面‘澎’(爆破),我在上面‘澎’(投弹),一起消灭敌人。”
张逸仙和鲁迪紧紧拥抱。
在悲壮的告别声中,大家登上了东去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火车。
鲁迪·缪勒尔,飞行学校毕业后参加了西班牙战争。1938年,鲁迪化名王有生参加苏联援华志愿军,来中国对日作战,驾驶着“伊一96”歼击机浴血奋战,在武汉保卫战中壮烈牺牲。
1935年5月,第四期学员也毕业了。同样是杜曼宁找陈冰岩等人谈话,并告诉他,回国后,住在北平,找个学校学习,以学生身份做掩护,等待组织接头。而后,照例开始填表,当时有一个问题,却令陈冰岩疑惑了一阵子。
杜曼宁突然问道:“你是中共党员吗?”
陈冰岩愣了一下,自己是不是党员呢?既然自己一直为中共党组织工作,那就一定是党员。于是,回答:“ 我是党员。”
杜曼宁不假思索地记录下来,可能在他的印象里,来学校受训的都是各国党组织中最优秀的分子,自然是党员。
陈冰岩和班里仅有的四名同志编为一组,他为组长。虽然,他们的目的地不同,但却都是在一处地点扎赉诺尔越境的。
大概,第四期学员不像杨奠坤等人员有重大使命。所以没有举行欢送仪式,而是静悄悄地上路了。
在西伯利亚大铁路列车上,陈冰岩开始思念一人,那就是王耀南。
王耀南此刻仍在军事情报学校,他在着手准备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陪同缪勒尔去中国。
原来,雄心勃勃的情报大师、特工校长缪勒尔再也奈不住寂寞,他要去中国实地看一看。一方面了解中国的国情,另一方面他要亲自指挥他的学员,开展史无前例的对日情报战。
一天,缪勒尔将王耀南找到办公室,兴致勃勃地问道:“伊万诺夫,你说中国的头一站,我到哪里好?”
“当然是北平,”王耀南说,“那是中国几个朝代的首都,古迹很多,有着浓厚的文化积淀。另外,它靠近满洲,对日侦察也很方便。”
“好,我接受你的建议。”缪勒尔又问,“我以什么身份去中国好呢?”
“你最好以商人的身份去中国,”王耀南建议,“使用中立国的护照,并且带上夫人和儿子。”
“这个主意好,因为我的中国之行更像一次度假。”缪勒尔得意地说道。
缪勒尔去中国的事,引起苏军情报部的高度重视。为此,杜曼宁将军专门找王耀南谈话。杜曼宁严肃地说:“缪勒尔将军亲自赴中国指挥对日情报工作,责任重大。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来保卫将军的安全。除了你跟随将军以外,还要选派一名同志协助你工作。”
“那么,就选派我们第四期同学陈冰岩吧,”王辉南说,“相信他已到了北平。”
“噢,你是说玛雅利,”杜曼宁点头,“他是个可靠的年轻人,我表示同意。”
之后,杜曼宁又找缪勒尔谈话。
“老朋友,你的安全我不能不管,”杜曼宁说,“除了伊万诺夫陪同外,在上海和满洲之间必须设一名联络员,以便减少你的不必要行程。”
缪勒尔笑了起来,“你以为我老了么?我会证明给你看的。”停了停他又说,“不过,我还是采纳你的建议,我准备让第五期学员马克西姆担任我的联络员,怎么样?”
“这都是你的学生,我不反对。”杜曼宁说道。
第4节 陈冰岩:矢志不渝求真理
1935年6月,北平。
清晨,北平上空雾气腾腾。太阳从房顶升起,好似一颗燃烧的火球。透过厚厚的一层玫瑰色的薄雾,太阳看上去就如同升起的月亮一样。
陈冰岩站在公寓的阳台上注视着雾中的太阳。这已是他来北平的第35天了,上级仍没有和他联络,难熬的一天开始了。
陈冰岩按着上级的指示越过国境,到扎赉诺尔上了火车,返回故乡阿城,在家只停留了几天,便立即奔向北平。到了北平之后,他在西城“宏达补习学院”学习,并在附近的二龙德山公寓住下,等候上级的指示。
陈冰岩像往常一样来到了学校。其实,他根本没心思听课,所谓的补习学院不过是骗学生的几个钱罢了。在这里纯属给自己找个掩护职业,学生嘛,警察一般是不放在眼里的。
国文老师讲些什么,他根本没有听进去。此刻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迅速找到情报组织。
7月15日上午,陈冰岩刚起床,便瞥见门口有一封邮差塞进来的信。他感到奇怪,北平举目无亲,朋友又少,谁会给他来信呢?
陈冰岩将信拾起拆开,阅读过后,心中不禁一阵狂跳:接上头了,终于接上头了。组织让他马上去青岛海滨浴场会见联络员。
陈冰岩急忙收拾了一下,拿起一个小包飞一样地从楼上冲下来。
在楼下,正遇到学院一同补习的同学,他见陈冰岩往学院相反的方向跑,便喊道:“今天考试,你不去了?”
陈冰岩头也不回地说:“让考试见鬼去吧!”
到了青岛海滨浴场,陈冰岩按着信中约定坐在太阳伞下,手中拿着一份《大公报》。此刻,他心中盘算着,会是谁来见我呢?这个人我认不认识?总不会是缪勒尔校长来见我吧。不,绝对不会的。他是苏联将军,情报专家,怎么会到这么危险的地方呢!正当他胡思乱想之际,有人轻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陈冰岩立刻转过身来,竟一下愣在那里。此人竟是王耀南。
王耀南坐到他的身边,笑道:“你这家伙,让我找得好苦哇。”
陈冰岩高兴地说:“我也在找你们呀!”
王耀南看了看他。“自从你离开莫斯科之后,我不久也回到了中国。5月份我曾带妻子到北平找你,在《北平日报》上还刊登了找你的寻人启事。左等右等不见你踪影,我只好回青岛。”
“那你是怎么找到我的,”陈冰岩急于想解开谜底,“是通过我们的组织吗?”
“对,是通过组织。”王耀南附和道。
陈冰岩见王耀南不愿详细说,便岔开话题,“你说的那份《北平日报》,我根本没有订阅,所以没看到启事。嗨,白白浪费这么多时间。”
王耀南看了看表,“等会我带你见位朋友,你千万不要吃惊。”
“朋友?”陈冰岩看到王耀南神秘的样子,一时竟不知道会在这里见到谁。
两人换上泳裤,在海边游泳。
这时,一个身材魁梧的欧洲人跃入水中,奋力搏击,陈冰岩见到此人,不由大吃一惊。
陈冰岩回头对王耀南说:“这不是缪勒尔校长嘛,他怎么会……”
“嘘,”王耀南示意他噤声,“缪勒尔负有重要使命来中国,在公开的场合你见到他不要谈话,要装做不认识一样。”
这时,缪勒尔夫人也跳进海水中游泳,她和缪勒尔都发现了陈冰岩。他们笑了笑,点了点头。这时,调皮的鲁迪游到他们附近,冲他们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