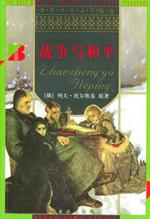丛林战争-第2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是出了偏差?奇怪!
这个念头的出现非同小可,万一方向错了,怎么办?那就只好在这万恶的丛林中宿营了,一阵恐惧攫住了我的心。但我不能向士兵们说出,我又掏出指南针检查开进的方向,可是找不到现在立足的坐标。丛林覆盖着苍穹,我无法观察到驼峰山在哪里。
砍伐越来越有经验,只是开通一条单人行道不再乱砍乱劈,有时,我们可以从空隙中穿越或是爬行,尽量少动刀斧。可是,每前进一步,我就多了一份疑虑,我有走了错路的预感。
罗伯特在昏迷中呻吟,嘴里不断地呼唤着一个女人的名字,我想不是他的母亲就是他的未婚妻。
他的全身已经出现了紫斑,脖颈僵直。我摸了摸他的胳臂,像火炭似地烫手,担架不能在丛林里行走,只好由士兵们轮流背负。90公斤的体重和滚烫的体温,使所有士兵望而生畏。瘦弱的士兵根本背不动他。……
我非常奇怪,富有丛林作战经验的克里斯却没有提出疑问,也不关心病员,一个劲地督促士兵向前开路,直到前面出现了一块排球场大小的乱石滩才停了下来。
克里斯少尉把我拉到一边低声说:
“队长!我敢说我们的方向走错了!”
“我也正在猜疑,可是,咱们是按着指南针的方位走的!”
“这里不是平原,我们为了找好砍伐的路线,已经拐过几次弯了。”
“你的意思是就在这乱石堆上宿营?”
“是的。如果沿着这条错路走下去,等到天黑可就麻烦了。”
“清水澡洗不成了!”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摆脱困境,……我看罗伯特也活不过今天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把他埋到这石滩上,明天就能轻装前进,不然,他会把我们拖死,幸好我们还没有出现脱水现象,再有几个躺倒的,我们就寸步难行了!……”
“他妈的!”我的心头漾起一种愤慨,“到这种鬼地方来作战,简直是发疯!”
克里斯含蓄地笑笑,那意思是说:中尉先生,你总算尝到一些丛林战争的味道了。
(二)夜宿乱石堆
——安德林《战地手记》之十一
我宣布在乱石堆上宿营。尽管大家洗不成清水澡,总算舒了一口气。天无绝人之路,这是在绿色海洋里上帝赐给我们的诺亚方舟。
尽管岩石在夕阳斜照下炽烈滚烫,士兵们宁愿脱光军衣赤身露体在阳光下暴晒,一天一夜的雨林雾海,我们连肠胃骨髓都被潮湿之气沤烂了。我们像日光浴似地躺在灰色的岩石上,霉气从全身毛孔里散发出来。
卫生员发给每个人一瓶治疗烂裆烂脚的药水。由于奇痒难耐,许多人已经把皮肤抓烂,抹上药水,被火烫了似地哇哇叫喊,……痛快地呻吟。
这里没有讨厌的蚊蚋,似乎也没有蚂煌。也许它们也受不了炽烈太阳无情的蒸烤,只有无害的蚱蜢从石缝里蹦出,欢快地跳到深草丛里。
克里斯没有命令机枪射手向四周丛林里盲射,似乎也没有让士兵们作防备游击队袭击的准备。我让克里斯作出解释。这种不耻下问的态度反而使他抱有感激之情,因为我尊重了他的经验和人格。
他说:“在原来宿营地,直升机从侦察到运送,已在那里作过多次盘旋,越共在密林里的瞭望哨自然会发现我们的行踪。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他们的游击队可以说无所不在,夜间自然会袭击我们,白天为了侦察我们的情况,自然会到达林间空地附近。我们的盲射有时歪打正着。……现在我们露营乱石堆,游击队并不知道我们的行踪。……也就匆须盲射。甚至官射还会自我暴露目标,把游击队引来。……”
我觉得他说得有理,并作了一点发挥,我说:
“我们走错路也许并不是坏事,这正好出乎越共游击队的意料,如果我们按正确路线直奔勺子湖,很有可能碰上他们的埋伏!……”
我们两个第一次这样和谐地谈话,由于我对丛林的初步认识,心理上自然有所沟通。……
太阳已经向丛林上方沉落。乱石堆上竟然拂过一丝凉凉的晚风。士兵们吃过晚餐之后,慵懒地躺在光滑的岩石上。只有卫生员史特里在照看着罗伯特。我在暗自盘算,如果明天找到勺子湖,直升机很容易找到我们。那里没有停机场,可以请他们垂下一个大网袋,把他吊上去。
这使我想到在异国土地上作战的困境,如果我们带着几个伤病员去侦察驼峰山,是无法完成任务的,必须把他们丢弃,这样,就会影响士气。谁不想到自己受伤生病后的处境呢?越共就好得多,他们的伤员病员可以随地安插,放在老百姓家里。……
昏迷中的罗伯特突然醒了,嘴里不断地呼叫,可是谁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也许是要水。卫生员用水壶灌他,他的牙关却咬得铁紧,他的紫斑肿块开始糜烂,流出乌黑的血水,他圆瞪着双眼,却不认识我们,他就像在烘箱上烧烤,眼里流露出恐惧的神情,仿佛看到什么魔怪向他袭击,他全身像在酷刑台上簌簌颤动,他的躯体陡然躬起来,随又瘫软下去,像一条活鱼在滚油锅里蹦跳打挺。……
“可怕!真是太可怕了!”军士长杰克逊似乎想按住他的躯体,却最终不敢伸出手去。
“如果他是清醒的,”克里斯恶狠狠地说:“就给他一枪,这是最仁慈的办法。……”
“也不知是什么毒虫咬了他,……”卫生员史特里低哑地嘟囔着。“完全没有救了,就是在基地医院他也活不了啦,可怜的罗伯特,……你就快些走吧,别受罪啦!”
罗伯特果然开始了强直性的痉挛,全身猛烈地颤震,像风中枯叶抖个不停,嘴角上泛起血沫,他的眼睛忽然瞪得奇大,最后奋然一挺坐了起来,伸出双手像迎接什么,高叫了一声“帕蒂!”就侧着身子猝然倒下,气绝身亡了!
这是多么可怕的死,那“帕蒂”是谁?是他的未婚妻吗?……
太阳已经落下树梢,天空却出奇地晴朗。
我亲自给罗伯特寻找墓地,沿着乱石堆向东走去,我想,让罗伯特死后也是头向他的家乡。这块乱石堆事实上是一块林间台地,比周围的凹地高出大约三米,我不知从地质学的角度如何解释它形成的原因。我在选准了岩石缝隙的走向后,命令士兵把罗伯特抬到石缝中安葬。把石缝上下全都塞满碎石,免得雨水把尸体冲出或是野兽把尸体拖走。……但我知道,不久就会腐烂,而后只剩下一副白骨。
我们28个人,全都摘下钢盔默立“墓”前,向他告别。为了不暴露目标,没有鸣枪致哀。
黑人机枪射手诺尔曼趴在他的坟头痛哭。克里斯踢了他一脚,厉声训斥:
“滚起来!你是士兵,不是他妈的老太婆!”
罗伯特,这个加利福尼亚的煤矿工人,连同他的歌声就这样留在异国的土地上了,但愿他魂归故土。
罗伯特的死,使全队得到了解脱,却也给人们的心灵罩上了阴影,谁不考虑自己的未来呢?死者已长留。生者何处去?谁知道明天乃至下一个小时,会出现什么意外呢?
这是一个星光灿烂的夜晚,士兵们睡在气垫床上,享受着初夜的清凉。黑暗裹着潮湿的夜气,从四周丛林里向乱石堆合拢过来,士兵们都在身上搭上雨衣。在一天的极度紧张疲倦之后,有些士兵已经沉睡,各自进入了梦乡。如果他们的梦境能够显现,那将是多么离奇古怪。
克里斯毕竟精力旺盛,我看到他悄悄起来提枪在手,谛听着远方的动静,我对他产生了几分敬意。
这时,夜气更加晦暗凝重,晶莹的星星在浩瀚无际的灰蒙蒙的天宇闪烁,像故乡亲人的含泪的眼睛,丛林里的鸱囗发出声声嚎叫,夜鸟扇动着柔软的翅膀掠过乱石堆的上方。我的思绪飞得很远,心头漾起阵阵凄楚:
我的父母和妹妹在做什么呢?他们对越南战争怎么看呢?当他们知道我这次丛林之行所经历的磨难,他们作何感想呢?
我的父亲是费城有名的律师,他以高尚的品行、独到的智慧和出色的服务赢得了盛誉,这种令人崇敬的尊严维持了30年之久。他深谙激流勇退之道,在一身严正无暇的情况下提前退休,在费城市郊特拉华河畔的小型农场里颐寿天年,那里有一所乡村别墅。
他的生活可以称得上潇洒疏放,一个农场、一方园林、一间宽大的图书室,便是他的快活的天堂。
退役后的卡尔逊上校,是我家的常客。他们两人可以在别墅的弹子房里进行无休止的战斗,或是在国际相棋盘上拼搏。……
在我读小学的时候,父亲就时常讲起我们的祖先。费城——这是美国的故都,那是伟大的拓荒者威廉·潘思于1682年创建的,他就是我的祖先。1790年到1800年是美利坚合众国的首都,这里有许多美国的第一:这里举行了第一届国会,第一个全国最高法院也在这里诞生,这里有美国的第一所银行、第一所医院、第一所医学院、第一所艺术学院。……还有富兰克林创建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宾夕法尼亚艺术学院。故乡是我的骄傲,我对它一往情深。
自从我考入西点军校之后,每当我回家度假时,卡尔逊总是向我介绍历来的战争,在二战时期他在中国多年。对中国的孙子兵法有所研究,他推崇备至的是中国的游击战争。
我可能受父亲职业的影响,对于逻辑推理有着特别的兴趣,再加上卡尔逊先生的视察见闻,所以在军校里我的军事理论总是名列前茅。可是我的理论在丛林战争的实践中受到了严酷的考验。我将对过去的许多观念来一次再认识。
这时,我听到克里斯少尉和杰克逊军士长低声说话,而后克里斯去睡了,杰克逊却坐在背囊上,抱着双臂面对着黑压压的森林。林间野兽在凄厉地吼叫,远方有隆隆的爆炸声,那是我们的轰炸机实行夜袭。
我想起了我的新婚妻子康妮。她是一头金发的美丽女郎。我想起中学时代我们的野营生活,我们班级男女学生走进了故乡的阿巴拉契亚山脉。茂密的森林、起伏的峰峦,还有白色的围墙、黄色的谷仓、绿色的房顶、红色的马厩、蓝色的栅栏、黑油油的土地、青青的草坪,还有那些美丽的田园牧歌式的乡村。
那时,我们是无忧无虑欢乐的一群,我们围着篝火跳舞唱歌:
我们来自阿拉巴马,带上心爱的五弦琴,
要赶到路易斯安邦,为了寻找我的爱人;
晚上起程大雨下不停,但天气还算干燥,
烈日当空我心却冰冷,啊,苏珊娜别哭泣。
昨晚上更深人静,我沉睡入梦境;
在梦中我见到苏珊娜,漫步下山来相迎;。
她嘴里吃着荞麦饼,两眼泪晶莹,
我离开故乡来找你,啊,苏珊娜别哭泣。
我马上要去新奥尔良,到四处去寻访,
当找到我的苏珊娜,我愿跪在她身旁;
倘若我找不到她,就只有把命丧,
黄土长埋他乡也甘愿,啊,苏珊娜别哭泣。……
现在,我躺在乱石堆上,回想起这首歌,竟然泪流满面,我十分骇异,这绝不是一个铁血军人的感情,我不知道我的泪水为谁而流。也许是为了罗伯特吧?如果他不死去,今夜他将会为我们唱很多歌。他是矿工,也是歌手,仅仅是那一首《克莱门泰因》就把我的心揪住了。辽远、深情、忧伤,感情冷漠的人是无法唱得那样动人的!也许他把深藏在心中的对未婚妻帕蒂的爱情借这首歌渲泄出来,甚至他已经预想到他们不能相见了。果然,他留在这乱石堆中,永远也见不到他的帕蒂了。
我擦干了泪眼,暗蓝色的天幕上星光闪烁,在这样的能使心灵净化的环境里,我对人生产生了一种迷惘感,我们不远万里到异国丛林中来献身,意义何在?
我又回到了中学时代,又回到了阿巴拉契亚山,又想到我和康妮在山林中漫游,我们在酣畅美妙的生活中迷失了自己,我记得那时,月光时隐时现,山林忽明忽暗,空气中弥散着野蔷薇的芬芳,我们不怕迷路,也不觉劳累,只要我们两人在一起,就不怕走到天涯海角。
为了表示勇气,我们两人曾装作迷路离开了群体,无畏地走进了万木幽深的峡谷,那里怪石嶙峋,山洪咆哮,我们穿过峡谷,走上了一丘石多草稀的山包,我们手挽手看着浑圆的落日在群峰之巅像火焰似地放射着红光。我们在美妙的爱情中度过了荒山之夜。
那时,我们都是“人道主义者”,对于婚恋还固守着一种旧的道德观,我和康妮都是清教徒,在西点军校毕业后,我们在费城的乔治基督大教堂里举行婚礼。度过蜜月之后,我来越南,而她便到波士顿《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编辑部去上班。
康妮和我一样,都是主战派。因为我们把共产主义看成比洪水猛兽还要厉害百倍的人间恶魔。我们不能看着东南亚像多米诺骨牌那样倒向共产主义,我们为自由世界而战是替天行道,上帝在上方注视着我们,我们是拯救人类脱出苦难的摩西!
起风了,四周的林木受了惊吓似地沙沙作响。涛声澎湃,像是一曲挽歌,夜风清凉,我打着寒噤坐起来吸烟。幽蓝色的星座已经倾斜,我又拉起雨衣倒头睡了,只觉得石缝里的茅草在夜风中簌簌有声地颤动。在无尽的遐想中,我渐渐进入梦境:
我先是看到瘸着腿的麦克罗在我们家的田庄上……跟他在一起的好像是康妮,我看不确切。我怀着一种妒意跟在他们身后。他们头也不回走向一条山谷,这山谷是我中学时代野营时去过的,其中有一条弯曲的小径,越走越陡峭,……而后他们隐进了一片丛林,……我失去了前进的目标,脚下全是双头的蟒蛇,我不知何去何从,……我隐隐听到“中尉,中尉”的叫声。……
惊醒过来,我看到克里斯少尉站在我面前。
(三)死亡之谷
——安德森《战地手记》之十二
我发现,经过一夜休整后的士兵反而显得萎靡不振睡眼惺忪疲倦不堪了,汗湿的污秽的军装在焐干之后留下了白花花的盐霜,有人腿脚肿了,走路一瘸一拐昏昏沉沉,好像昨天几个小时的砍伐把他们的精力榨干了似的!我要他们重新振作起来,但首先必须确定今天的行动目标;
克里斯的意见是退回原地,因为我们对来路已作了砍伐,返回比较容易,在原地等候直升飞机的支援,由直升机直接把我们投到勺子湖畔。……没有停机坪,我们就沿绳梯下去。对勺子湖完成四周的丛林侦察搜索,如无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