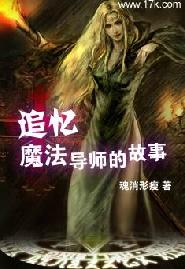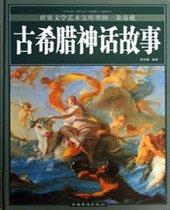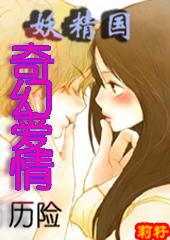不是故事的故事-第2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廖参谋长得很帅,外形像样板戏里的洪常青,肚皮里有点墨水,文绉绉的;常班长却一脸土气。
他们的任务是抓大联合和搞复课。由于亨元在两派联合中姿态较高,出身又比何西和皮旦等党员好,所以选中了他作为唯一的教师参加大联合临时领导小组。
其成员还有:胡虎和"泥腿子"、"红苗子"各一名小将。武斗工事已拆除,教师们纷纷从三层楼搬回校内,亨元搬进了原来的党支部兼校长室。
亨元在外面搭一张铺睡觉,里面则与其他"领导人员"一起办公。这样,与计萍的约会方便得多,因为晚上别人都走掉了,这个地方可以由他一个人使用。
时值一九六八年,"抗美援越"高潮期,"同志加兄弟"的越南人紧缺血浆,中国人依靠庞大的人口优势发动了义务献血,要求共产党员带头。
教工造反总部头头借口身体素质太差,没有报名。亨元与他的那一派人私底下讥笑议论一番之后,“挺身而出”,到枫林医院进行了血液检查。
报告出来,医生说:这只血特别好,各项指标完全合格。大约一个星期内就要抽血了,定量200CC。
亨元从娘胎落地,活了近三十年,很少光顾医院,除了伤风咳嗽到门诊部配点药吃,基本上没有打过针。说基本不说根本,缘由大学二年级补蛀牙到市公费医院去,在舌根上打过一剂麻醉针。
现在,听说要用一根象自来水笔吸水管那般粗细的针头插进血管,从血管里抽出一瓶桔子汁那么多的血,送给素不相识的越南人。心里紧张万分,不知道自己能否熬过这一关而不在众人面前出洋相。
那时候,"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军宣队要已经联合起来的两派教师各抽出2、3个人下乡办"伸腿班"。
教工总部方面派出杜行和另几位教师人去杨红大队;"七教员"则推出亨元、马龙等人去新立大队。陈林因与马龙谈得拢,也加盟去新立大队。
一个政治教员、一个数学教员、一个语文教员,三个人构成了这支伸腿班的教学队伍。借新立小学一间教室,生源是当地小学毕业没有上初中的农民子弟。
家访动员后,来了二、三十人。作为唯一的党员,亨元自然成了这个伸腿班的负责人。同时兼教政治课,还发挥特长,给学生上音乐课。
不会弹风琴,(也没有风琴)笛子或胡琴伴奏,反正学生和老师要求都不高,凑合着能对付。
路比较远,从枫林出发要走三刻钟,中午是不能回家吃饭了,就在小学搭伙,他们有一个厨子,多做三个人的饭并不麻烦。
在亨元等人下乡办伸腿班的时候,学校里重新建立了三结合临时领导班子。老干部胡虎仍然被“结合”进去,而教师由复员军人翁玉取代了亨元。
不过这个临时班子寿命不长,两派对它都有意见,胡虎本是个傀儡,翁玉想两派都不得罪,结果左右不讨好,有一次居然在亨元等人面前急得哭出来。
此人也算是行伍出身,却毫无军人的豪迈气概。其妻比他小十几岁,倒是个豆腐西施,还是他来枫林中学教书前,在新行农中当负责人时的一个学生。
他看中了这位当时只有十六、七岁的农家姑娘。在穷追不舍之下发生了关系而且怀了孕,这下事情闹大了,如果无限上纲,非但要吃官司,甚至可能吃"花生米"。
只好"私了",豆腐西施变成了翁玉夫人。新行农中不好耽下去了,于是调来了枫中。到文革中期,他已有了三个男孩。
翁玉夫人文化不高,只能在村校代代课。主要经济来源靠丈夫六十多元工资,维持一家六口够拮据了。他把经济大权独揽一身,不许夫人乱花一分钱,但对她的衣着打扮却很注意。
他利用数学上的几何图形原理,无师自通学会了裁剪和缝纫,从而给老婆穿上一件件新衣,他自己则不修边幅,因此夫妻俩站在一起,不很相称。
国庆节一过,浦江县派出了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浩浩荡荡进驻各上层建筑单位。军宣队撤走了,临时三结合组织也偃旗息鼓。
现在来枫林中学掌权的是江涛、封锐等来自叶松和海塘公社的贫宣队队员。
他们根据"红太阳"作出的清理阶级队伍的最新指示,提出要深挖教师队伍中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所以把两个伸腿班的教师召回学校,开办了一次次的清队学习班。
"三家村"和"四家店"的走资派和牛鬼蛇神们重新被看管起来;其他教师被打发到奋斗大队举办"脱离工作、脱离教学、脱离家庭"的"三脱离"学习班。
亨元打了个被头包背在身上,依依不舍地与仍旧留在枫中教工宿舍那间小屋的计萍告别。数十名男女教师分住在奋斗小学的两间教室里。
课桌椅并成床,白天被头卷一卷又变成小组讨论会场。吃着简陋的一日三餐,过着与世隔绝的封闭式生活。而主宰着他们命运的贫宣队员们,正在根据大字报和小字报进行分析、排队和内查外调。
阳历年刚过,在上海远郊小镇的枫林中学内,贫宣队根据最高指示把十几名教师打进了劳改队,这已经远远超出老人家关于"阶级敌人仅仅是一小撮","不超过5%"的估计。
但是,内查外调仍然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贫宣队毫无收兵之意。江涛有时到奋斗大队来给封闭着的教师们"透透风",说:
“学校里有一颗埋藏得很深的"定时炸弹"还没有挖出来。”“不揭不知道,一揭吓一跳,你们等着瞧吧,阶级敌人也许就睡在你们身边!”
自命不凡的江涛抛下这最后的两句话后又回到了学校。果然不久,一个爆炸性的消息传到了奋斗大队:亦华是现行特务,已经隔离审查。
这个消息把大家惊呆了,尤其是"七教员",几乎是致命的一击。余下的六教员以及同情七教员的人对亦华的特疑持怀疑态度。
因为她虽然出身旧军官家庭,但父亲是北阀时代的军官,与国民党关系不大,何况,中学时家乡湖南就解放了,她也参了军,分在文工团。
一九五六年以调干生身份考入某地师范学院中文系,1960年毕业,本可留在城市里工作,却响应党的上山下乡号召,主动与他人对调到枫林这个偏辟小镇来教书。
几年来担任高中二班主任、语文教师,工作卓有成绩。此人待人和蔼,大家推选她为工会副主席(主席是陶崇)文革前的党支部还列她为建党对象。
她与师范同学辛河已成对象。辛毕业后分配在七宝镇上的上海农校任教师,几乎每个周末,他都要蹬着那辆从旧货店以七十余元人民币买来的自行车到枫林来相会。
他们住教师宿舍区另一间单独的小屋,也不足六平方米。如此清白人生,怎么能同狰狞可怖的现行特务联系起来呢?但是,江涛以其三寸不烂之舌向教师们解释:
"越是不像特务的人越有可能当特务。你们不能光看表面,亦华的老实都是装出来的。你们可知道,她每天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在干什么?在拍电报!同国民党特务机构联络。"
据贫宣队介绍,他们手里有两张王牌,足以证明她是个现行特务。那就是发现她藏有一本密电码和一架发报机。
前者已为贫宣队搜获,放在她的档案里;后者已发现隐藏机器的地洞,可惜机子已被她转移。审问之下,得知转移到她爱人七宝镇住所。
迅速派人将罪证取回,是一架极普通的四灯管收音机。亨元等人过去到她房里闲坐时也曾见过,岂料它里面还有特殊装置。现在摆在贫宣队办公室,等待专家鉴定。
亦华当时三十多岁戴一付近视眼镜,正怀着几个月身孕。在小将的严密监管下,苦度春秋一年有余。其次子在禁闭室里产下,患先天性心脏病。
她望眼欲穿等待结论,却沓无音讯。得知内情的人告诉亨元:实际上,所谓收发报机早已否定。这架四灯管收音机根本安不上特殊装置。
所谓地洞,经核实,在亦华搬进去前早已存在是冬天放山芋用的。只是密电码从何来,还是个谜,亦华自己也说不清楚,所以贫宣队只好把她挂起来。
贫宣队要撤走了,把案子移交给大多数人来自上海钢铁厂的工宣队。工宣队把已为贫宣队启用,正在调查他人历史的亨元召来,要他掌管各"牛鬼蛇神"的档案材料。
亨元得以窥见亦华被打成现行特务的那部分材料。抽出卷宗,一本三十二开的练习簿引起了他的注意。练习薄左上角用大头针别着张小纸条,上书"密电码"三字。
翻开练习簿一看,不禁一怔:天哪!这不都是我自己的手迹吗?还是在1967年两派学生大闹武斗的时候,亨元等七人做了逍遥派,彼此的宿舍经常走来走去。
闲暇无事,他取一本空白练习簿,每页都画上无数小方格,每四格为一组,表示一句成语。为启示自己的记忆,以拼音字母填入小格。不知哪一天遗留在亦华的小间里,竟成为她未能解脱特务嫌疑的罪证。
于是,亨元迅速向工宣队汇报。开始,他们怀疑他编造故事为亦华翻案。后来听他说得有板有眼,就要他写一份证明材料。亨元将此事的来龙去脉祥祥细细写在另一本练习簿上交给工宣队。
不久,亦华被撤销了隔离审查,但没有平反。工宣队头头解释:本来就没有下结论,谈不上平反。亦华夫妇向有关方面提出了恢复名誉、赔偿损失的要求,得到的答复与工宣队一样。
隔离室产下的婴儿患先天性心脏病,医院里动了手术,一切费用都要自己负担。所幸,他们的两个儿子长大了都很有出息。
大儿子考入交通大学电脑系,毕业留校任教,后来去了美国,在某研究所开发新产品。隔离审查产下的二儿子,智商比哥哥还要高几分,读高中时崭露头角。
毕业前夕为复旦大学新闻系吸收免试入学,毕业后担任某报外文版记者,过了几年也到了美国,住在他哥哥的小镇上,已获得硕士学位。
亦华夫妻俩在文革后一起调往市区工作,辛河当过区教育局长,亦华当过师范学校校长,这在文革中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他俩退休后双双远渡重洋去美国与两个儿子相会,享受天伦之乐。这也许是造物主赐与人类的一种苦尽甘来的补偿吧。
且说亨元和大分教师在团结大队参加三脱离学习班。天气越来越寒冷了,贫宣队毫无将他们撤回学校的意思。亨元过着枯燥乏味的军事化生活,心里牵挂着独守空房的计萍。
突然,一个意想不到的“机遇”降临到他身上。江涛来到团结大队,把他叫去:"我们内查外调缺人手,经贫宣队集体研究,决定把你从学习班抽出来,参加调查组。"
亨元和海塘公社来的贫宣队员封锐搭档。封锐是二十余岁的农村青年,中学文化,善于思索。在一起出差外调过程中有时也透露些内幕新闻给同伴听。
他的政治立场左中有右,比较尊重客观事实不盲目迷信、崇拜权威。第一次,他们一起出差无锡,调查江言的出身和政治历史问题。
江言出身破落地主家庭,因为解放前三年还在读书没有划地主成份,而他的妻子,解放前嫁到他家里,四清中却划了地主成份。
江妻也在枫林镇小学教书。计萍曾告诉亨元,小学的造反派把江妻整得很厉害。有时候无缘无故把正在冲厕所的"地主婆"叫去,要她背诵毛主席语录,略有差错,一个巴掌打过去,把她脸上的眼镜打落。
这次到无锡,是因为江言交代了他的传奇式经历而去核实。江在读高中的时候,其表兄在江南组织忠义救国军对抗日寇,偶而也和新四军闹磨擦。
这支部队开拔到江言家乡,表兄吸收他参军,授予少校军衔。从军不到一星期就遇到了新四军打了一仗,忠义救国军溃不成军。
江言在慌乱中急中生智,抢了一个难民的小孩,换上老百姓衣服才得以逃生。外调没有结果,但亨元还是在本校清队成果材料中像写小说一样描述了江言的这一段历史。多才多艺的物理教师顾白还配之以插图,用大字报形式张贴出来,吸引了不少学生观看。
第三十四回
外调衣裤被盗摇头夸说弟好北方女子亦俏南方贫农身娇
亨元在无锡时买了两篓子油面筋,准备送给上海的丈人家。火车到上海与封锐分了手,说要在上海过一夜,次日再回枫林。他不知道丈人家怎么去法,只听说离新申中学不远。
想起新申中学的晚霞,还有神经病已治好的傅新,不妨先到他们那里,有个落脚点后再去找丈人家。寻到那里,已近晚饭时间,所幸傅新是单身汉,有间鸽子笼式的宿舍在校内。
东大两位同窗相别八、九年后重逢。傅新的声音仍然是发育不全的孩儿嗓和娘娘腔,他喋喋不休地说着自己这几年的情况,自我感觉似乎比晚霞对他的评价好得多。
他热情邀请亨元与他合铺过夜,并张罗着为亨元准备晚餐。房间里挂着刚洗过的衬衫、汗衫、和短裤,狭小的空间弥漫着湿气。
亨元托他把两笼油面筋设法送到东余杭路计宅。傅新表示一定完成任务。次日上午他领着亨元来到教师办公室,遇到几位过去一起在县中搞社教运动的教师,可惜没有见到晚霞。
过了两周,计萍告诉他,她家那天接待了一位尖喉咙的青年男子,提着两笼油面筋,说是计萍从无锡买来孝敬父母的。
计芳不在家,计母以为这就是女儿在枫林找的对象,因为也戴眼镜片子。一问说是新申中学教书的,倒有点搞得稀里糊涂了。这不明不白的油面筋不敢吃,挂在屋顶下,最后发了霉。不久,贫宣队又决定调查一位老教师的政历问题。该人的老家在河北省南皮县。于是,又指派封锐和亨元前往北方调查。
这对别人来说也许是件好差使,南皮就在北京附近,可以借此朝圣伟大领袖脚下的土地,亨元却十分勉强,因为正准备着与计萍成婚。
虽然文革期间一切从简,但是房间和家具都是免不了的。住房问题解决得很顺利,计萍和房管所负责人曾一道在枫林街头画过宣传画,根据优先考虑结婚户用房的政策,计萍提出的要求得到了满足。
新大楼302室即亨元和他的同事以前住过的那间公房,配给了这对新婚户。所需家具按当地起码标准,要求二十八条腿:即一桌四椅、大床和五斗橱各一。
哈哈已和平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