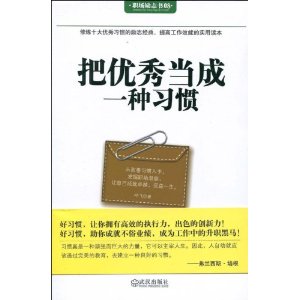成一:白银谷-第1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康笏南应酬回来,兴致很好,也没有再问到樊掌柜。
孙北溟想了想,康笏南坐镇,自己亲自查问这样一个小老帮,阵势太吓人了。他就给开封庄口的领庄老帮写了一封信,命他抽空来怀庆府庄口,细查一下账目,问清这里生意失常的原因,报到汉口。天成元在河南,只在开封、周口和怀庆府三地设了分庄。开封是大码头,平时也由开封庄口关照另外两个分庄。由开封的老帮来查这件事,总号处理起来,就有了回旋的余地。
所以,他们在此只停留了一天,就继续南行了。
行前,改雇了适宜平原远行的大轮标车,车轿里宽敞了许多,舒适了许多。所以,经武陟、荣泽,过河到达郑州,虽然气候更炎热,孙北溟倒觉着渐渐适应了。他看老亭的样子,似乎也活过来了。
但到新郑,康笏南中了暑。
3
新郑是小地方,康家在这里没有任何字号。他们虽住在当地最好的客栈里,依然难隔燠热。就是为康笏南做碗可口的汤水也不易。孙北溟感到,真是有些进退两难。
镖局的武师,寻到江湖的熟人,请来当地一位名医。给康笏南把脉诊视过,开了一服药方,说服两剂,就无事了。康笏南拿过药方看了看,说这开的是什么方子,坚决不用。他只服用行前带来的祛暑丹散,说那是太谷广升远药铺特意给配制熬炼的,服它就成。另外,就是叫捣烂生姜、大蒜,用热汤送服,服得大汗淋漓。
在新郑歇了两天,康笏南就叫启程,继续南行。可老太爷并没有见轻,谁敢走?
包世静武师提出:“到郑州请个好些的大夫?”
康笏南说:“不用。郑州能有什么好大夫!”
老亭说:“那就去开封请!”
康笏南摇手说:“不用那样兴师动众,不要紧。新郑热不死我,要热死我,那得是汉口。我先教你们一个救人的办法,比医家的手段灵。我真要给热死,你们就照这办法救我。”
众人忙说,老太爷不是凡人,哪能热死!
康笏南说:“你们先记住我教给的法子,再说能不能热死我。那是我年轻时,跟了高脚马帮,从湖北羊楼洞回晋途中,亲身经见的。那回也是暑天,走到快出鄂省的半道上,有一老工友突然中暑,死了过去。众人都吓坏了,不知所措。领马帮的把势,却不慌张。他招呼着,将死过去的工友抬起,仰面放到热烫的土道上。又招呼给解开衣衫,露出肚腹来。跟着,就掬起土道上的热土,往那人的肚脐上堆。堆起一堆后,在中间掏了个小坑。你们猜,接下来做甚?”
众人都说猜不出。
“是叫一个年轻的工友,给坑里尿些热尿!热土热尿,浸炙脐孔,那位老工友竟慢慢活过来了。”
众人听了,唏嘘不已。
孙北溟说:“老东台,你说过,御热之法最顶事的,是心不乱。你给热倒,是不是心乱了?你老人家不是凡人,我们都热死,也热不着你。不用说热死人的故事了。你就静心养几天吧,不用着急走。”
“大掌柜,你说我心乱什么?”
“这一路,你就只想着西帮之衰,走到哪儿,说到哪儿。这么热的天,想得这样重,心里能不乱!”
康笏南挥挥手,朝其他人说:“你们都去吧,都去歇凉吧,我和大掌柜说会儿话。”
众人避去后,康笏南说:“我担忧是担忧,也没有想不开呀!”
“心里不乱就好。西帮大势,也非我们一家能撑起,何必太折磨自家!”
“我跟你说了,我能想得开。我不是心乱才热倒。毕竟老迈了。”
“年纪就放在那里呢,说不老,也是假话。可出来这十多天,你一直比我们都精神。以我看,西帮大势,不能不虑,也不必过虑。当今操天下金融者,大股有三。一是西洋夷人银行,一是各地钱庄,再者就是我们西帮票号。西洋银行,章法新异,算计精密,手段也灵活,开海禁以来,夺去我西帮不少利源。但它在国中设庄有限,生意大头,也只限于海外贸易。各地钱庄,多是小本,又没有几家外埠分庄,银钱的收存,只能囿于本地张罗。惟我西帮票号,坐拥厚资,又字号遍天下,国中各行省、各商埠、各码头之间,银款汇兑调动的生意,独我西帮能做。夷人银行往内地汇兑,须赖我西帮。钱庄在当地拆借急需,也得仰赖我票号。
所以当今依然是天下金融离不开我西帮!我们就是想衰败,天下人也不允许的。”
“大掌柜,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这是叫你宽心的话,也是实话。就说上海,当今已成大商埠,与内地交易频繁,百货出入浩大。每年进出银两有近亿巨额,可交镖局转运的现银却极少,其间全赖我西帮票号用异地彼此相杀法,为之周转调度。西帮若衰,上海也得大衰。”
“大掌柜,你这是叫我宽心,还是气我?天下离不开西帮,难倒西帮能离开天下?”
“洪杨乱时,西帮纷纷撤庄回晋,商界随之凋敝,朝廷不是也起急了,天天下诏书,催我们开市。那是谁离不开谁?”
“不用说洪杨之乱了。我们撤庄困守,也是坐吃山空!”
“坐吃,还是有山可吃。”
“大掌柜,你要这样糊涂,还跟我出来做甚!”
“我本来也不想出来的,今年是合账年,老号柜上正忙呢。”
“那你就返回吧,不用跟着气我了!”
“那我也得等你老人家病好了。”
“我没有病,你走吧。老亭——”
老亭应声进来,见老太爷一脸怒气,吃了一惊。
“老亭,你挑一名武师,一个伙计,伺候孙大掌柜回太谷!”
老亭听了,更摸不着头脑。看看孙北溟,一脸的不在乎。
“听见了没有?快伺候孙大掌柜回太谷!”
老亭赶紧拉了孙北溟出来了。一出来,就问:
“孙大掌柜,到底怎么了?”
孙北溟低声说:“我是故意气老太爷呢。”
老亭一脸惊慌:“他病成这样,你还气他?”
孙北溟笑笑说:“气气他,病就好了。”
“你这是什么话?”“你等着看吧。老太爷问起我,你就说我不肯走,要等他的病好了才走。就照这样说,记住了吧。”
老亭疑疑惑惑答应了。孙北溟走后,康笏南越想越气。孙北溟今天也说这种话!他难道也看我衰老了?他也以为我会一病不起?
躺倒在旅途的客舍里,康笏南心里是有些焦急。难道自己真的老迈了吗?难道这次冒暑出巡,真是一次儿戏似的举动?决心出巡时,康笏南是有一种不惜赴死的壮烈感。别人越劝阻,这种壮烈感越强。可是越感到壮烈,就越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信心。年纪毕竟太大了,真说不定走到哪儿,就撑不住了。所以,中暑一倒下,他心里就有了种压不下的恐慌。
现在给孙北溟这一气,康笏南就慢慢生出一种不服气来。他平时怎么巴结我,原来是早看我不中用了!非得叫他看看,我还死不了呢。
他问老亭:“孙大掌柜走了没有?”
老亭告诉他:“没有走,说是等老太爷病好了才走。”
“叫他走,我的病好不了了!”
他嘴上虽这样说,心里可更来气:他不走,是想等我死,我才不死呢。
这样气了两天,病倒见轻了。
听说康老太爷病见轻了,孙北溟就一脸笑意来见他。康笏南沉着脸说:“大掌柜,你怎么还不走,还想气我,是吧?”
孙北溟依然一脸浅笑:“我不气你,你能见轻呀?上年纪了,中点暑,我看也不打紧,怎么就不见好呀?就差这一股气。”
“原来你是故意气我?”
“老东台英雄一世,可我看你这次中暑病倒,怎么也像村里老汉一样,老在心里吓唬自己!
你说我说得对不对?”
“对个鬼!我哪里吓唬自己来?”
“我跟你几十年了,还能看不出来?我知道,我一气你,你就不吓唬自己了,英雄本色就又唤回来了。”
“大掌柜,你倒会贪功!不是人家广升远的药好,倒是你给我治好了病?你去哄鬼吧!”
“哈哈哈!”
4
离开新郑,到达许州后,就改道东行,绕扶沟,去周家口。周家口不是小码头,康家的票庄、茶庄,在周口都有分庄。
虽说越往前走,气候越炎热,但大家显然都适应了这种炎夏的长途之旅。没有谁再生病,也没有遭遇什么意外。康笏南就希望多赶路,但孙北溟不让,说稳些走吧,这么热的天,不用赶趁。
康笏南就向车老板和镖局武师建议,趁夜间有月光,又凉快,改为夜行昼歇,既能多赶路,也避开白天的炎热,如何?他们都说,早该这样了,顶着毒日头赶路,牲灵也吃不住。康笏南笑他们:就知道心疼牲灵,不知道心疼人。
于是,从许州出发后,就夜里赶路,白天住店睡觉。
白天太热,开始都睡不好觉。到了夜里,坐在车里,骑在马上,就大多打起瞌睡来。连车老板也常坐在车辕边,抱了鞭杆丢盹,任牲灵自家往前走。只有康笏南,被月色朦胧的夜景吸引了,精神甚好。
那日过了扶沟,转而南下,地势更平坦无垠。只是残月到夜半就没了,朦胧的田野落入黑暗中,什么也现不出,惟有寂静更甚。
寂历帘栊深夜明,
摇回清梦戌墙铃。
狂风送雨已何处?
淡月笼云犹未醒。
康笏南想不起这是谁的几句诗了,只是盼望着能有一场雨。难得有这样的夜行,如有一场雨,雨后云霁,淡月重出,那会是什么味道!这样热的天,也该下一场雨了。自从上路以来,似乎还没有下过一场像样的雨。中原这样夏旱,不是好兆吧。
没有雨,有一点灯光,几声狗叫也好。很长一段路程,真是想什么,没有什么。康笏南也觉有瞌睡了。他努力振作,不叫自己睡去,怕夜里睡过,白天更没有多少睡意。
就在这时,康笏南似乎在前方看到几点灯光。这依稀的灯光,一下给他提了神。这样人困马乏地走,怎么就快到前站练寺集了?
他喊了喊车倌:“车老板,你看看,是不是快到练寺集了?”
车倌哼哼了一声什么,康笏南根本就没有听清。他又喊了喊,车老板才跳下辕,跑到路边瞅了瞅,说:“不到呢,不到呢。”
康笏南就指指前方,说:“那灯光,是哪儿?”
“是什么村庄吧?”车倌打了个长长的哈欠,又跳上车辕:“老掌柜,连个盹也没有丢?真精神,真精神。”
康笏南还没有对答几句,倒见车倌又抱了鞭杆,丢起盹来。再看前方灯光,似乎比先前多了
几点,而且还在游动。他以为是自己看花了眼,定神仔细望去,可不是在游动!
那也是夜行的旅队吗?再一想,觉得不能大意。几位武师,没有一点动静,也在马上打盹吧?
康笏南喊醒车倌,叫他把跟在车后的伙计招呼过来。
伙计下马跑过来。康笏南吩咐把包师傅叫来。
包世静策马过来,问:“老太爷,有什么吩咐?”
“包师傅,你们又在丢盹吧?”“没有,没有。”
“还说没有呢。你看前方,那是什么?”
包世静朝前望了望,这才发现了灯光。
“快到前头的练寺集了?”
“还没睡醒吧?仔细看看,那灯火在动!”
包世静终于发现了灯火在游动,立刻警觉起来,忙说:“老太爷放心,我们就去看个究竟!”
康笏南从容说:“你们也先不用大惊小怪,兴许也是夜行的旅人。”
包世静策马过去,将镖局两位武师招呼来,先命马车都停下,又命四个拳手围了马车站定。
包世静问两位武师:“你们看前方动静,要紧不要紧?”
白师傅说:“多半是夜行的旅人。就是劫道的歹人,也没有什么要紧。没听江湖上说这一段地面有占道的歹人呀!”
“会不会是拳民?”
郭师傅说:“在新郑,我寻江湖上的朋友打听过,他们倒是说,太康一带也有八卦拳时兴。”
“太康离扶沟,没多远呀!”
郭师傅说:“太康在扶沟以东,我们不经过。我跟朋友打听扶沟这一路,他们说,还没传到这头。这头是官道,官府查得紧。”
包世静听了,说:“那我们也不能大意!”
白师傅说:“包师傅你就放心。我和郭师兄早有防备的,斗智斗勇,我们都有办法。”
郭师傅就说:“我先带两名拳手,往前面看看,你们就在此静候。”
说完,就叫了两个拳手,策马向前跑去。
这时,白武师已从行囊中取出四条黄绸头巾,交给包世静一条,天成元的三位伙计,也一人分给一条。他交待大家,先收藏起来,万一有什么不测时,再听他和郭师傅的安排。
包世静就着很淡的灯光,看了看,发现黄绸巾上画有“乾”卦符,就明白了要用它做什么。
“白师傅,怎么不早告我?”
“这是以防万一的事,早说了,怕两位老掌柜惊慌。”
“他们都是成了精的人,什么阵势没有见过。”正说着,孙北溟大掌柜过来了:“师傅们,怎么停车不走了,出了什么事?”
包世静忙说:“什么事也没有。这一路,大家都丢盹瞌睡的,怕走错了道,郭师傅他们跑前头打听去了。”
孙大掌柜打了个哈欠,问:“天快亮了吧?”
“早呢。”
“前站到哪儿打茶尖?”
“练寺集吧。”
“还不到?”
“这不,问去了。”
孙大掌柜又打了个哈欠,回他的车上去了。
这同时,老亭已经来到康笏南的车前。
“老太爷,还是连个盹也没有丢?”
“你们都睡了,我得给你们守夜。前头是什么人,问清了吗?”
“听说镖局的郭师傅问去了,多半也是夜行的旅人吧。”
“还用你来给我这样说,这话是我先对他们说的。前方的灯光,也是我先发现的!老亭,这一出来,你也能吃能睡了?”
“白天太热,歇不好,夜里凉快,说不敢睡,还是不由得就迷糊了。”
“还说热!真是都享惯福了。嫌热,那到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