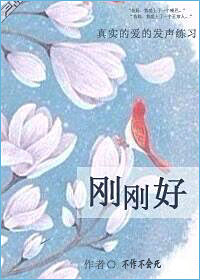不会游泳的鱼-第1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正想问问她失约的原因,这时她一挥手匆匆地说“回见”就小碎步地跑走了,随她望去,看见那个球星,她是奔他去了。
海海立在那儿,现在的心事他是懂的。现在的欢乐和难过比以前更甚,有点难以承受。先前的欢乐和伤感,是茫然的一片,现在却是明明白白。他搞不懂自己为什么知道是不能得,不可得,不该得,却就是那么地想要得到。
//
…
第六章桔树之江北,则化为枳(1)
…
“这是这个月的房租。”潘凤霞把一张支票递给老头。
到了月初付租时,董家还没有凑够钱。夫妻俩没办法了,一咬牙,说:“先给他一张空头支票。这几天把钱凑上。”“要是凑不上呢?”“那就装傻,就说银行出了问题。”夫妻俩点点头,所见略同的样子。
“谢谢。”老头没看一眼就收下支票,“两个孩子怎么样了?有空叫他们上我那,我给他们补习作文。”
“谢谢。”潘凤霞说,“我替我们全家谢谢我。你对我们很照顾。”
现在所有的社交基本都由潘凤霞出面。董勇怎么也不愿意开口说英语,总是支吾地混过去。而人家没有听懂,请他原谅,再说一遍,他就一副“说了会死”自我防范意识很强,打死也不再说一遍。潘凤霞就替他说,潘凤霞的英语也很烂,只是不停重复,手势丰富,表情生动,人家会意起来比较容易。有了潘凤霞,董勇就更不说英语。遇到非说英语不可的时候,他就“你说你说”把潘凤霞推到前台。
董勇说:“霞,你还真行。英语混混也就混出来了。”
潘凤霞不以为然地说:“学说话嘛,最主要的就是要脸皮厚。你得说啊。”
此话一出,董勇就没话了。这句话原是他的。当年他多机灵啊,学什么像什么,学广东人讲话,学福建人讲话,学陕西人说话,学完他自己不笑,很助兴地看别人笑,看见潘凤霞的笑更是失了禁。他在那模仿,她就在人群中早早地进入了期盼,哑着半启的嘴等待着他的把戏奏效。他们是多么一唱一和的一对。人家说:“董勇,你真有语言天赋。”董勇说:“学说话嘛,最主要的就是要脸皮厚。你得说啊。”
潘凤霞就是不明白那么机灵的人到了美国怎么就成了木头,什么都适应不来。潘凤霞已经能够应付基本的餐馆用语,被调到前面当服务生。董勇还是一句英语不说,还在厨房里打杂,不仅如此,而且打杂的活也没保住。现在全职在家里呆着,当起了家庭夫男,剪折扣券,承担所有家务。以前董勇是多么幽默、有才,大度,还有点坏。她能列出他一连串的优点,现在的董勇只剩下“老实”两个字。无能的人才老实呢。女人看不上老实的男人,觉得没劲。女人跟着老实男人,只是为了安全。可是这种安全在美国正是最大的不安全。潘凤霞觉得自己像一个走在穷途末路上的老人,毫无前途可言。
以后的几天潘凤霞回家的时候,总想着,别撞上老头,别撞上老头。说曹操曹操到。这一天老头迎面走来开门见山说:“这是一张坏的支票。”
潘凤霞先是装出听不懂他在讲什么的表情。她现在发现听不懂英语也不全是坏事,可以为自己赢得时间考虑对策。
老头抖抖手上的支票,叫着最简单的字眼:“坏的,坏的,没钱,没钱。”
装听不懂是装不下去,潘凤霞又换了一种假装。她假装天真地说:“你是说支票不能用?怎么可能?这不可能呀。”这几天,这个浑然无辜的表情一直在她头脑里表演着,今天现场即兴表演,仍是不尽人意。
老头婉转地说:“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自己有时候并不清楚,你们应该打电话到银行去问问。”
“可不是吗?”潘凤霞的吃惊更深了一步,像美国人那样两手合在胸前,嘴巴张得老大。
老头没去看她,似乎是不忍心看她。一个中年妇女为了一点房租竟然这样地表演起来,他都替她于心不忍。
“对不起。真的很抱歉。”
“下回要注意了。”老头又说,“谢谢你们把楼道扫了,谢谢你们送来的甜酸排骨。你们不需要做那些。”
“顺手的事。”潘凤霞的头低着,头发垂下,两个脚对得平平的,像受教导的学生那样谦卑着自己。这在老头眼里成了浅度的苦肉计。
“可是房租不能再拖了。”老头知道这话在这当下挺刺激,但他不得已。老头的意思是再明白不过了:不要以为扫扫楼道、送送甜酸排骨,就可以抵了你们的房租?
“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这个意思。”潘凤霞苦笑了一下,心里想,自己就是这个意思,至少可以换个通融晚些交房租。
“现在找到好的房客也不容易。大部分的房客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把音乐开得很大声,或者把邻居搞得不愉快。我一看到你们一家人就感觉诚实可靠。我是没有关系,可这不是我的公寓,我也是要交差的。最近什么东西都涨了。屋顶也要翻修一下,免得漏水。要知道,雨季快到了。”
老头似乎在不经心地饶着家常。脸皮再厚,也会被这些不经心的困境鞭笞、刺激出良知。没钱,廉耻还是有的。潘凤霞愧疚与难为情地低着头,保证道:“是是是。”
“那现在能付吗?”
//
…
第六章桔树之江北,则化为枳(2)
…
“我们下星期一定交,一定。下星期可以吗?”潘凤霞脸上的天真与眼里的哀求矛盾着。手上的两袋塑料袋从左手换到右手,再从右手换到左手,气氛中的尴尬使她的动作更加匆忙。她心里说:别再逼了,要是逼出人命可不好玩了。
“要下星期?”
“是这样的:我的先生失去了工作,现在全靠我当服务生的那点钱维持一家四口的开支。今天我打一个桌子,他们吃了一百块钱,我心里想那怎么也能给我十几二十块的。你猜他们付了多少小费?二块钱。我们这个月实在是太困难了。”
潘凤霞说着说着眼圈就红了。她想用手去擦擦泪,却又意识到这些眼泪没有必要去擦,留着更好,就改道去捋几下头发。
老头没料到潘凤霞给他来这一手,当场就慌了。他只看到潘凤霞生龙活虎的一面,一股子对生活经久不败的兴致和稳扎稳打的野心。他不曾见过她如此多愁善感,大概也觉得折磨过了头,他对此负有责任。他叹口气,缓和一下口吻:“我很抱歉听到这些。”
说完就去安慰潘凤霞。美国人的安慰方式都是一个山姆大叔结实的拥抱,同时说“总会有办法的一切都会好的”。潘凤霞于是不去计较这拥抱的紧度,把它当作美国礼仪。这圆滑的拥抱,让这个六十多岁的老光棍心里有了点激情,于是将她揽入怀中。这个丰满的中国女人身上带着一团治家、持家的温暖,这温暖使老头很触动。
潘凤霞承受着一些轻柔的抚摸,觉得有点不对劲了,她安慰自己,他都可以当你爹了,这么拍摸也是说得过去的。再接着老头又腾出一只手伸入她乌亮的秀发,亲吻她的黑发,再亲吻她咸咸的脸颊。这带着怜爱的亲吻,是对失意者的安慰。她能感觉那股热呼呼的呼吸,带着一种混沌的气体,这有点不合适了,可是为了那点可怜的房租,她也是可以适应的。
潘凤霞把自己从拥抱中温和地、不太伤老头自尊地挺出身来,把深埋在他肩头的脸扭过来,可怜又自尊地看了一眼老头,那意思是:我都惨成这样了,你好意思趁火打劫吗?
那一眼就足以让老头自责与害臊。说到底,还是一个洁身自好的老头。坏,也就坏在一张嘴巴上,心地还是有美国人民善良纯朴的一面。
他连忙放开潘凤霞:“对不起。我只是想安慰你,没有别的意思。千万别误会。房租,就下个星期交吧。”
她马上看到自己做出牺牲的回报。
“我相信你。”老头又说。这句话后面的意思是,所以你也要相信我。
“谢谢。”
老头想,得说点什么别的,把这有点僵的气氛缓和下来。于是闲聊起来:“是的。老实说,我是喜欢你们这家人的,你们总是说这么多的对不起、谢谢。你们的两个孩子也教育得很好,非常有礼貌。你知道这条街上的人并不这么说话,他们只会说带F的脏话,都是卡车司机的语言。”
“谢谢。”潘凤霞心里想,他们倒不是什么好修养,是穷得只能夹着尾巴靠着不停“对不起”、“谢谢”来替他们抵挡风寒。
“你看你又谢谢上了。”老头笑道。
“真的是要谢谢你嘛。这个周末到我们家来吃晚饭吧。”
“好。”老头眼睛看着潘凤霞手上的几个大袋子,“一个人拿这些太重了,让我帮你吧。”
“谢谢,不了。我可以叫我的丈夫来帮我。”
“你丈夫可能不在,因为我刚才去敲门,却没有人开门。”
“是吗?”潘凤霞脸上装得一无所知,心里想,黄世仁敲门,杨白劳敢开门吗?
果然她一进家门,董勇就从洗手间里探头探脑地出来,一脸的唬到还没有退却,小声而警惕地问:“没被那老头撞见吧。好险啊,刚才他来敲门,我就是不开,装作不在家的样子,嘿嘿……”
潘凤霞突然非常瞧不起他。他的头发又浓又密,油腻腻的,好几天没洗了。她无名火就上来了。潘凤霞之前所受的窘态本没什么,现在被丈夫的窝窝囊囊刺激出一肚子的气。
“董勇,你倒是会躲,让我在外面给你挡箭。董勇,你还是个男人吗?”
这句话是她来美国后最常吵的,也是潘凤霞最灵验的一句话,董勇一听这话就又泄气又生气,又来了。
他痛不欲生地骂道:“潘凤霞,你还有完没完?”
“让你老婆在外面挡风挡雨。你还是个男人吗?是男人你就应该养活老婆孩子,而不是躲在家里跟缩头乌龟一样。”
每每这时,董勇就不动声色地离开。幸亏他离开了,不然潘凤霞心里还有更恶毒的会说出来——董勇,就是因为你无能,别人在外面揩你老婆的油了。
退下来的董勇痛苦地想弄明白,那个温顺的小美人怎么就给这个凶神恶煞的母夜叉偷偷地掉了包。到了美国算是理解什么叫“桔树之江北,则化为枳”,那个风情万种的“祝兄”永远地留在了中国,现在这个凶巴巴恶狠狠的悍女人,他完全不认识。
//
…
第六章桔树之江北,则化为枳(3)
…
这时看见儿子女儿睡眼朦胧、泪眼朦胧地站在各自房间门口,同时看着他们。
“求你们别吵了,别吵了。我们都快被你们烦死了。”丁丁突然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说,“我们在学校已经过得很不舒心了,就指望家庭温暖了,现在家里又成了这样。真是外忧内患。我们来美国图个什么呀?有话不能好好说吗?为什么要这样骂来骂去呢?”
海海同情地看了父亲一眼,父亲在国外的失落他感同身受,为此不免抱怨母亲过分、无情,他扯了一嗓子:“妈,你别对我爸这样,我爸他心里不好受。”
“你们以为我心里好受吗?”潘凤霞一抹眼泪对她的一双子女说,“虽然我很抱歉让你们看到这些,但我也庆幸。”
丁丁愤愤地说:“庆幸?庆幸什么?”
潘凤霞说:“庆幸你们这么小就看见这一切,还来得及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人靠得住。你们只能靠自己。”
一向话少的海海也突然说了长长的一串话:“学校里不高兴,学校就像地狱,家庭里不幸福,家庭也像地狱,现在学校和家庭都不幸福,整个世界对我们就是地狱。”
潘凤霞听了这话,心里“噔”地一落。海海从来不表达情绪,通常是连个表情都没有,现在连“地狱”这种词都出来了,以后她也就不再敢当着孩子的面吵架,也担心对孩子造成心理阴影。
海海又过来劝父亲,他很重感情地拍拍父亲的肩:“爸,你别跟我妈一般见识。”
董勇抬起头看了儿子一眼,他微笑,艰难着自己。
似乎有一个伤痛存在于这个家庭,对于董勇,那是一个无法探知的伤痛。伤痛时时刻刻在成长、成熟,终于与他共存了。他的存在就是伤痛的存在,他成了伤痛自己。
伤痛不仅是董勇一人的,潘凤霞也有伤痛。董勇受伤后,她非常难过。她对自己说,我应该对董勇好一些。她拼命去回忆当年他们唱梁祝的情景,多么男才女貌的一对,堪称剧团的一道风景线。董勇到这年纪,可还算是帅的了,而且真心爱她。可是她进了家门,看见董勇在小灯底里翘着他残缺的食指剪折扣券,突然心里很烦,而且有点瞧不起他。那油腻腻的头发,她怎么曾经会视为潇洒呢?现在她都不能多看,一看就烦。她已经对他受伤的食指头视而不见了。他有时也能做到视若无睹,有时则要重点突出,总是在他耍赖的时候。他会拉着丁丁的手去摸他的伤痕,看着女儿半恶心半同情地皱着眉撇过脸去,他脸上会有一种无赖式的满足。不仅如此,他还会像孩子一样通过一些小事来发泄情绪。比如故意把电视开得很大声,比如莫明其妙发出几声怪叫。
今天潘凤霞进家门前,再一次对自己保证:不要给董勇发火,要对他好一点。她控制自己心里微度的厌烦,欢跃地拉着戏腔:
“梁兄,我回来啦。”
“回来了?”
“今天小费很高,我还从餐馆带了一些菜回来,你不用做饭了。”
“今天怎么样?”
“就是那样,一个字:累。一天下来我的骨头都快累酥了。再这么累下去,我早晚会给累死的。”
董勇不知道该说什么,说什么都显得自己挺无能,让老婆在外面如此操劳;不说又显得很不体贴。他只能“噢”、“噢”了两声。这时发现潘凤霞带回一大束鲜花,就把话题叉开:“这花哪里来的?”
“好讨厌啊,今天又有一个美国佬来找我麻烦。他一张口就对我说:你是我看过的最漂亮的东方女人。我有六幢房子,四部车子。”
潘凤霞夸张了一点点罢了。夸张的那一点点是女人的炫耀。
她在国内也常这样,三天两头地讲点艳遇给老公听听。比如:今天演出完了,又有个台商一直在后台等着,一见到我就说要娶我,说我是他见过的最有女人味的女人。接着就拿出一个五克拉的钻戒,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那钻戒的大小就随着她的手的比划一圈圈地放大。
董勇不是不知道:这些故事真真假假,加上她勤劳的想像力,这想像力是带幻觉的,直到她都真假难辩。可他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