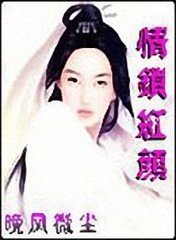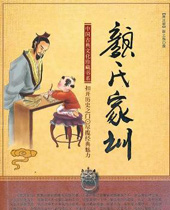一怒为红颜-第1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定是禹大哥提前回来了,我去开门。”她跳下椅子,连拖鞋都来不及穿,就三步并两步地冲去开门。
他笑着自语,“和小孩没两样嘛。爱黏人、心无城府,而且纯真、清新得让人打心底疼爱。”他提起她的拖鞋也跟着离开厨房。
沈蝶衣打开大门,笑盈盈地喊,“禹大哥,欢迎你……啊—;—;”待看清立于门口的人不是她期盼的人时,她的失望溢于言表,“你要找谁?”她无精打彩地问。
禹世岳莞尔一笑,“我虽不是你口中的禹大哥
沈蝶衣眨眼偏着头凝视他,想想在哪里见过他。猝然,惊恐的画面一闪而过,她想起他是禹世岳,郑曲伶的小叔。
郑曲伶的凶悍、阴沉,她记忆犹新,那巴掌更像噩梦般纠缠她好一阵子。
她机伶伶地打个颤,警戒地防备他,“找我有什么事?”她的手不自觉地抚着曾挨打的脸颊,害怕是他嫂子托他来找她。
禹世岳莫名其妙地说:“刚不是好端端的吗?怎突然害怕成这样子,我长得那么可怕吗?”他指着门内,“其中一定有误会,我们可以进屋谈吗?”
禹宴龙的叮咛犹在耳际,他不在家这期间,不许陌生男子进人屋内,于是她摇头拒绝。
这时候司马煌出现在她身后,她彷佛遇见救星,立即躲到他身后,“煌叔。”
他慈爱地拍拍她的手臂,“不用怕,有我在没人能动你。把拖鞋穿上,地板很冷,你进去吧。”
“嗯。”她瞄他一眼,留下他们独自进屋。
禹世岳想留住她,却被他阻止。
司马煌慈爱的神色褪下,换上精明、冷凝的脸孔。“你找蝶衣有何事呢?禹二公子。”
禹世岳吃惊地说:“你认识我。”
司马煌冷哼,傲然地说:“你尚未回答我的话。”
禹世岳心中有个大概,眼前这位难缠的中年人似乎是派来保护沈蝶衣的,看来,他的计画要成功比登天还难。“我想和沈秀聊聊,请她帮忙。”
“我陪你聊聊倒可以,蝶衣就免谈了。”司马煌仍挡在他面前。
二楼传出悦耳的钢琴声,禹世岳抬头望向二楼,司马煌则听着音乐,知道沈蝶衣的快乐、愁闷、悲伤都会藉弹琴来排解心底思绪。
“她为何怕我?”禹世岳不解地问。
“她不是怕你,而是你让她联想到你大嫂,郑曲伶曾对她施暴,怎不令她心有余悸呢!”司马煌解释道。
“大嫂怎会施暴呢?她们认识吗?”
“哼,你不会回去问她呀。”司马煌手指一弹,左右各走出一位男子,“请回去吧,不要再来打扰蝶衣。”他下着逐客令。
“我—;—;”禹世岳只说了一个宇,就被那两位男子请走。
司马煌暗忖,宴龙真的是神机妙算,要他保护蝶衣不受打扰,甚至,还怕有人不利于她,未雨绸缪调派保全人员暗地里注意她的安全。
第九章
圣诞节将至,商家播放圣诞歌曲,四处洋溢着浓厚圣诞节的气氛。
‘思乡’PUB店内也装饰着高大的圣诞树,布置的美轮美奂,还播放诗歌,让来自异乡的洋客人聊慰思乡之情。
这晚,坐在吧台前的有邬建良、江季穗夫妇及沈蝶衣,萧尧忠和阮秋红则在吧台内忙着为他们调饮料。
江季穗不时以奇异的眼光盯着沈蝶衣,邬建良则一副欲言又止的表情。
阮秋红调一杯胡桃咖啡给沈蝶衣,“蝶衣,陈家的公司倒闭了,你知道吗?”老天有眼,当她得知‘森畸’倒闭时,感到一阵大快人心,这叫现世报。
沈蝶衣拿着小汤匙搅拌起泡奶油,挑着胡桃,心不在焉地说:“不知道,也不想去知道。”她不想提起和陈家有关的事。
阮秋红啐道:“我最讨厌你这种消极、鸵鸟的心态,一旦讨厌的事一律不过问。嗟!受不了,至少你也该拍手叫好,他们终于遭到报应了。”
沈蝶衣浅浅地笑,睨她一眼,“你替我高兴还不是一样。”
萧尧忠把史丁格给邬建艮,把泡沫琴酒给江季穗。“秋红,人要有风度,纵然幸灾乐祸、高兴得要死,也不能表现得太明显。”他取笑阮秋红落井下石的坏心眼。
“你懂什么,那叫天谴、报应。”阮秋红大声嚷道。
萧尧忠不和她辩,招呼着客人。
邬建良啜口酒,忍不住疑惑地问:“蝶衣,你认识‘巨曜’企业财团的负责人吗?”
“不认识。”沈蝶衣迷惑不已,“怎么了?”
阮秋红口快地说:“邬大哥,蝶衣哪可能认识那种大财团。”她一副不可能的表情直摇头,沈蝶衣则附和地点头。
江季穗自语,“芬芳是这么告诉我的没错呀!”
沈蝶衣听到这个名字全身一震,“江姊,纪芬芳去找你!”
“那臭女人找你干么?”阮秋红的口气很冲。
江季穗叹口气,望邬建良一眼,见他点头,才开口道:“几天前我和建良在街上遇见纪芬芳,她形色枯槁,一副潦倒的模样令人同情。我叫住她,问她要去哪儿,她说要去找你。”
“找我。”沈蝶衣指着自己的胸口,“找我做什么?我没见到她呀。”
“她说‘纪氏’、‘森崎’是被你未婚夫整垮的,要找你算帐。”江季穗转述纪芬芳当时的话。
沈蝶衣的心一动,她是有要求禹宴龙为她讨公道,给他们一点教训,但并无意逼他们走上绝路呀!
“不对呀,禹宴龙是建筑设计师,哪有那么丰厚的财力及权势去整垮两家公司呢?”阮秋红分析其中不合逻辑的细节。
邬建良在贸易公司上班,哪会不知‘巨曜’这家国际间有名的大企业,那是世界十大排名之一的大公司。他听闻‘巨曜’的老板是法裔的华人;‘巨曜’第一代负责人曾遭人绑架,因而”巨曜’的继承人都不现身,只是隐于幕后推动业务。总之”巨曜’的负责人都蒙着神秘面纱。
“郑曲伶不知从哪弄来芬芳的电话号码,她告诉芬芳禹宴龙是‘巨曜’的负责人,他为了替你姊姊复仇才展开这场报复行动。”邬建良定定地看着沈蝶衣,“你真的不知道吗?”
她螓首轻摇,“我只晓得禹大哥是飞腾建设公司的负责人,其余一无所知。”她口中虽远么说,但她终于弄清楚,为何禹大哥身旁的左右手都是法国人,而且常有各种不同肤色的人找他。
江季穗想再问,但萧尧忠插入谈话间。
“你们不应再问蝶衣任何事,她已经说了她什么都不知道。诚如秋红所言,这是纪芬芳和陈森郁的报应,自作孽不可活,加诸于沈采桦身上的苦楚终也让他们尝到,从此毋需再谈这话题。”他突然强硬的作风,引得众人恻目。
其中最惊讶的人莫过于是阮秋红,她觉得萧尧忠似乎护卫着沈蝶衣。
沈蝶衣同意地颔首,并转移话题,“江姊、邬大哥,再两天后的圣诞节,姊姊就要回家了,各位到我家庆祝姊姊康复。”
“好呀,办个热闹的舞会。”江季穗提议。
“可以啊,大家疯狂热闹一番。”邬建良为沈采桦的痊愈高兴。
沈蝶衣一方面为姊姊能离开疗养院高兴,另一方面却因禹宴龙的逾期未归而难过,她想与他分享这份快乐。
“秋红,你可以借我抱抱吗?”沈蝶衣捂着胸口,“我这里好难过!”说着,她眼眶微红。
“不舒服吗?”江季穗伸手采试她的额头温度。
阮秋红走出吧台,来到她身旁,了然一笑地说:“想他!”阮秋红脚一蹬坐上高脚椅,旋转椅子面向她。
沈蝶衣旋过椅,倾着上半身抱住她,把头靠在她肩上,寻求她的慰藉。
阮秋红给予她安慰,抚顺着她的秀发。此时,门口有辆车大刺剌地停着,阮秋红正面对着门,看着那辆拉风的跑车很生气,心中暗骂,没常识乱停车,甚至停在店门口。
“尧忠,你去把那辆车赶走!没水准,乱停车。”她骂道。
萧尧忠探头往透明玻璃门一看,“是他。”他淡淡地说。
“你认识?”她见门一开走进一位高大、气势迫人的俊美男人。
他冷冷的眼光扫向他们,他们也都望着这位眉宇间散发狂野的男人。
禹宴龙身穿三件式的西装,外罩一件黑色大衣,踩着优雅的步伐朝他们走近。“我说过你只能在我怀中,为何依偎在她身上呢!”
那熟悉浑厚的嗓音和那独一无二的懒懒腔调,她永远也忘不了,沈蝶衣猛张开眼,抬首看向发声处,朝思暮想的人已近在咫尺。
“禹大哥。”她的思念已尽在此言中。
禹宴龙满意她的想念,想必他的重要性已在蝶衣心中占绝大部份,他想。
他伸手举起她,她双手环抱他颈项,整个人贴在他身上。“你骗人,说要打电话给我也没有,而且超过五天才回来。”她娇嗔道。
禹宴龙抱着她,张狂地笑,“想我吗?”他完全无视众人的侧目。
“嗯,非常地思念你。”她仰着头,快乐写满她眼底,“我有好多好多快乐的事要说给你听哟。”
“回家再慢慢告诉我吧。”他抱着她就往外走,连让她和朋友道再见的时间也没有,没一会,门外的跑车迅速消失夜色里。
禹宴龙的霸道、独裁让众人都咋舌,“他是谁呀?从进门到离开看也不看我们一眼。”邬建良问出所有人的疑问。
他们皆以为回答的会是阮秋红,没想到是萧尧忠解答。
“蝶衣的未婚夫,禹宴龙。”
“连我都没见过他,你怎会知道那是蝶衣的未婚夫?”阮秋红用古怪的眼神看他。
“我认识他呀。”萧尧忠耸耸肩,拿着抹布擦台面,“就是他来取消蝶衣的工作。”
邬建良和江季穗面面相觑,心中有着同样的疑虑,“他看起来顶多三十几岁,能接掌跨国际的庞大事业吗?”
萧尧忠笑而不语,不予置评。
四人聊了好一会,“太晚了,该回家。”邬建良夫妇告辞离去。
阮秋红抓住萧尧忠的手臂,“嘿,他们都离开了,老实告诉我,你所知道的内情。”
萧尧忠亲亲她的脸,“什么内情,我不知道呀。”
她巴着他,“哼,别想瞒我,快说。”
他翻翻白眼叹口气,了解阮秋红的个性跟牛一样的固执,若不告诉她,她绝不会善罢甘休。
“禹宴龙是不是‘巨曜’的负责人我不清楚,但他是我的合伙人,这间PUB是他的,他提供资金、店面,由我在幕前经营。”他与禹宴龙相识是他生命里一场难得的际遇。
她张口结舌,错愕不已,“原来你们是这层关系,所以你才会出面替蝶衣解围。”
“当你的蝶衣他们来这里,我就接到他的电话,要我暗地里看着她,不许有人问及陈家的事。”
“照你所言,蝶衣被监视。”
“是保护!禹宴龙是位可怕的人物,深沉难懂、吃人不吐骨头,惹上他绝没有好下场。”
阮秋红吁口气,偏头笑着说:“他那么可怕,配蝶衣正好,她柔得像水。本来我还有些担心,怕纪芬芳那儿女人找她,会欺负她,这下,嘿,我可放心了。”
“纪芬芳别想见到蝶衣,想接近她,得通过滴水不透的防卫层。”
“太棒了,客人又上门了,工作工作!”阮秋红催促着他。
禹宴龙感冒了,头痛地在卧房休息。
沈蝶衣从唱片公司回到家后,司马煌就告诉她这件事,她一听急忙要上楼探视他。
“蝶衣,等等。”司马煌叫住她。
“惶叔,有事吗?”她回头看他。
“宴龙一感冒脾气就大得吓死人,他的习性是要只安静休息一天病就好了,绝对不能去吵他。”他怕她踩到地雷。
禹宴龙的家人都知晓他这习性,若惹恼他,他可是六亲不认的。
“我知道了。”沈蝶衣点点头,放轻脚步声上楼。
司马煌坏心眼地想,自己今日绝不上二楼,蝶衣愿送死,他也‘没法度’,自求多福比较实在,闲闲地泡荼、啃呱子总比面对发怒的狮子好。
沈蝶衣安静无声地打开卧室的门,悄悄地走到床边,看见他睡着了,她到窗边拉上窗帘隔开冬日的阳光,让他睡得舒服些。
刚回家就生病,唉!她拉张椅子在床旁坐下,把牛皮纸袋内的纸张拿出来,用迥纹针固定成一叠,翻阅着一张张的歌词。
禹宴龙并没有睡得很沉,他感觉身旁有人彷佛在偷窥他。他心中嘀咕着,哪个不知死活的人,敢在他不舒服的时候在他房间。
他微张眼睛,正想开口骂,看清那人是沈蝶衣后,又把话吞回肚里,他注意着她的动作。
她看看歌词,又把目光移到他脸上,眼底净是担忧。
他张开眼睛对上她的目光,他炯亮的眼神让她吃一惊。
“你醒啦!我吵到你了吗?”她倾向前俯视他。
“没有。”
“那我留在这里陪你好吗?我不会出一丁点的声音,我只想在你身边。”
乍见她坐在床边,奇异的,他并不生气,心底溢满幸福、温馨的感受,这异样的感觉来自她真心的关怀吧。
禹宴龙掀开棉被的一角,“躺进来,坐久可会冷的。”
沈蝶衣高兴地脱掉鞋,钻进被窝里抱住他,而他感冒仍不改习惯,还是裸着上身睡觉。
他把棉被拉好,密密地盖住两人,阖眼休息。
她抱着他,下巴靠在他裸胸,静静地盯着他看,唇畔泛起一抹笑意。
“笑什么?”他闭着眼问。
“咦!你怎知我在笑呢?”她微微惊诧。
“我感觉得到呀。”他掀起眼险,捏捏她的鼻子,“还没告诉我,你在笑什么?”
沈蝶衣笑咪咪地说:“平时你总露出不可一世的表情,霸道得很,没想到你也会感冒,病毒碰到你应该会毙命的呀!”
他啐道:“坏心眼哦!竟取笑我会生病,人吃五谷谁不会生病。”
“抱歉啦,我不是故意笑你。”她伸手抚着他突出的五官,“不要生气好吗?其实我很懊悔不能为你做些什么,可是这时候你不舒服,我可以乘机照顾你,回报你一些。”
他又闭上眼,手搂紧她,“那就闭嘴,陪我睡。”
“嗯,好。”她满足地更偎近他怀里。
晚餐时,沈蝶衣为他煮一锅香芋粥,端到卧房喂禹宴龙。
司马煌拍额称奇,蝶衣居然能平安无事,没被轰出来。他存着她没事,自己应该也会没事的心态,干脆用托盘装着晚餐也上楼,移位走到卧房门口用餐,打算观看文艺戏。
但他才扒口饭,饭尚未吞下就差点被禹宴龙丢来的枕头砸到,禹宴龙就要再丢第二个枕头时,他举手阻止,“别丢,我马上走。”他差点噎死,兼被枕头打死。司马煌只得再次端起托盘幸幸然地下楼,口中嘀咕着,“回餐厅吃饭吧!爱情戏甭看了,可惜哪。”
沈蝶衣眼见滑稽那一幕,不觉地笑出声,“煌叔好‘古锥’哦。”
“哼,那是活得愈老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