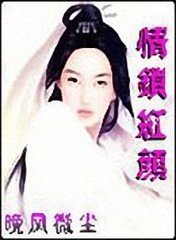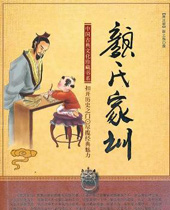一怒为红颜-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沈蝶衣流着泪静静听着邬建良夫妇轮流描述妹姊婚后所受的苦,愈听,她的心愈痛,泪珠掉得更快。
“爱情是经不起百般摧残,采桦再也无力坚持这段婚姻,伤痕累累的她,终于答应她公婆的要求和陈森郁离婚,但就在她要签字的两天前,上天和采桦开了一个玩笑,采桦发现她怀孕了。”江季穗长长叹口气,“采桦为了孩子反悔不肯离婚,想当然尔,采桦的日子定是更难过……”
她顿了顿,“陈家所经营的公司在那时候所投资的事业产生危机,面临倒闭,于是陈家对采桦提出无理的要求,一是离婚让陈森郁迎娶正在交往的纪秀,她家的财力能让公司起死回生、渡过危机;二是,采桦扛下所有的债务以挽回这桩婚姻。好胜心强的采桦应允了第二个条件,相信她丈夫对她的爱应能顺利的让她处理债务。”
江季穗义慎填膺地接着说:“采桦错估陈森郁的感情,债务一转移到采桦名下,他就推卸所有的责任,继续和那位纪秀拍拖。采桦变卖你父母留下的所有财产清偿债务,有天采桦回家在卧室撞见陈森郁和纪秀在床上偷情,于是,在双重刺激下,采桦从二楼滚下来流产了,失去孩子的打击让她崩溃了,她躲进虚幻的世界不敢再面对这无情的世间。”
听她叙述完这场悲剧,有泪不轻弹的邬建良也红着双眼。
沈蝶衣抹去泪水,心细如发的她提出疑问,“那这幢房子怎没卖掉呢?”
“采桦把地契拿去向银行借贷八百万,再不缴纳利息这幢房子将面临拍卖的命运。”邬建良歉然地道,“最近这两个月我们实在没办法再替采桦付银行利息……”
“邬大哥,谢谢你们替姊姊所做的一切,剩下的就交给我了。”沈蝶衣知道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家庭要照顾,上班族的薪水有限,他们能撑到她回国已属不容易,“陈森郁就放任姊姊不管,包括债务方面吗?”
“陈家推卸得很干脆,已离婚的下堂妻和他们无关。”江季穗激动地挥着拳头,“说什么转移债务要办假离婚才能不牵连公司的营运、这根本就是圈套,找采桦当替死鬼。他们可逍遥了,既没债务,独生于又娶个门户相当的富家女。”说完,她用鼻音重重哼一声,充满鄙视、不屑之意。
“除了银行外,姊姊还背负多少债务?”沈蝶衣无力地问,也为自己做心理建设,未来她的生活将是愁云惨雾,和债务为伍。
邬建良轻轻地说:“一千万。”说完,他闭上眼,不忍看她无助的脸庞。
沈蝶衣双手放在椅子的把手上,脸埋进臂弯。看来她这一生也还不完这所有债务,她该怎么办呢?
邬建艮夫妇不知如何安慰她,所有安慰的话语在这一刻说出来都显得太矫情。
“邬大哥、江姊,请你们把姊姊所在的院址写下来,我想静静地思考。”沈蝶衣虚软的轻语从臂弯处飘出。
他们把院址写在便条纸上,不再多说,悄然退出并为她锁上门。
飞腾建设公司
郑曲伶穿着一套诱人的低胸紧身红色洋装迈进公司,举手投足净是撩人的风情,让办公室里的员工直勾勾地盯着她瞧。
“伍秀,燕龙在吗?”她大刺刺靠在伍研沁的桌前问道。
伍研沁从设计图上抬起头,不高兴在绘图工作时被打扰,“郑秀,老板尚未从加拿大回来,你来公司也没用,况且你坏了老板的规矩,他不准女友来公司打搅他工作,他会非常生气的。”她心想,老板昨天就回来了,自己偏不告诉她。
“不久燕龙就会成为我老公,我凭这点就敢到公司逛逛。”郑曲伶骄傲地宣布着。
她的宣告立刻引起办公室的员工一阵哗然,可是没人相信她的话,老板这只采花蝶会甘愿停留在一株花朵上吗?不可能的。
伍研沁不留一点颜面给她,讥讽道:“一个月前,这里站着一位美艳的尤物叫珊蒂,跟你一样宣布同样的消息,没两天的光景,她被老板剔除生活外,从此想见老板一眼比登天还难。”她眼神露出不屑、鄙夷的光芒。
另名员工谢秩恒也走近她们,“郑秀!你应该很清楚老板是换女人比换衬衫还快的花心男人,没有人能进驻他的心底,所以你不要来公司乱宣布消息。”
“是吗?没多久你们就知道我的厉害,到时候我会以老板娘的身分请你们两位回家吃自己,出言不逊的代价就是如此。”郑曲伶颇富心机的眼眸恶毒地瞪视他们。“我回去了,燕龙回来要他和我联络。”她命令式的语气彷拂他们是下人。
伍研沁怒瞪她离去的身影,咬着牙骂道:“八爪女!仗着自己的美貌和人尽可夫的身体就随意侮辱人实在可恶,我就不相信老板真的会娶她,除非瞎了眼。”
谢秩恒拿着建筑设计图在空气中扇着,“她的香水会毒死人。”他受不了整个室内溢着浓馥的香水味。
他的一句话引得办公室的众人哈哈大笑。
此时,坐在五楼的禹燕龙从监视系统中把郑曲伶和伍研沁、谢秩恒的对谈都听进耳中,他冷冷地笑着,阴鸶的眼眸射出寒光。曲伶对自己自视太高,更低估他的能耐,她想凭什么收服他呢?美色?或是金钱?哼!他倒想看看她能耍什么手段。
坐在禹燕龙对面的两位建筑师都被他阴沉的表情给吓到,这样的禹燕龙令他们不寒而栗,更往椅子里缩,生怕扫到台风尾。
沈蝶衣伫立于安辉精神疗养院外,迟迟提不起勇气按铃进人院内,眉睫间净是哀伤地注视宽广的疗养院。
她静然呆立在门外多时,引起守卫的侧目,毕竟精神疗养院一般人是不会轻易涉足的,因为怕被人当成疯子看待。
守卫打量门外的女孩,穿着白色洋装、凉鞋,脂粉未施,乌黑闪亮的披肩秀发,清秀美丽的脸蛋,虽然稍嫌瘦弱些,但是位清秀雅致的佳人。
守卫打开侧门走出来,“秀,你有事吗?”
沈蝶衣乍闻问话声,猛然转向发声处,才发现身旁不知何时站了人,她太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连别人靠近自己都不自知。
“我想探望我的姐姐。”她呐呐地说。
守卫从她眸低看到浓浓的哀愁,暗叹她那双乌黑日莹的大眼盛满哀愁,破坏就有明这灿烂的光芒
“为何不按铃进来呢?”他从她的神情得知她的畏缩、不安,“进来吧,我叫工友带你去医务室,你不曾来探病嘛。”
“我刚回国,才知道姐姐在此疗养。”沈蝶衣怀着改惶惶不安的心跟随守卫进入疗养院。
守卫招来一位工友,托他带领沈蝶衣到医务室。
一位女医生接见她,“我是这家疗养院的主任,小贵姓,想探望哪能位病人?”
“我叫沈蝶衣,我想探视我姊姊沈采桦,可以吗?”一路走来沈蝶衣不敢相信在花园草坪上的男男女女都是精神异常者,他们看起来和正常人没两样。
女医师翻阅病历卡,“沈秀,令姊的主治医师是周贤民医生,我请他带你去见她,顺便了解她的病清。”
“嗯,谢谢。”
等了一下子,一位身穿医师白袍、斯文俊秀的男士走了过来。
周贤民露出亲切和煦的笑容。“沈秀,请跟我来吧。”他已从内线电话中得知她是沈采桦的妹妹。
两人沿着长廊前进,沈蝶衣轻轻地问:“周医师,我姊姊的病严重吗?”
“她的情绪还不是很稳定,有自虐的倾向……”他把沈采桦的病情大致告诉她,“或许你回国了,对她的病情会有很大的帮助,她非常思念你,亲情的抚慰比任何药物治疗还有效。”周贤民从邬建良夫妇的口中得知沈采桦一切的遭遇,以及沈蝶衣的种种。
“那我可以带姊姊回家吗?”
“不行,她受的打击太大了,导致她精神崩溃,然而,最大的打击来自于她的流产。她把全副的心力投注于腹中的胎儿,胎儿没了,她自责得非常厉害。一年的时间里她仍幻听到小孩的呼唤,责骂她不是好妈妈,没有保护他,所以她想寻死去陪伴她的小孩,绝不能让她拿到尖利的物品,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我明白了。”沈蝶衣红着眼眶,她可以想像姊姊那痛苦的哀嚎,只求能和死去的胎儿相聚。
“到了,就是这里。”周贤民拍拍她的肩给予勇气、“沈采桦最近幻听的情形较少了,自虐的次数也比往常少很多,你安心地进去吧,她就像正常人一样。”
“谢谢你。”沈蝶衣感激地说道。
他示意护士为她打开门。
沈蝶衣迈着沉痛的步履进入病房内,终于,在房间窗台前看到睽违已久的身影,决采桦正趴在窗口看着花圃,蝴蝶的飞舞吸引她的目光。
沈蝶衣想哭,却又不得不忍住泪水,发热的眼眶令她难受,双手捂住嘴巴强咽下哭声,想用笑脸拥抱她最爱的姊姊。半晌,她才缓缓开口,“姊,我回来了。”
熟悉的嗓音让沈采桦僵住了,午夜梦回她都听到她最疼爱的妹妹撒娇腻着她的嗓音,可是一回头张开眼,妹妹的踪影就消失了,她才想起妹妹在德国哩。现在才下午,她也没睡觉,为何会听见妹妹的声音呢?
“姊,不回头看看我吗?难道你不要我了。”沈蝶衣颤抖着发出声音。
沈采桦霍然回头一看,泪水迅速淹没双眸。“蝶衣,真的是你?”她颤巍巍地问,生怕是南柯一梦。
“是我,我学成归国了。”沈蝶衣任由重逢的泪水流下,投进姊姊的怀抱“我好想你。”
“我也想你。”沈采桦抱紧沈蝶衣,“我天天盼望你早日回国,每天我都拿着你的照片端详,好怕你不要我。”在她封闭的世界里她仍然惴惴不安,生怕遗弃她的世界也会带走她最爱的妹妹。
“我永远爱你,怎会不要你呢?”沈蝶衣好心酸,一向精明能干的姊姊变得宛如迷失的小孩,上苍为何如此对待她呢?
第二章
傍晚时分,沈蝶衣向守卫领首,步出疗养院。她沿着坡道踽踽独行,心头沉甸甸,压得她喘不过气来。陪了姊姊整个下午,姊姊恍恍偬惚地诉说自己的婚姻,讲到流失胎儿时,姊姊激动地掐住她的手臂,整个人陷入疯狂状态,不知道已在无意中使她受伤。
安抚住她激动的情绪,姊姊又陷人空洞的冥想里,忽略她身旁的妹妹,直到许久后再度宛如正常人般清醒,才发现蝶衣两只手臂净是她的抓痕……
沈蝶衣回想下午的相处,再也隐忍不住泪水,为姊姊的不幸哀痛,她干脆蹲在路旁,掩脸哭泣。她实在无法坚强面对邃变的姊姊,她就像菟丝花般攀爬姊姊这棵大树依附着,如今……
她不愿邬建良夫妇看到她软弱的一面,因此她独自来探望姊姊,而事实证明她是个软弱、没有勇气的人,承受不了时,唯有用哭来逃避一切。
禹燕龙驾着吉普车前往安辉精神疗养院,这家疗养院是他外公开办,现在由他继承。
“咦?那女孩蹲在路旁干么?”
他脑海中迅速掠过几个问号、心想,莫非是追求他的女人所耍的花招,故意引起他的注意。但是,他的行踪没有人能掌握,也没有人知道他是安辉幕后的老板。
他轻哼,不想理她,反正,最近他对女人失去兴趣,女人大都是贪婪的,一旦对她好点,就希冀得到他的人、霸占他全部的爱,烦死了。
他踩下油门加速越过路旁的她,当车子超过她五十公尺,他的手不由自主地转动方向盘把车掉过头驶回方才减速的地方。
他停下车,懊恼自己反常的举动,用手指梳爬额前的刘海,自嘲自己以冷硬、铁石心肠出名,居然会为蹲在路旁的女孩浪费宝贵时间,天要下红雨了!
下车,他走近女孩身边,见她纤瘦的肩膀抖动不已,整张脸埋在双臂中。他揪见她雪白的手臂有明显的抓痕,令人怵目惊心,而且每一条抓痕都渗着血丝。
“秀,你受伤了吗?”他温声问道。
见她没有回答,没有耐心的他,冷笑着想掉头就走,不再搭理她。可是,他的心再次背叛意志,促使他半弯下腰,伸手去摇她的肩胛,“秀,你怎么了?需要我帮忙吗?”
他手掌的温热透过衣衫传到沈蝶衣的肌肤,她震了一下,缓缓抬起头,侧看肩膀上温热的手掌,顺着手掌向上望,她看见一张浓眉、五官分明帅气的男性脸庞。
后知后觉的她,瞪视眼前的陌生人,防备的神情表露无遗,“先生,有事吗?”她扫掉她肩上的大手,想要站起来,可是脚麻得差点站不起来。
她完全不晓得双眸因哭泣太久,而肿成核桃般大,脸色苍白的这副柔弱样子都落人禹燕龙的眸底。
“我问你怎么了?你却问我有事吗?”他觉得这情形还真好笑,“难不成我方才的问话你都没听到。”
沈蝶衣摇摇头,把落在颊边的发丝拨向耳后,掏出手帕擦拭脸上的泪痕,“对不起,我要走了。”她急忙想要离去。
“等一下,你受伤了,我送你去医院。”禹燕龙话一出口,自己也吓一跳,他心想,今天下午自己是哪条神经不对劲,变得如此鸡婆、好心肠,也许是她那楚楚可怜的模样,让人不由想保护她吧。
沈蝶衣注视着手臂上的伤势,那皮肉之痛远不及心痛,“不用了,谢谢你。”她漠然道谢后,朝着公车站牌走去。
“奇怪的女孩。”禹燕龙点燃一根烟,睇睨着渐行渐远的背影,他莞尔一笑,自语道:“难得八百年才发一次好心,结果得了一个闭门羹。”他觉得那女孩挺有个性的。
他捻熄香烟,告诉自己,算了吧,他还有事要处理,可没空再去理那不相干的陌生女郎。
阮秋红站在沈家的门前叹息,蝶衣回国也过了两星期,可是这段日子蝶衣避不儿面,说是要想想未来的事,想通了自然就会去见她,可是快半个月了都没消息,她实在担忧蝶衣会想不开,于是她迳自跑来沈家。
阮秋红伸手按门钤,为好友的遭遇感到心痛。这种与债务为伍的日子很难熬,都是那个陈森郁王八羔子的错,她咒他不得好死。
门一开,沈蝶衣看见是好友阮秋红,心中原本的惶恐不安才退去,她害怕下楼开门,怕再面对那些来讨债的人。
他们的消息好灵通,她回到家的第二天就陆续有人打电话来讨债,说什么姊债妹还是天经地义的事,甚至还挖下狠话,若她不还钱就要给她好看。唉!还有人是登门要债……
“蝶衣,你看到我好像松了一口气,怎么了?”阮秋红仔细地瞧着她的神色她的眉宇间有着浓浓哀愁,这些哀愁进驻她眸底,她知道吗?“你消瘦许多,你知道吗?”阮秋红伸手抚着她明显消瘦的脸蛋。
“进来吧。”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