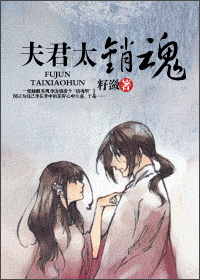匆匆,太匆匆-第1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中自己那已开始 涣散的神志。她蠕动着嘴唇,低呼了一个名字,谁也没听清楚她喊的是谁。然后,她叹了口 气,用比较清晰的声音,说了一句:“缘已尽,情未了!”接着,她用左手握住床边的母 亲,右手握住床边的父亲,闭上眼睛轻声低语:“不再流浪了,不再流浪了!”
这是她说的最后一句话。
袁嘉珮,乳名鸵鸵,在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弥留,二十五日死于肝癌,并非肝炎。 年仅二十四岁!
二十四!这数字好像一直与她有缘,她是在二十四日遇到韩青的,她弥留那天,正是他 们认识五十四个月的纪念日,勉强挨过那一天,她就这样默默的走了。
韩青赶到台北,鸵鸵已经去了。他竟来不及见她最后一面!他没有哭,没有思想,没有 意识,从荣民总医院大门出来,他只想到一个地方去,海边。鸵鸵最爱看海,相识以来,他 曾带她跑遍台北近郊的海边。最后一次带她看海,是他还没退役的时候,那天是他休假,她 到新竹来看他,又闹着要看海。他起码问了十个人,才知道最近的海边名叫“南寮”,他一 辈子没去过南寮,却带着鸵鸵去了。那天的鸵鸵好开心,笑在风里,笑在阳光里,笑在海浪 帆影中。那天的他也好开心,笑在她的欢愉里,笑在她的喜悦里,笑在她的柔情里……他曾 一边笑,一边对着她的脸儿唱:
“阿美阿美几时办嫁妆?
我急得快发慌……“
是的。海边。鸵鸵最爱去的地方。
他想去海边,于是他去了。
在沙滩上,他孤独的坐着。想着鸵鸵;第一次和她看海,她告诉他,她心里只有他一 个!最后一次和她看海,他对她唱“阿美阿美几时办嫁妆?”现在,他孤独的坐在沙滩上, 看着那无边无际,浩浩瀚瀚的大海,整个心灵神志,都被冻结凝固着,那海浪的喧嚣,那海 风的呼啸,对他都是静止的。什么都静止了,时间,空间,思想,感情,什么都静止了。
“又怕你飘然远去,让孤独笑我痴狂!”
忽然间,这两句歌词从静止的思绪中迸跳出来。然后,他又能思想了,第一个钻入脑海 的记忆,竟是数年以前,丁香也曾坐在沙滩上,手中紧抱着徐业伟的手鼓。
他把头埋进弓起的膝盖里,双手紧握着圈住膝头。他就这样坐着,不动,不说话。海风 毫不留情的吹袭着他,沙子打在他身上,后颈上,带来阵阵的刺痛。他继续坐着,不知道坐 了有多久,直到黄昏,风吹在身上,已带凉意,潮水渐涨,第一道涌上来的海浪,忽然从他 双腿下卷了过来,冰凉的海水使他浑身一凛,他蓦的醒了过来。
他醒了,抬起头来,他瞪着海,瞪着天,瞪着他不了解的宇宙、穹苍。然后,他站起身 子,机械化的移动他那已僵硬麻痹的手脚,缓缓的向海岸后面退了几步。站定了,他再望着 海,望着天,望着他不了解的宇宙、穹苍。突然间,他爆发了!用尽全身的力量,他终于对 着那云天深处,声嘶力竭的大喊出来:“鸵鸵!鸵鸵!为什么是你?为什么是你?你还有那 么多的事要做!你的法国呢?你的巴黎呢?你的香榭大道和拉丁区呢?还有,你的木棉花 呢?你的写作呢?鸵鸵!你怎么可以走?你怎么可以走!你那么热爱生命!你那么年轻!你 答应过我要活到七十八岁的!七十八岁的!难道你忘了?你许诺过我,要用四十年的生命来 陪伴我!四十年!你忘了?你忘了?你说过要告诉我们的子孙,我们曾如何相知和相爱,我 们的子孙哪!难道你都忘了!都忘了?为什么在我这样拚命的时候,你居然可以这么残忍的 离我远去!鸵鸵!鸵鸵!鸵鸵……”他望天狂呼,声音都喊裂了,一直喊到云层以外去。 “鸵鸵!鸵鸵!鸵鸵……”
他一连串喊了几百个“鸵鸵”,直到发不出声音,然后,他扑倒在一块岩石上,在这刹 那间,许多往事,齐涌心头;那第一次的舞会,那八个数字的电话号码,那小风帆的午餐, 那第一次牵手,第一次接吻,第一次看海,第一次去赵培家,第一个周年纪念日……太多太 多,数不清,算不清。多少恩爱,多少誓言,多少等待,多少计划……包括最后一段日子中 的多少煎熬!难道都成追忆?都成追忆?哦!太不公平,这世界太不公平!他以为全世界没 有人可以分开他和鸵鸵,但是,你如何去和死神争呢?他从岩石上慢慢爬起来,转过头来, 他注视着天际的晚霞,那霞光依然灿烂!居然灿烂!为谁灿烂?他再度仰天狂叫:“上帝, 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数年前,他曾为徐业伟狂呼,那时,鸵鸵尚在他的身边,分担他的悲苦。而今,他为鸵 鸵狂呼,身边却一个人都没有。他仰首问天,天也无言,他俯首问地,地也无语。他把身子 仰靠在那坚硬的岩石上,用手下意识的握紧一块凸出的石笋,那尖利粗糙的岩石刺痛了他的 掌心,他握紧,再握紧……想着水源路的小屋,想着赤脚奔下三楼买胃药,想着拿刀切手指 写血书,想着鸵鸵捧着十二朵玫瑰花站在他的门前……他不能再想,再想下去会追随她奔往 大海,这念头一起,他瞪视海浪,那每个汹涌而来的巨浪,都在对他大声呼号:
“不能同生,但求同死!”
他被催眠了,脑子里一片混沌。
离开了身后的岩石,他开始向那大海缓缓走去,一步又一步,一步又一步,一步又一 步……他的脚踩上了湿湿的沙子,浪花淹过了他的足踝,又向后面急急退走,他迈着步子, 向前,再向蝌蝌蝌蝌虬……
忽然,他听到鸵鸵的声音了,就在他身后清清脆脆、温温柔柔的嚷着:“有就是没有! 真就是假!存在就是不存在,最近的就是最远的……”他倏然回头,循声找寻。
“鸵鸵!”他喊:“鸵鸵!”
鸵鸵的声音在后面的山谷中回响,喜悦的、快乐的、开心的嚷着:“我的,你的,一 切,一切,是我俩的一切,我俩的巴黎,我俩的木棉花!”“哦!鸵鸵!”他咬紧嘴唇,直 到嘴唇流血了。他急急离开了那海浪,奔向岸边,奔向沙滩,奔着,奔着。一直奔到筋疲力 竭,他倒在沙滩上,用手紧紧的抱住了头。哭吧!他开始哭了起来。不止为鸵鸵哭,为了许 多他不懂的事而耶小伟,鸵鸵,小梅梅,和他们那懵懂无知的青春岁月!当那些岁月在他们 手中时,几人珍惜。而今,走的走了,散的散了,如诗如画的鸵鸵,竟然会与世长辞了。
他似乎又听到鸵鸵那银铃般的声音,在唱着那支她最心爱的歌“All Kinds of Everything”
“雪花和水仙花飘落,蝴蝶和蜜蜂飞舞,帆船,渔夫,和海上一切事物,许愿井,婚礼的钟声,以及那早晨的清露,万事万物,万事万物,都让我想起你——不由自主。
… 。“他用手蒙住耳朵。万事万物,万事万物,都因鸵鸵而存在。如今呢?不存在就 等于存在吗?存在就等于不存在吗?鸵鸵啊!你要告诉我什么?或者,我永远追不上你的境 界了!你的境界太远,太高,太玄了!鸵鸵!我本平凡!我本平凡!我只要问,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风呼啸着,浪扑打着,山顶的松籁,和海鸥的鸣叫,浪花的怒吼… 万事万物,最后, 全汇成了一支万人大合唱,汹汹涌涌,排山倒海般对他卷了过来:“匆匆,太匆匆!”匆匆,太匆匆!“尾声韩青说完了他和鸵鸵的故事。
桌上的烟灰缸里,已经堆满了烟蒂,烟雾继续在空气中扩散着,时间已是八月一日的凌 晨了。
他的身子靠进椅子的深处,他的头往上仰,眼睛无意识的看着我书房的天花板,那天花 板上嵌着一排彩色玻璃,里面透着灯光。但,我知道他并不在看那彩色玻璃,他必须仰着 头,是因为泪珠在他眼眶中滚动,如果他低下头,泪水势必会流下来。室内静默了好长一段 时间,我的稿纸上零乱的涂着他故事中的摘要,我让我的笔忙碌的画过稿纸,只为了我不能 制止住自己眼眶的湿润。过了好一会儿,我想,我们两个都比较平静了。我抬眼看他,经过 长长的叙述,陌生感已不存在,他摇摇头,终于不再掩饰流泪,他用手帕擦亮眼睛,我注意 到手帕一角,刺绣着“鸵鸵”两个字。“你每条手帕都有这个名字吗?”我问。
“是的。”我叹口气。不知该再问些什么,不知该再说些什么。事实上,韩青的故事叙 述得十分零乱,他经常会由于某个联想,而把话题从正在谈的这个“阶段”中,跳入另一个 “阶段”里。于是,时间、事件,和地点,甚至人物,都有些混淆。而在叙述的当时,他曾 多次咬住嘴唇,抬头看天花板(因泪水又来了),而让叙述停顿下来。我很少插嘴,很少问 什么,我只让他说,当他说不下去的时候,我就靠在椅子里,静静的等他挨过那阵痛楚。故 事的结局,是我早就知道的,再听他说一次,让我更增添了无限惨恻。我叹息着说:“肝癌,我真不相信一个年轻人会害上肝癌!”
“我一直以为是肝炎,小方也以为是肝炎。”他说。闪动着湿润的睫毛。“其实,连小 三小四都不知道她害了绝症,只有她父亲知道,大家都瞒着,我去看她的时候,我做梦也想 不到她会死!做梦也想不到!”他强调的重复着,又燃起一支烟。“可是,事后回想,我自 责过千千万万次,鸵鸵一直多病,她的胃——我带她去照过X光。比正常人的胃小了一半, 而且下垂,所以她必须少吃多餐。她身体里一点抵抗力都没有,流行感冒一来,她总是第一 个传染上… 在台北的时候,我常为了拖她去看医生,又哄又骗又说好话,求着她去。从没 见过比她更不会保护自己的人!如果她早些注意自己的身体,怎样也不会送命,她实在是被 耽误了,被疏忽了。如果我在台北,如果我守着她,如果我不为了证实自己而去南部… ” 他咬紧牙关,从齿缝中迸出一句话来:“她一定不会死!她一定不会死!”“别这样想,” 我试图安慰他,室内,悲哀的气氛已经积压得太重了。“或者,她去得正是时候。二十四 岁,最美丽、最青春、最可爱的年龄,去了。留下的,是最美丽、最青春、最可爱的回 忆。”“你这样说,因为… ”
“因为我不是当事人!”我代他接了下去。正视着他。“你怎么知道鸵鸵临终的情况?”
“事后我去了袁家,再见到鸵鸵的父母… ”他哽塞着:“我喊他们爸爸、妈妈。”我 点点头,深刻了解到袁氏夫妇失去爱女的悲痛,以及那份爱屋及乌的感情,他们一定体会到 韩青那淌着血的心灵,和他们那淌着血的心灵是一样的。
“韩青,我们都不懂得死亡是什么。”我说:“不过,我想,鸵鸵假若死而有灵,一定 希望看到你振作起来,快乐起来,而不是看到你如此消沉。”“你懂得万念俱灰的意思 吗?”他问。
“哦,我懂。”他沉思了一下。忽然没头没脑又问了我一句:“你知道All Kinds of Everything那支歌吗?”
不等我回答,他开始用英文唱那支歌:
“万事万物,万事万物,都让我想起你——不由自主。”
他停住了。又抬头去看天花板,泪珠在眼中滚动。
“我不敢怨恨上帝,”他说:“我不敢怨恨命运!我只是不懂,这些事为什么发生在我 们身上。当年,我和鸵鸵逛来来百货公司,她在许愿池许了三个愿。为了我们三对。结果, 徐业平和方克梅散了!小伟淹死了,丁香进了疗养院。最后剩我们这一对,现在,连鸵鸵都 去了。三对!没有一对团圆!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人,都会死的,每个人都会 死!我没为对面的老婆婆哭,我没为太师母哭……可是,我为小伟哭,我为鸵鸵背我为我们 这一代的懵懂无知而哭!”
他越说越激动,他不介意在我面前落泪了。我也不介意在他面前含泪了。“韩青,”我 停了很久才说:“对生命而言,我们每个人都是懵懂无知的。”“你了解生命吗?”他问。
我沉思良久,摇了摇头。
“我从不敢说我了解任何事,”我从心底深处说出来,坦白、诚恳的看着韩青。“更不 要谈‘生命’这么大的题目。我只觉得,生命本身可能是个悲剧,在自己没有要求生命的时 候就糊糊涂涂的来了,在不愿意走的时候又糊糊涂涂的走了。不过,”我加重了语气:“人 在活着的时候,总该好妹活着,不为自己,而为那些爱你的人!因为,死亡留下来的悲哀不 属于自己,而属于那些还活着还深爱着自己的人!例如你和鸵鸵!鸵鸵已无知觉,你却如此 痛苦着!”
他吸着,沉思着。他的思想常在转移,从这个时空,转入另一个时空,从这个话题,转 向另一个话题,忽然间,他又问我:“你会写这个故事吗?”
我想了想。“不知道。”我看着手边的稿纸。“这故事给我的感觉很凄凉,很久以来, 我就在避免写悲剧!那——对我本身而言,是件很残忍的事,因为我会陷进去。尤其,你们 这故事……其实,你们的故事很单纯,并不曲折,写出来能不能写得好,我没把握。而 且……”我沉思着,忽然反问他一句:“你看过我的小说吗?”“看过,就因为看过,才会 来找你。总觉得,只有你才能那么深刻的体会爱情。”我勉强的笑了笑。“总算,也有人来 帮我证实,什么是爱情。你知道,在我的作品中,这是经常被攻击的一点,很多人说,我笔 下的爱情全是杜撰的。还有很多人说,我把爱情写得太美、太强烈,所以不写实。这些年 来,我已经很疲倦去和别人争辩有关爱情的存在与否。而你,又给了我这么一个强烈深切的 爱情故事。”“是。”他看着我,眼光热切。“我不止亲自来向你述说,而且,我连我的日 记——一个最真实的我,好的,坏的,各方面,都呈现在你面前。还有那些信,我能保存我 写给鸵鸵的信,是因为方克梅的关系。鸵鸵不敢把信拿回家,都存在小方那儿。鸵鸵死后, 小方把它们都交给了我。所以,你有我们双方面的资料。”我仍然犹豫着。“你还有什么顾 忌吗?”他问。
“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我说,试着要让他了解我的困难和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