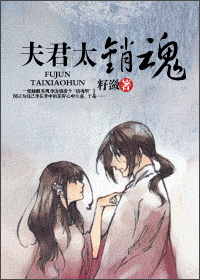匆匆,太匆匆-第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匆匆,太匆匆 4
韩青始终不能忘怀和鸵鸵初吻时,那种天地俱变,山河震动,世界全消,时间停驻的感 觉。这感觉如此强烈,如此带着巨大的震撼力,是让他自己都感到惊奇的。原来小说家笔下 的“吻”是真的!原来“一吻定江山”也是真的!有好些天,他陶醉在这初吻的激情里。可 是,当有一天他问她,她对那初吻的感觉如何时,她却睁大了她那对黑白分明的眸子,坦率 的,毫不保留的说:“你要听真话还是听假话?”
废话!韩青心想。他最怕袁嘉珮说这种话,这表示那答案并不见得好听。“当然要听真 的!”他也答了句废话。
“那么,我告诉你。”她歪着头回忆了一下,那模样又可爱又妩媚又温柔又动人。那样 子就恨不得让人再吻她一下,可是,当时他们正走在大街上,他总不便于在大庭广众下吻她 吧!她把目光从人潮中拉回来,落在他脸上,她的面容很正经,很诚实。“你吻我耳朵的时 候,我只觉得好痒好痒,除了好痒,什么感觉都没有。等你吻到我嘴唇时……嗯,别生气, 是你要问的哦……我有一刹那没什么思想,然后,我心里就喊了句:糟糕!怎么被他吻去 了!糟糕!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糟糕,怎么不觉得romantic?糟糕!被他吻去了是不是 就表示我以后就该只属于他一个人了?… ”
“停!”他叫停。心里是打翻了一百二十种调味瓶,简直不是滋味到了极点。世界上还 能有更扫兴的事吗?当你正吻得昏天黑地,灵魂儿飞入云霄的当儿,对方心里想的是一连串 的“糟糕”。他望着她,她脸上那片坦荡档的真实使他更加泄气,鸵鸵,你为什么不撒一点 小谎,让对方心里好受一点呢?鸵鸵,你这个让人恨得牙痒痒的小东西!
袁嘉珮看看他,他们在西门町的人潮里逛着,他心里生着闷气,不想表现出来,失意的 感觉比生气多。他在想,他以后不会再吻她,除非他有把握她能和他进入同一境界的时候。 鸵鸵,一个“小东西”而已,怎么会让他这样神魂失据,不可自拔!“哎哟!糟糕!”她忽 然叫了一声,用手捂着耳朵。
“怎么了?”他吓了一跳,盯着她,她脸色有些儿怪异,眼睛直直的。“我的耳朵又痒 了!”她笑起来,说。
“这可与我无关吧?”他瞪她:“我碰都没碰你!”
“你难道没听说过,当有人心里在骂你的时候,你的耳朵就会痒?”“嗯,哼,哈!” 他一连用了三个虚字。“我只听说,如果有人正想念着你的时候,你的耳朵就会痒。”
“是吗?”她笑着。“是的。”他也笑着。
她快活的扬扬头,用手掠掠头发,那姿态好潇洒。她第一次主动把手臂插进他手腕中, 与他挽臂而行,就这样一个小动作,居然也让韩青一阵心跳。
几天后,他买了一张小卡片,卡片正面画着个抱着朵小花的熊宝宝,竖着耳朵直摇头。 卡片上的大字印着:
“最近耳朵可曾痒痒?”
下面印了行小字:
“有个人正惦记着你呢!”
他在小卡片后面写了几句话:
“鸵鸵:耳朵近日作怪,痒得发奇,想必是你。今夜又痒,跑出去买了此卡,稍好。
青“
他把卡片寄给了她。他没想到,以后,耳朵痒痒变成了他们彼此取笑,彼此安慰,彼此 表达情衷的一种方式。而且,也在他们后赖的感情生涯中,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
十一月底,天气很凉了。
这天是星期天,难得的,不管上夜校还是上日校的人,全体放假,于是,不约而同的, 大家都聚集到韩青的小屋里来了。徐业平带着方克梅,吴天威还是打光杆,徐业平那正念新 埔工专,刚满十八岁的弟弟徐业伟也带着个小女友来了。徐业伟和他哥哥一样,会玩,会 闹,会疯,会笑,浑身充满了用不完的活力。他还是个运动好手,肌肉结实,田径场上,拿 过不少奖牌奖杯。游泳池里,不论蛙式、自由式、仰式… 都得过冠军。他自己总说:“我前辈子一定是条鱼,投胎人间的。因为没有人比我更爱水,更爱海。”其实,徐业 伟的优点还很多,他能唱,能弹吉他,还会打鼓。这天,徐业伟不但带来了他的小女友,还 带来了一面手鼓。徐业伟介绍他的女友,只是简单的一句话:“叫她丁香。”“姓丁名香吗?”袁嘉珮好奇地问。“这名字取得真不错!”
“不是!”徐业伟敲着他的手鼓,发出很有节奏的“砰砰,砰砰砰!”的声音,像海浪 敲击着岩石的音籁。“她既不姓丁,也不叫香,只因为她长得娇娇小小,我就叫她丁香,你 们大家也叫她丁香就对了!”丁香真的很娇小,身高大约才只有一五五公分左右,站在又高 又壮的徐业伟身边,真像个小香扇坠儿。丁香,这绰号取得也很能达意。她并不很美,但是 好爱笑,笑起来又好甜好甜,她的声音清脆轻柔,像风铃敲起来的叮当声响。她好年轻,大 概只有十六、七岁。可是,她对徐业伟已经毫无避讳,就像小鸟依人般依偎着他,用崇拜的 眼光看他,当他打鼓时,为他擦汗,当他高歌时,为他鼓掌,当他长篇大论时,为他当听 众。韩青有些羡慕他们。虽然,他也一度想过,现在这代的年轻人都太早熟了,也太随便 了,男女关系都开始得太早了。于是,他们生命里往往会失去一段时间——少年期。像他自 己,好像就没有少年期。他是从童年直接跳进青年期的。他的少年时代,全在功课书本的压 力下度过了。至于他的童年,不,他也几乎没有童年… 摇摇头,他狠命摇掉了一些回忆, 定睛看徐业伟和丁香,他们亲呢着,徐业伟揉着丁香的一头短发,把它揉得乱蓬蓬的,丁香 只是笑,笑着躲他,也笑着不躲他。唉!他们是两个孩子,两个不知人间忧苦的孩子!至于 自己呢?他悄眼看袁嘉珮,正好袁嘉珮也悄眼看他,两人目光一接触,他的心陡然一跳, 噢,鸵鸵!他心中低唤,我何来自己,我的自己已经缠绕到你身上去了。
鸵鸵会有同感吗?他再不敢这样想了。自从鸵鸵坦白谈过“接吻”的感觉之后,他再也 不敢去“自作多情”了。许多时候,他都认为不太了解她,她像个可爱的小谜语,永远诱惑 他去解它,也永远解不透它。像现在,当徐业伟和丁香亲热着,当方克梅和徐业平也互搂着 腰肢,快乐的依偎着。… 鸵鸵却离他好远,她站在一边,笑着,看着,欣赏着… 她眼底 有每一个人,包括乖僻的吴天威,包括被他们的笑闹声引来而加入的隔壁邻居吉他王。
是的,吉他王一来,房里更热闹了。
他们凑出钱来,买了一些啤酒(怎么搞的,那时大家都穷得惨兮兮),女孩子们喝香吉 士。他们高谈阔论过,辩论过,大家都损吴天威,因为他总交不上女朋友,吴天威乾了一罐 啤酒,大发豪语:“总有一天,我会把我的女朋友带到你们面前来,让你们都吓一跳!” “怎么?”徐业伟挑着眉说:“是个母夜叉啊?否则怎会把我们吓一跳?”大家哄然大笑 着,徐业伟一面笑,还一面“砰排排,砰排排”的击鼓助兴,丁香笑得滚到了徐业伟怀里, 方克梅忘形的吻了徐业平的面颊,徐业平捉住她的下巴,在她嘴上狠狠的亲了一下。徐业伟 疯狂鼓掌,大喊安可。哇,这疯疯癫癫的徐家兄弟。然后,吉他王开始弹吉他,徐业平不甘 寂寞,也把韩青那把生锈的破吉他拿起来,他们合奏起来,多美妙的音乐啊!他们奏着一些 校园民歌,徐业伟打着鼓,他们唱起来了。他们唱“如果”:
“如果你是朝露,我愿是那小草,如果你是那片云,我愿是那小雨,如果你是那海,我愿是那沙滩… ”
他们又唱“下着小雨的湖畔”,特别强调的大唱其中最可爱的两句:
“虽然我俩未曾许下过诺言,真情永远不变… ”
唱这两句时,方克梅和徐业平痴痴相望,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小丁香把脑袋靠在徐 业伟的肩上,一脸的陶醉与幸福。韩青和袁嘉珮坐在地板上,他悄悄伸手去握她的手,她面 颊红润着,被欢乐感染了,她笑着,一任他握紧挝挝挝挝她的手。噢,谢谢你!他心中低 语:谢谢你让我握你的手,谢谢你坐在我身边,谢谢你的存在,谢谢你的一切。鸵鸵,谢谢 你。他们继续唱着,唱“兰花草”,唱“捉泥鳅”,唱“小溪”:
“别问我来自何方,别问我流向何处;你有你的前途,我有我的归路… ”
这支歌不太好,他们又唱别的了,唱“橄榄树”,唱“让我们看云去”。最后,他们都 有了酒意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大唱特唱起一支歌来:
“匆匆,太匆匆,今朝有酒今朝醉,昨夜星辰昨夜风!
匆匆,太匆匆,春归何处无人问,夏去秋来又到冬!
匆匆,太匆匆,年华不为少年留,我歌我笑如梦中!
匆匆,太匆匆,潮来潮去无休止,转眼几度夕阳红!
匆匆,太匆匆,我欲乘风飞去,伸手抓住匆匆!
匆匆,太匆匆,我欲向前飞奔,双手挽住匆匆!
匆匆,太匆匆,我欲望空呐喊,高声留住匆匆!
匆匆,别太匆匆!匆匆,别太匆匆!“
是“少年不识愁滋味”吗?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吗?是知道今天不会为明天留住吗? 是预感将来的茫然,是对未来的难以信任吗?他们唱得有些伤感起来了。韩青紧挝着鸵鸵的 手,眼眶莫名其妙的湿了。他心里只在重复着那歌词的最后两句:
“匆匆,别太匆匆!匆匆,别太匆匆!”
匆匆,太匆匆 5
方克梅特意来找韩青谈话,是那年冬天的一个早上,华冈的风特别大,天气特别冷,连 那条通往“世外桃源”的小径都冻硬了,路两边的杂草都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方克梅和徐业 平两个,一直不停的在说话。韩青踩在那小径上,听着远远的瀑布声,听着穿梭而过的风 声,听着小溪的淙淙,只觉得冷,览览览。什么都冷,什么都冻僵了,什么都凝固了。包括 感情和思想。“韩青,你别怪我,”方克梅好心好意的说:“介绍你和袁嘉珮认识的时候, 我并不知道你会一头栽进去,就这样正经八百的认起真来了,你以前和宝贝,和邱家玉,和 小翠都没认真过,这一次是怎么了?”
“我告诉你,”徐业平接口:“男子汉大丈夫,交女朋友要潇洒一点,拿得起,放得 下,聚则聚,散则散… 这样才够男子气!”“嗬,徐业平!”方克梅一个字一个字的怪叫 着:“你是拿得起,放得下,聚则聚,散则散,够男子气的大丈夫啊!你是吗?是 吗?… ”“不膊膊!我不是#####”徐业平慌忙对方克梅竖了白旗,举双手作投降 状。“我自从遇到你方姑娘,就拿得起,放不下啦,男子汉不敢当,大丈夫吗——总还算 吧!”他问到方克梅脸上去。“等你嫁给我,当我的小妻子的时候,我算不算你的大丈夫 呢?”“要命!”方克梅又笑又骂又羞又喜,在徐业平肩上狠狠捶了一拳。差点把徐业平打 到路边的小溪里去。徐业平大叫:“救命,有人要谋杀亲夫!”
韩青看着他们,他们是郑而重之的来找他“谈话”的,现在却自顾自的在那儿打情骂俏 起来了。韩青一个人往前走,孤独,构构构构构。冬天,你怎么不能冻死孤独?他埋着头走 着,还不太敢相信方克梅告诉他的:“袁嘉珮另外还有男朋友,是海洋学院的,认识快一年了,他们始终有来往。所以,你 千万不要对袁嘉珮太死心眼儿!”
不是真的,他想。是真的,他知道。
现在知道她为什么若即若离了,现在知道她为什么忽热忽冷了,现在知道她为什么在接 吻时会想到一连串的“糟糕”了。不知那海洋学院的有没有吻过她?当时她想些什么?
“喂!韩青,走慢一点!”方克梅和徐业平追了过来。他们来到了那块豁然开朗的山 谷,有小树,有野花,有岩石,有草原…只是,都冻得僵僵的。
“你真的‘爱上’袁嘉珮了吗?”方克梅恳切的问:“会不会和宝贝一样,三分钟热 度,过去了就过去了?你的历史不太会让人相信你是痴情人物。你知道,袁嘉珮对你根本有 些害怕…”“她对你说的吗?”他终于开了口,盯着方克梅。“是她要你和我谈的,是 吧?”“哦,这个…”方克梅嗫嚅着。
“是她要你来转告我,要我离开她远一点,是不是?是她要你来通知我,我该退出了, 是不是?”
“噢,她不是这意思,”方克梅急急的说:“她只觉得你太热情了,她有些吃不消。而 且,她一直很不稳定,她是个非常情绪化的女孩。你相不相信,大一的时候,有个政大的学 生,只因为打电动玩具打得一级棒,她就对人家崇拜得要死!她就是这样的,她说她觉得自 己太善变了,她好怕好怕…会伤害你!”韩青走到一棵树下面,坐下来,用双手抱住膝, 把下巴搁在膝盖上,呆呆的看着前面一支摇乙曳曳的芦苇。
“喂!喂!”徐业平跳着脚,呵着手。“这儿是他妈的冷!咱们回学校去喝杯热咖啡 吧!”
“你们去,我在这儿坐一下。”韩青头也不抬的说。
“韩青!”方克梅嚷着:“把自己冻病了,也不见得能追到袁嘉珮呀!”“我不冷。” 他咬着牙“我只想一个人静一静。”
“那么,你在这儿静吧!”徐业平敲敲他的肩,忽然在他耳边低声问:“你什么时候下 山?”
“不知道。”他闷声的。
“那么,”徐业平耳语着:“你房门钥匙借我,我用完了会把钥匙放在老地方。”他一 语不发的掏出钥匙,塞进徐业平手里。这是老花样了。
徐业平再敲敲他的肩,大声说:“别想不通了去跳悬崖啊!这可不是世界末日,再说嘛,袁嘉珮也没有拒绝你呀,如果 没有一两个情敌来竞争一下,说不定还不够刺激呢!”“唉鞍鞍,”方克梅又“唉”起来 了。“你是不是在暗示我什么,想找点刺激吗?”“不膊膊!”徐业平又打躬又作揖。“我 跟他说的话与你无关,别尽搅局好不好?”“不搅局,”方克梅说:“如果你们两个男生要 说悄悄话,我退到一边去。”她真的退得好远好远。
“韩青,”徐业平脸色放正经了,关怀的,友情的、严肃的注视着他,不开玩笑了,他 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