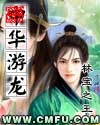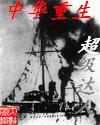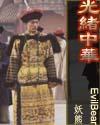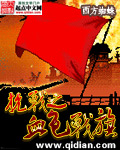血色中华-第2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车轮滚过凹凸不平的石板路,颠簸中张绍华留意到了何复生的情绪变化,知道这孩子和赵慧亲厚,就温言道:“无论佛兰死不死,我们肯定要和法国人打一场硬仗的,佛兰,他的作用不在于与法国人的最终和谈,而在于我们要用他来拖时间。”
他心中也挺惦记着赵慧,很愿意她能尽快来到河内,但路上动荡不安……算了,还是再等等吧……
张绍华没有把话说尽,他必须用佛兰来拖延来自南方的法军,通过外交斡旋来避免腹背受敌的危机,因为他们面对的情况很危险,中越兵团并非完全在他的掌握之下,彼此是为了各自的利益才走到一起,拧成一股劲,由于他和中华村几大首脑的苦心布置才旗开得胜,胜利鼓舞着长期受压迫的越南人,甚至作为盟军加入的老挝人。
然而兵贵士气,面对强大的敌人,这些缺乏严格训练的游兵散勇只怕经不起考验,一旦遭受重大打击,溃散起来肯定比散沙还快。
从统领全局的角度出发,所有的军事机要都要通过他和萧庆云、铁坤的手,经过慎重过滤后才适当地分下去,那些越南老挝同盟军该知道的让他们知道,不该知道的永远也不会知道,这样对彼此的军心士气都有很大好处。
利用佛兰来挡住北上的法军,他要当作一场戏来做,还要高调地来唱,让盟军和占领区的百姓们都知道这件事,把己方已经掌握主动权的局面深入民心,对局势的稳定有百利而无一害!
他们很快来到河内圣玛丽教会医院,该医院正为战后大批涌到的伤者而忙碌,到处可见伤兵患者躺的躺,挨的挨,医生护士及修女们忙得脚不点地团团转。
张绍华首先把佛兰夫人及其一对儿女带到外科手术室对面的休息室,让她们亲眼看到三十多名中越兵团的小伙子们坐在那里排队轮候验血抽血,几个护士在那里忙乎,看完了,还让外科主任克里斯特和她直接交待了佛兰的伤势和手术进度。
和其他在战役中受伤的各国士兵们对比,佛兰不算伤得太重,只要有足够的血液保证手术能顺利进行,如无意外应该不至于丢掉性命。
在得知丈夫还没死,而且医院确实从佛兰被送到医院开始奋战至今,佛兰夫人无话可说,只好坐在手术室外搂着小女儿等待,她那十一岁的儿子很不耐烦地用鞋跟把椅子踢得“笃笃”响。
克里斯特看看站在一旁的张绍华,又看看在分散在手术室四面八方戒严的士兵们,心中很替他们的总督不值,还未能接受江山易主的现实。
张绍华很有礼貌地和克里斯特说:“感谢贵院大力支持,鄙人代表全体官兵向您们致谢!”
克里斯特很敷衍地和张绍华握了握手,颇为冷淡地说:“能为总督大人以及张大人效劳,是我们的荣幸。”
张绍华不去计较对方的态度,直接提出要求:“佛兰手术后,请贵院为佛兰夫人及孩子们安排一个独立单间,夫人要留下来亲自照顾丈夫,鄙人很欣赏夫人这样的法国女性。”当然了,让士兵看守着也是很有必要的。
佛兰夫人抬起眼向张绍华投去诧异的目光,茫茫然竟觉得委屈莫名,如果说他们法国人没有错,那么这些反抗入侵的亚洲人似乎也没有错……那么,到底错的是谁?!假如这个世界没有公义可言,难道连是非都不存在?
她无法理清思绪,这个东方男人的所作所为完全颠覆了她的世界。
最后,张绍华走到她们母子跟前,真诚地说:“夫人,您的丈夫一定可以很快康复,夫人和孩子们有什么需要随时提出。”
佛兰夫人被他深邃善意的目光笼罩着,不知不觉放开小女儿站起来,拉起裙裾很正规地行了个屈膝礼,低声说:“鲁沙代表总督感谢先生的好意!”
张绍华从容地笑了笑:“鲁沙,很美丽的名字!”
佛兰夫人无法揣测对方为何忽然冒出这么一句话来,但从小所受的教育令她很自然地作出条件反射——低下头,首次露出女人的矜持,喃喃道:“谢谢!”
在她的心中,这是一个高贵淑女必须的礼节,但其他人听不到他们的对话,只看到张绍华像个国王般傲然立在那里,在接受总督夫人谦卑的拜见……所有人都不知不觉掉进了张绍华刻意营造的氛围里,克里斯特和其他在场的人都很惊讶地看着这一幕,尤其是那些法国人和越南人,大家都不能理解为何永远高高在上的佛兰夫人会对这个华人如此恭敬!莫非……莫非……
这一幕经过很多目击者的口耳相传,立即在广大市民和士兵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大部分人开始对河内的新主人刮目相看,一个有能力有威信的强势新形象就这样逐步建立起来。
安排好这里的事情后,张绍华还特意到各个病房转了一圈,问明了伤兵们的大致情况才匆匆离开,因为萧庆云派人送来口讯,邱健在老街那边发来电报,说今天下午两点希望能和张绍华接通电话,他有要事必须和张绍华说。
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这是中越兵团占领河内的第一天。
张绍华等人赶回总督府时人群已经散去,河内城内外都相对平静,大部分人抱观望态度,虽然都不相信法国军队会就此罢休,但他们对进驻的军队印象还算良好,很多非法国籍的商人更因为安民告示上提到的减税减息等等新措施窃喜,暗暗希望这支军队能长期镇守河内。
张绍华一进门就闻到股炖肉的香味,驻守总督府的战士们在分批吃午餐,看到张绍华等人都纷纷和他们打招呼。
张绍华扫了一眼餐桌,看到大家在吃的是法式红酒炖牛扒,外带沙拉、面包、土豆等配菜和主食,大伙儿都吃得很高兴。
“复生,你和大勇都饿了,吃饭去吧!李佳,你也去。”他丢下这句话,自己却顾不上喝口水就大步穿过长廊,径直往通讯室走去。
推开大门,看到萧庆云正焦急地在房间内踱来踱去,小虎和几个通讯兵在那里折腾那几台电报机,以保持和其他部队的联系。
萧庆云抬头看到来人是张绍华,立即拉过他迫切地说:“团长,小邱那边很危急!敌人越来越多,他们顶不住了!还有,江河镇那边也发生多次遭遇战!”
为了保住胜利果实,不让刚被佛兰调离河内的法军反扑,因此根据他们定下的作战方针就是以太原、永安和福寿这三个镇为桩,坚决守住此三镇,并把三镇连成一线,一节节用重火力把法军往北逼,中途由越南游击队把法军切开,令其彼此无法呼应,从而逐渐消耗法军主力,一点点吃掉他们。
结果战线越烧越长,被打得晕头转向的法军只好不断往北撤,江河镇那片也受到波及,玄武队全体出动,徐林张龙等人把矿工们都发动起来,号召全体人员参加自卫战,气氛非常紧张!
第四十四章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今天可能是入夏以来最热的一日,正午的艳阳高挂,微风树荫带不来半丝凉意,通讯室内幸亏有良好的通风系统才不至于很闷热,但张绍华还是站在那里直冒汗,他随手脱下外衣扔在椅背上,提起衬衫扣子不停地上下抖动,让清风入怀,稍稍带来点凉意。
张绍华清楚了形势后,立即令萧庆云和留在中华村的铁坤等人联络,同时让通讯兵紧急和其他部队的首领联络,而小虎则受命在忙着和还在往回赶的刘平取得联络。刘平多次在中越边境往返,最后一次的目的地是云南四川的交界地。
临行前张绍华嘱咐他一定要随时和总部保持联络,但由于当时国内无线电报还非常落后,1934年(民国23年)5月泉州刚设立无线电台时,设备简陋,线路简单,只有泉州—福州、泉州—厦门、泉州—上海3条无线电路。就算是1936年,落后的西南西南一带根本谈不上民用无线通讯,因此他们约定刘平每到一个地方都尽快利用当地的有线电报或电话设备和总部联络。
关得紧紧的窗边有张深褐色的书桌,桌面上堆满凌乱的报纸书籍,张绍华走过去拔拉了几下,首先看到一小段被人用红笔圈着,翻译成法文的英文报纸报道:“蒋介石在控制贵州、云南后,下令云、贵两省的鸦片改经湖北外运,不再经过两广过境,广州对鸦片的贸易每年损失达六百万银圆。本年1月,广东陈济棠决定从本月起实行“樽节开支”,军官的俸薪减发4%到13%不等,全军各团的津贴金亦减到1000元……”
正好,这时通讯室内的收音机里在播放当天的新闻,听起来应该是国内广西电台的广播:
“今天,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广西省政府、中国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在省会南宁联合举行扩大纪念周。广西的党、政、军首脑,省党部全体职员,总司令部全体官佐,省政府各厅、处长和职员共数千人参加。集团军副总司令白崇禧在大会上发表反蒋抗日演讲……”
萧庆云背着他百忙中还来得及甩过来一句:“反蒋抗日了啊!”
张绍华脑海里的某扇记忆大门被撞开,他脱口而出:“阿萧,是‘六一事变!’”。
萧庆云捏着话筒在等中华村的通讯兵去把铁坤叫来,边回头茫然地反问:“什么‘六一事变’?儿童节事变?”他印象中只记得著名的“西安事变”快要来了,对儿童节事变完全没概念。
张绍华摇摇头,再紧张也笑起来:“兄弟,这是国民党时期,儿童节是四月四日!你居然连三毛流浪记都没看过!六一事变是两广的军阀联手起来反对蒋介石的……”这时,铁坤在那边接听电话了,萧庆云无心听下去,忙对着话筒:“喂!喂!铁坤,你们那边要稳住阵脚,同时派奇兵突出,多想办法把敌人往西边赶……”
张绍华闭上嘴留神聆听,他没想到自己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见证了鲜为人知的“六一事变”,此时,白崇禧悠扬的声音在空气中低回:“……广西这六年来惨淡经营,埋头苦干的目的,都是为了抗日。广西的自卫政策和三寓政策所准备的八百个团的民团后备队、八万名干部,就是准备抗日救国使用的。经数年来努力,虽未完成预定计划,但此刻已不容许我们再作准备了。我们要倾全省之力,发动民族革命斗争,实行李总司令提出的焦土抗战……”
李宗仁总司令、白崇禧副司令、还有广东的南天之王陈济棠、镇守云南的云南王龙云……这几个枭雄的名字和生平在张绍华心中浮浮沉沉,如果中华村这批人能在越南北部甚至老挝打下一片江山,将来迟早会和这些枭雄碰面,到时候,会是盟友还是敌人?
托从前爱读起点及铁血军事文的福,张绍华依稀记得这次“六一事变”是以失败告终的,陈济棠还被逼从香港逃到欧洲隐居,直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当年九月才被蒋介石召回国,命为国民政府委员会、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
这些人都是雄霸一方的铁腕人物,不过,目前还真是可能要摸摸龙云的老虎屁股……
思索中,还有一本小册子无意中引起张绍华的注意,他定睛看了看,嗯?《中国的西北角》这六个大字跳进他眼里,他走过去拿起小册子翻了翻,发现这是一本叫《中国的西北角》的通讯集,该书的作者就是日后被称为中国新闻记者第一人的范长江。
据扉页介绍范长江当年才二十五岁,就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进入西北,历时10个月,行程万里,小册子详尽地记录了他沿途的所见所闻,是一本非常精彩的西北考察录。
张绍华信手翻开就看到这么一段:“东北事变后,一般国人的眼光又注意到西北上来,从报章杂志宣传讨论,到要人的视察,专家的设计,以至于实际建设工作的进行。“开发西北”的声浪震动了一般国人的耳鼓。农林、牧畜、卫生、水利、几乎应有尽有。”
然而事实证明开发西北效果微乎其微,范长江为一路所见的西北人民的困苦生活而心酸,同时也为四川甘肃一带多不胜数的苛捐杂税及军队负担而震惊,可谓到了生生要把活人往死路上逼的程度。
他在报道中这样描述:农民除了缴纳各种苛捐杂税以外,还要应付忙于军队的负担:粮之外的油、盐、柴、炭、料、草……无不征发于民间,设有“兵站”专司其事。”重压之下的农民养成了一种“及时行乐”的风气,不管情形怎样,有了钱在手,那管借的高利贷也罢,卖家具的也罢,即刻要用也罢,他先到小饭馆去大吃一顿再说,宁可出了馆子再借高利,亦无所用其踌躇!粮价飞涨,而民间粮食日益耗尽,纵出高价,亦无处购买。故此辈苦力遂无以为生,相继成为饿蜉……
张绍华对这些情况还是知道的,这也是派刘平等人前往的原因之一。
在这本小册子里,张绍华第一次看到了国民党内部对红军长征的正式报道,范长江这样写道:“虽然当时并没有真正进入苏区,但在徐向前部在白石铺住过一两个月,街上遗留下许多和标语,最大的标语是:“武装拥护苏联!”大大的红墙的上面,差不多的民房集镇都有如此一个标语。”
看到这段,他不由自主地皱了皱眉,感觉上他一直对苏联没好感,丫当时支持中共红军,目的也是为了亚洲的控制权,难道还真是为了你们中华民族国富民安不成!
“张帅!刘平!找到刘平了!”小虎强压着激动低呼起来,唯恐骚扰了萧庆云和铁坤的重要对话。
刘平在电话那头听到张绍华的嗓音相当兴奋,两人连彼此问候都省了,生怕通讯会忽然中断,刘平一口气先把目前的状况汇报:“我们从黔桂一带招揽到很多人!那里的人听说有饭吃立即跟我们走人,什么人才都有!妈的,经过杨森的地盘,我们都分开走了,还是被这狗日的派兵一顿追杀……”
张绍华忙说:“我记得这小子不是刚从云南昭通调到西昌及川滇边区驻防了?你怎么遇上他的军队了!”
名将杨森原任国民党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陕边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