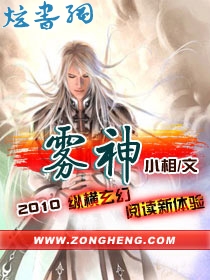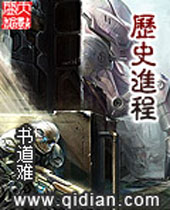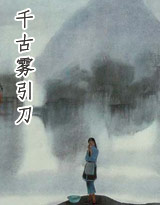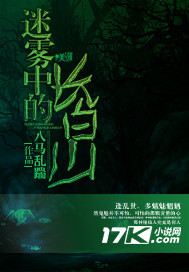历史的云雾-第3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有关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的史料迄今开放仍十分有限,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会议记录,中央社会部、中央组织部在这一时期的档案基本都没开放,但是某些权威机构利用上述资料编写了若干著作,包括具有工具书性质的论著,却为研究者了解毛在整风期间的活动提供了一些线索,若再配之以其他资料,有关情况的大致轮廓还是可以看出的。
《毛泽东年谱(1893…1949)》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一部重要著作,这部书在编辑方针上有非常明确的意识形态倾向性,凡与毛的官方解释有所不合的资料均已被年谱收入了大量珍贵史料,编者的态度也十分认真,《毛年谱》尽管在编排上存在着不够全面的缺点,但没有改写或伪造史料,而这种现象在80年代以前是普遍存在的,因此,《毛年谱》对研究者仍有重要价值。
陈教授在《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中运用了《毛年谱》中的资料,又是出于史家的谨慎,使用该书的频率较低,笔者完全理解陈教授的担心,但是过份的谨慎也会带来问题。
关于1943年9月开始的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以清算中共历史上“路线错误”为主题的政治局会议,在陈著中有很好的描述。毛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的讲话,为会议定下了调子。讲话要点,在《毛泽东年谱》中有简略的反映,其他资料如: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任弼时传》、《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等对此都有说明,所以可以肯定毛参加了1943年9月政治局会议,这个情况是可知的,并非是“不得而知”(陈著,页381)。
陈云和王稼祥是中共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此两人在党的核心层中的地位都曾发生过微妙的变化,陈著根据1943年3月20日政治局会议作出的几项组织决定,即陈云、王稼祥列名于新成立的中央组织委员会;王稼祥担任中央宣传委员会副书记,负责管理华北党政军民工作;陈云负责管理大后方工作—依此作出判断:陈云、王稼祥仍旧跻身于中共核心权力圈之中(陈著,页378)。但是,仅从这些任职名单上是看不出当时中共权力中枢变动的真实底蕴的,简言之,成立这个机构是毛泽东、刘少奇联手剥夺其他领导人权力的一项精心的安排。陈云、王稼祥进入这些机构后,其原有的权力已被剥夺大半。事实是,陈云长期担任的中央组织部部长一职在1943年初就被中予以中止,毛泽东派当时正蒙受他信任的彭真代理中组部部长。当时陈云确实身体虚弱,毛“关心”他的身体,叫他搬到自己居住的枣园休养,真正的原因乃是,陈云对当时正在兴起的审干、肃奸斗争有所怀疑,毛嫌陈云碍手碍脚,才让他“休息”。陈云尊重毛的权威,对自己境遇的变化毫无怨言,一年后,陈云复出,转任西北财经办事处领导,彭真正式就任中组部部长,从此,陈云从干部组织系统转业到财经系统。对陈云的高度党性,毛看在眼中,记在心里,1945年中共七大后,老政治局委员陈云再度进入政治局,这才真正“跻身于核心权力圈”。至于王稼祥,在1943年3月“跻身核心权力圈”则更非事实。虽然王稼祥多年来一直效忠于毛泽东,整风之初还十分活跃,积极批判昔日的朋友王明,但终因其历史上曾属于国际派大将,在1943年后逐渐受到冷遇。王稼祥不甘落伍,在1943年7月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但是“错误路线”代表人物的身份却长期湮没了他的这份功劳,发明“毛泽东思想”概念只能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刘少奇,而非王稼祥。在清算历史的1943…1945年,王稼祥终于病倒,虽与毛、刘等同住延安,却离“核心权力圈”不啻十万八千里。
陈著在谈到中共领袖在党内斗争的态度时提出一个看法,他说,“为了避免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的指责”,毛以外的中共领导人,“可能比毛泽东显得更残酷无情,刘、周、邓和彭德怀都免不了有这种问题,他们是等而上之者”(陈著,页9…10)。陈著在提出这一看法时,没有举出任何证据。笔者认为,就“党内斗争”的范围,在对其对手“残酷无情”方面,中共党内实无人能与毛比肩,毛可以打破常规,不受任何党纪的约束,一口气杀掉4500名红军(张国焘、夏曦大开杀戒是在毛之后),刘、周、邓、彭比毛“等而上之”一说,没有事实依据。
陈著中对中共建国后一些事件的叙述也有少量错误。1955年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发生的一次震动全局的政治事件,80年代后,围绕胡风案件,已出版若干著述,陈教授在撰写本书时都已注意并加以选择利用。然而陈著在分析胡风“三十万言书”时却断言,胡风没想到自己的言论根本便是和毛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背道而驰的(陈著,页658),其实胡风早在40年代中叶就知道自己与毛的文艺观存有差距,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已有不少文献提及,1947年中共在香港组织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评就完全证明了这一点,胡风对这其中的缘由是心知肚明的。去年公开的胡风1949年日记对此问题亦有相当详细的描述。另外,在反胡风及由此引起的肃反运动中,领导运动的组织是中央和各省、市级党委的十人小组,而非五人小组(陈著,页659)。
研究中共党史,若仅从文献字面加以理解或过份依赖于官方文字而缺少必要的分析,肯定也会造成理解上的误区。陈著说,反右派运动以后,整风继续进行,效果甚大(陈著,页674),这种说法来源于当年官方的出版物。事实上,反右以后,整风无疾而终,根本没有进行,仅仅从当年官方的文件和报章中是不可能看清真实情况的。陈著举出两例作为上述判断的依据:军队高级将领下连队当兵,扩大发行《参考消息》,但这些都不足以支持上述的判断。因为将军下连队当兵是大跃进期间“发扬共产主义精神”的产物,与反右以后继续开展整风,基本不搭界,况且军队系统在反右时也不是重点单位。至于扩大发行《参考消息》早在1956…1957年上半年就已实行了。
至于陈著中说1979年后中共宣布对右派分子实行了“平反”(陈著,页870),这也不确。官方的正式说法是“改正”,两词的涵义区别大也,所以史家在使用这些话语时,还需察微觉疑。
陈著中还有一些错误可能是过份依靠推测而未及详细研判史料而造成的。例如,陈著提到中共建国后,“虽然保持农村和城市的基本体制,例如保甲制度,但他们强调群众动员,以镇压反革命的名义,在基层展开逮捕,并开始初步改造工作”(陈著,页495),这样的描述总体上是符合当时社会情况的,但仍欠准确性。中共革命成功后,在城市第一步做的就是“城市民主改革”,在农村则是建立村组建制,通过这些措施,废除了保甲制等旧的社会基层结构,以后又经土改、镇反运动,完全建立起中共在城乡的基层社会结构,所以不存在一段时期内保留保甲制度的事实。
陈著中还提到建国初,中共将知识分子编入各种协会,“参加这种团体……有固定工资可领”(陈著,页688),事实也不是这样。当时被吸收进各协会的多为知识分子中的头面人物,并非所有知识分子都被编入各学会,被接纳进学会主要是一种政治荣誉,各学会并不给知识分子开工资,开工资的是他们各自所属的单位。另外,50年代初不少知识分子处于失业状态,以后或被政府安置就业,或通过参加革命大学,经过审查、重新分配工作才领到薪金。
陈著中提到刘少奇在1962年提出“三和一少”(陈著,页741),这是文革期间批判刘少奇的说辞,此主张实际上是由时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提出,与刘少奇无涉,尽管刘少奇倾向于接受王稼祥的意见,但版权归王而非刘。
陈著说,文革期间,“无论城市和农村,老百姓都基本无失业之虞”(陈著,页849),在城市,此说还可以成立(事实是当时城市也有少量无业人员),但在农村,就业、失业的概念似乎用不上。
又言,“70年代初,因为与美国恢复关系,中国大陆电视观众已经注意到中国比资本主义国家落后”(陈著,页850),实际情况并非如此。70年代初,中国电视节目和电视机的数量都极少,一般百姓根本看不到电视,而且电视上的所有节目都已作了彻底的政治过滤,从电视上,观众根本无法了解外部世界的情况。笔者在70年代初看过中国乒乓球队访日、访美的记录片,这两部记录片都在当时的电视台播映过,所有镜头都在比赛场内,几乎没有一个场外的镜头。
以国人而言,站在民间立场研究中共历史,确是一项艰难而寂寞的事业,治史尤如在攀登高山险岭,山间道路崎岖,云雾环绕,说不尽艰难苦涩,治史者只能小心翼翼,迂迂而行。然而这又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正如陈教授所言,凡我国人,怎能忽略中共革命这一本世纪最重要的现象呢?陈教授有感此问题之重要,特别有感于台湾岛内不少人有与大陆渐行渐远的心态,以一人之力,历时数年,完成这一扛鼎之作。陈教授秉持学术中立的立场,努力贴近中共革命,在宏观把握、专题分析、理论开掘等方面,皆获很高的成就。笔者这篇文章仅从史料运用的层面对陈著发表了一些意见,陈著的重大价值还有待专门论及,这是特别需要加以说明的。陈著中的若干缺失,与全书的成就相比,只是个别小疵,丝毫不影响该书的整体价值。走笔至此,深深感到,写信史难,写中共信史更难,转念又思之,难,固然是也,可是这其中何尝未另有一番研究乐趣呢?
注释:
'1'毛泽东:《总前委的一封答辩信》(1930年12月20日),载《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1985年),第14册,页634。
'2''3'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党史资料通讯》(1981年合订本),(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页89、144。
(本文发表于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1999年6月号)
叙事视角的多样性与当代史研究
——以50年代历史研究为例
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历史学有很大的变化与发展,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论述,对我们认识过去、吸取历史的经验,推动近现代史的研究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检视近二十年有关近现代史的叙述,不难发现它们大致分属于两种不同的类型: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上述两种叙事方式占据了近二十年近现代史叙事的主流地位。
所谓“革命叙事”产生于20至40年代,即左翼革命主义的史学,瞿秋白、张闻天、何干之等一批“有机化”或“组织化”的新知识分子,从苏联和日本左翼新理论中引入一系列概念和范畴,建构了左翼革命力量对中国的现实,过去,和未来的认识和解释的体系,其主要命题是论证中国近代革命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帝国主义侵略”、“封建主义压迫”、“阶级战争”、“革命”、“人民群众”、“工农专政”、“经济的决定因素”等成为这种叙事的基本主题。〈1〉〈2〉〈3〉
所谓“现代化叙事”最初产生于西方,八十年代初被介绍到中国。其主题是论证一百多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经验和教训,传统与现代、社会变迁、经济增长因素、制度创新与政治参与、公共空间和市民社会等成为观察,认识现代化问题的框架。〈4〉这两种叙事方式都从各自的角度对百年来的中国历史作出了概括和分析,在相当的程度上反映了历史进程的实质。
“革命叙事”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中第一次引入了苏联革命理论的基本概念,既强调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又强调变革生产关系,推翻旧有秩序的极端重要性;同时强调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国家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痛苦记忆,把中国近代看作是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中国,中国人民抵御西方侵略、扩张的反抗过程。在这个叙事框架中,突出彰显了反帝,底层造反,革命组织,革命领袖人物的思想和领导对推动历史前进的重大作用。
“现代化叙事”是叙事方式的全面转换,它将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置放于一个与世界紧密联系的视野下来认识,而这反映了一百多年来历史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即中国是在深受外国影响的背景下,展开现代化进程的。“现代化叙事”也把100多年来的中国历史置放于社会变迁的大过程中,通过对现代化动力、范围、速度、现代化的主体与客体等的研究来展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各层面相。这种从八十年代引入的叙事方式对现时中国的改革与开放有直接的启示作用。
然而这两种叙事方式都各有其不足:在“现代化叙事”中,中国内部的因素经常会被不经意地忽略,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具有普适性;但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更有其特殊性,从西方社会发展的经验中产生的某些概念,不一定能涵盖和解释中国社会的复杂性。
与“现代化叙事”相比较,“革命叙事”对我国历史学的影响更大,在长达几十年中,它是占绝对支配地位的主流叙述,至今仍有广泛的影响。“革命叙事”产生于革命斗争的年代,具有强烈的思想政治动员色彩,在革命胜利之后,如何将这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叙述和深厚的学术性加以有机融合,是一个新的紧迫的课题,勿庸置疑,史学界在“融合”方面曾取得重要的成就,但遗憾的是,从50年代中后期开始,“革命叙事”就逐渐走向僵化和教条主义。在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中共党史研究中,形成了某种根深蒂固的传统,阻滞了学术性研究的展开和深入。
“革命叙事”逐渐教条化是和它过分追求“宏大叙述”而紧密联系的。反映在传统的中国近现代史和党史研究领域,“宏大叙述”的基本特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