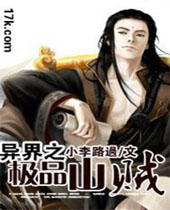怒海争锋之极地征伐-第1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感到担心。当然这首先是因为缺水,但也是因为进程缓慢。他了解“诺尔福克”号,而且他在“康斯替图欣”号上见过许多美国军官,在波士顿当战俘的时候也见过不少。他知道,要是“诺尔福克”号是由他们中间的哪一位指挥的,它就会在不过度损耗桅杆和索具的前提下,尽快地向南航行。它甚至可能已经弥补了被耽误的一个月时间,在他之前就驶过了圣洛克角。舰上的人们也让他担心。“惊奇”人已经接纳了直布罗陀的疯子们,对待他们很和蔼,帮他们切肉,疯子们听不明白时,还在他们耳边大声吼叫;不过,尽管“惊奇”人和“保卫者”人在一起经受了繁重的拖船劳动,尽管他对值班岗哨的安排进行了修改,“惊奇”人还是不能接纳大多数“保卫者”人。几乎所有的惩罚,都是由于双方打架而引起的。杰克怀着焦虑的心情,期待最终穿过赤道那一天的到来;在传统的粗野嬉闹中,恶意会现出丑陋的原形。他知道以前就有过不受欢迎的人被弄成残废的事情。有个人在恶作剧当中还真的被淹死了。那是杰克在“富米达布尔”号上当航行官助手时发生过的事情。况且由于酷热中持续的劳作,由于质量不好的伙食,大家的脾气变得非常恶劣。这又让杰克的焦虑增加了几分。当然,作为上帝之下唯一的主宰,他可以禁止在穿越赤道时举行传统的仪式,但指挥一艘以这种方式治理的军舰,他会感到羞愧。
再者,他感到军舰的氛围中有某种东西,某种他还无法确定的东西。从受雇的机遇来说,杰克一直是幸运的,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海上度过,因此和大多数与他年资相当的军官们相比,他和军舰官兵相处的经验更多;而且他的经验还更加全面,因为一个性情暴躁的舰长曾经在好望角把候补生奥布雷先生降了级,把他转成桅前的普通水兵,让他和其他普通水兵一起生活,一起吃,睡,劳动。这段经历,让他谙熟了水兵的做派和情绪,熟悉了他们的表情、手势和沉默的含义;而现在他肯定舰上发生了某种事情,某种虽然掩藏着,但大家都明白的事情。可以肯定,那件事既不是密谋兵变,也不是豪赌。他在几艘捕获赏金丰富的军舰上见到过豪赌,而“惊奇”人现在却几乎连一只山羊也没有;不过军舰上有某种激动,有某种遮遮掩掩,而兵变或者豪赌,本来也可能有这样的特性。
他的感觉很对。除了舰长,除了随军教士,当然还除了军械官,舰上所有人都知道这某件事。在一艘拥挤的军舰上,要私密地进行任何事情都是非常困难的,而所有人都知道侯隆先生和荷纳太太关系暖昧。对于从事这桩冒险事业,他所处的位置很理想,因为他的吊床和候补生们挂在一起,而军械官的王国,也就是荷纳太太照看候补生的地方,就在附近。军舰上很少有其他人可以在这些地方出入而不激起一些议论,现在侯隆既然已经差不多喂饱,他就充分地利用了自己的机会。
大家普遍认为,他过于充分地利用了机会;大家还觉得,在一个谨慎的开端之后,他变得过于自信了;大家觉得他马上就会挨揍了,伙计,狠狠地挨一顿揍了。侯隆不会欺负水兵,也不会去惩罚他们,所以大家丝毫也不主动地厌恶他,但因为他又算不上是个水兵,他也不受人尊敬;再说,虽说他暂时运气很好,虽说他的好运气很令人嫉妒,但总有可能他是个约拿。对全船的人来说,他一直是个陌生人。荷纳也差不多一样,他阴沉的脾气和潜在的凶猛,让他在舰上没有朋友,尽管从他自己那方面看,做为一个干练的军需官他是受人尊敬的,做为一个万一被触犯就很难对付的杂种,他又是令人害怕的。
所以,在把军舰拉出变风带的劳作间隙,现在大家可以怀着最强烈的兴趣,观察这两个陌生人了。在着迷的旁观者们看来,随着这对情侣的谨慎变得越来越松懈,爆炸肯定在变得越来越近。但这些猜测,虽然自由地交流着,却从来也没有传到大舱里去;而在下级军官室,在随军教士在场的时候,猜测也会暂时被抑制住。
因此,虽然从迎风面船舷转折处的旁边,从他通常的位置上,杰克常常观察到心照不宣的表情,但对这些表情背后的特定理由,他一直毫无所知;不过,即使他知道其中的理由,在狐鲣出现的时候,他还是会命令所有小艇下水的。黎明时分,甲板上发现了几十条飞鱼,而等太阳升起时,可以看见它们的追逐者在水面之下大群大群地掠过。水兵们驾着小艇,以极大的热忱,奋力挥动起渔网和渔绳,拉上来几大堆的鱼,这种鱼不需要在宝贵的淡水中浸泡就可以吃;而且正如斯蒂芬对马丁评论的那样,狐鲣,就像它的近亲大金枪鱼一样,不仅是一种热血鱼类,而且是爱神维纳斯的促进者。
除了兰姆太太,船上所有人都尽可能让自己填饱了狐鲣,在盛宴之后,侯隆可爱的六月玫瑰从下层传来,他现在下班了。军械官走上甲板,去修理船首楼一门大口径短炮。歌声突然中断了。在船首楼上,军械官拍了拍口袋,发现自己没带手帕,于是又开始走回自己的卧舱。
幸亏全体船员集合的哨子声响了起来,这对情侣才得救了。这是因为,在东北方向的远处,出现了一片深紫色的浓云,闪电正在云层下面闪烁着。杰克认定,这片浓云很可能会把一场正在转向的暴风的边缘带给他们,所以还不如把所有的上桅杆降下来,尽管几个小时以前,为了追赶飞鱼柔风最后的喘息,上桅杆才刚刚扯起来。
他这样做其实很有好处,暴风转向的角度,比他和普林斯或者掌帆长所预期的,要更加陡急。在经过各种变化之后,它越过宁静的海面,嘶嘶地呼啸着朝左舷后方飞来,它是一条以每小时三十五英里推进的白线,它的背后是浓密的黑暗,三只灰色的小鸟在它前沿来回穿插。它带着不断增强的吼啸声,猛然砸向军舰,立刻把它遮盖起来。斯蒂芬和马丁两个人,想用望远镜辨认那几只灰色小鸟,于是粗心地松开了扶手,暴风立刻把他们抛射到背风面的排水孔里。还没等好心的水兵们把他们拉起来,整个天空就变成一团咆哮的雨,这团雨温暖、浓厚,夹杂着巨大的雨滴和粉碎的水沫,令他们在爬上倾斜的甲板时,几乎无法呼吸,也令所有的排水孔狂喷大水。“对不起,你在说什么?”马丁在全能的、无所不在的轰鸣中喊道。
“我只是在朝医生喊‘屠夫’。”杰克对着他的耳朵吼道。“在海上,有人摔倒的时候,我们都这么说的。来,抓住桅脚栏杆。”
有十分钟时间,“惊奇”号在缩起帆篷的前桅中桅帆下飞速行驶。风势稍微减弱后,他们马上开始铺展各种各样为收集雨水而准备的帆布,并且抬出了很多琵琶桶。可是很不幸,大雨毫无价值地淹没甲板之后,就几乎耗尽了自己。人们把大桅最高第二帆张在船首楼的支柱之间,帆上还用炮弹压着,总算积攒了些雨水,但沉迷于自己才智的侯隆先生解开了错误的索结,又损失了其中的一部分。
尽管如此,在暴雨持续的短暂时间里,他们还是积存了够用八天的水,而且水还非常纯净。舰上的女人们,甚至连几乎瘫痪的兰姆太太,都把所有能找到的小盆小桶全装满了——她们的小件衣物已经浸泡在水里。
更令人宽慰的是,紧跟着暴风,吹来了一股稳定的柔风。或许这就是东南贸易风最初的气息。
不过,这些好处当然是要付出代价的。太阳烤晒的甲板极其可厌地漏起了水,“惊奇”号上上下下(尽管兴高采烈地稳健行驶着)回响起滴水的声音,就连最底层甲板和储舱本身也在漏着水。除了衬铁皮的面包房,漏水把所有储藏室、所有卧舱、这些卧舱里所有吊床都弄得湿淋淋的;而且还没等到傍晚的太阳以突兀的热带方式落下去,囚禁在舱内的热空气就已经充满了霉味。书上、衣服上、鞋子上、海洋标本上、便携肉汤上、当然还有每个人都睡在其下的粗大横梁上,都长出了霉,长出了蓝色、绿色、有时候还是斑驳的灰色的霉。除了舰长,每个人时不时都会在那些横梁上撞头,这倒不是因为杰克·奥布雷比别人都矮小——事实上他身高六英尺还多——而是因为他的卧舱有更大的净空。或者更确切地说,他的那些卧舱,因为他有三个舱:舰长专舱在左舷,其中包括后桅的基座部分和一门三十二磅大口径短炮,除非客人超过四五个,他通常是在那儿吃饭的;他睡觉的舱房在右舷一侧;然后紧靠船尾,是他的豪华大舱,它横跨整艘军舰,被精美的、带弧度的、向内倾斜的七扇船尾窗照亮着,是舰上最通风、光线最好、最令人向往的地方,也是基里克的王国,它被不停地用沙擦着,用水洗着、刮着、磨着,永远散发着蜂蜡、新鲜海水和干净油漆的味道。
“也许我们今晚可以来点音乐?”斯蒂芬从他散发着恶臭的狗洞里上来,建议道。
“噢,上帝,不行。”杰克马上叫道。“只要这迷人的微风持续下去,我就得去驾船,我得呆在甲板上。”
“不管你在不在甲板上,它自己肯定也会航行的。看在老天的分上,你有这么能干的军官,等轮到他们负责值班岗,他们不管怎样都会熬夜的。”
“你显然说得对,”杰克说,“可是在这种前景微妙的情况下,舰长的责任是呆在甲板上,用他意志和腹肌的合力来催促军舰。你可以说,那是买了一只狗,自己又对着马厩的门叫——”
“锁上了马厩的门。”斯蒂芬举起一只手,说道。
“正是这样。锁上了马厩的门,你还自己叫。可你知道,除了天堂、大地,还有别的东西。斯蒂芬,你不想坐在大舱里自己拉琴吗,或者去邀请马丁来,或者把斯卡拉蒂改编成适合提琴演奏的谱子?”
“不了。”斯蒂芬说,他任何时候都不愿意显得像在沾光,于是他消失在弥漫着霉味的下级军官室里,和马丁、亚当斯先生、航行官一起,玩起了半便士输赢的惠斯特扑克游戏。但比起往常来,现在专心玩牌变得相当困难,因为海军陆战队的霍华德正在学吹德国笛子,他所依据的方法,尽管听说特别浅显、无须很高的理解力,可还是让他极端地困惑;而莫维特正对贺尼读着伊利亚德的片段,他虽然声音很低但却极其陶醉。因此,医务兵来叫他和希金斯去做夜班巡视时,他并不感到十分遗憾。
在甲板上,奥布雷舰长一手拿着已经变冷的、或者至少已经半冷不热的豌豆布丁,另一只手抓住主桅杆上桅最靠船尾的直立后支索,确实在用他腹肌的收缩和他意志的持续努力催促他的军舰;不过他还做了很多别的事。确实,他有一批得力的军官,况且普林斯和莫维特两人尤其对护卫舰了解很深;可他认识它的时间却比他们要长得多——他还是个不听管教、被罚站桅顶的男孩子的时候,就把自己姓名的起始字母刻在了它前桅杆中段的桅杆帽上——而且直截了当地说,他比其他人都更善于驾驶这艘军舰。
他几乎就是在骑一匹威风凛凛的马,他熟悉它的情绪和步调,就像他熟悉自己的情绪和步调一样,这是因为,虽然他从没拉过缆绳,或者摸过舵轮(除了因为要不时感觉它舵柄的震动,感觉舵柄啮合的准确程度),他却有一支高度灵敏的船员队伍,他和他们一起驾船,追逐过富有的捕获船,逃脱过强大到毫无希望的敌人,也是通过他们,他和船有了最贴近的接触。在航程的早期,他对风帆的升降是小心谨慎的,中桅帆的帆篷晚上总是收缩着以防大风。现在他放弃了这套做法,每天晚上,“惊奇”号都上上下下扯满了补助帆,只要补助帆能承受得住就行。而对水兵们而言,大多数人都很清楚,这是又一次的场合,船正在逃离强大到毫无希望的敌人。他们观察到,舰长保留了最初几桶散发恶臭的有毒雨水;通过无所不在的仆人们,他们也听到了下级军官室和大舱里关于这个问题的所有议论;而且通过直接的偷听,他们还听到了后甲板上所有相关的对话。而那不多几个想反驳的人,那几个没有被他们船伴的辩才说服的笨屁股蠢蛋,也被连续不断派到舵轮去的不当班的精干舵手们,被一个值班岗接着一个值班岗持续出现在甲板上的舰长,被他坚持叫他们以超自然速度扯起所有船首三角帆和支索帆的命令,给完全说服了。
黎明时分,他仍旧在甲板上,利用海洋的每一次涌起、风的每一次推动,让船驶得更远一些,更快一些。柔风已经偏转到朝南方向,在这个时候,“惊奇”号已经尽可能收缩了帆篷,它那些迎风帆的纵椽都瑟瑟抖动着。随着太阳的升高,风力也增强了很多,现在它显示了抢风扬帆开行的时候,它能够做些什么——它背风面的船首链台浸没在船头波华丽的泡沫中,船头波的白线在它船舷下面深深地弯曲着,船腹的铜板包底都露了出来,而宽阔的尾波以每五分钟一海里的速度,从它背后笔直地逃离。他把手头没有任务的水兵们都叫到甲板上来,他把他们,连同两班岗哨的全体水兵一起,沿着迎风面的栏杆排开,好让军舰更加稳定,接着他又升起了大桅最高第二帆,他站在那儿,双脚牢牢地抵住倾斜的甲板,浑身被飞沫浸透了,他的脸扭歪着,满脸是没有刮过的淡黄色胡楂,他看上去完全兴高采烈。
他中午仍旧在甲板上,现在柔风稍微减弱了一些,但依然恒稳得令人高兴。
它从东南偏东方向吹来,已经宣布自己是真正的贸易风了。而且在太阳越过子午线的时候,他和航行官以及其他在场的军官们,无限满足地发现,在这次观测和上次观测之间,“惊奇”号航行了一百九十二英里,已经彻底逃离了无风变风带。
早早地吃过午饭,他在小床上睡了整整一下午,他仰面躺着,打着鼾,他的鼾声如此之大,如此持续,连船头钟阁里的水兵们都互相挤眉弄眼,露齿而笑了,而兰姆太太摇着头,对海军陆战队中士的妻子低声说,她从心底里可怜奥布雷太太。可在全体集合的时候,他睡醒了过来。因为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