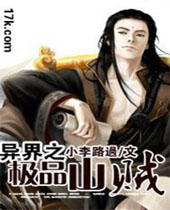怒海争锋之极地征伐-第2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停下。”第八遍钟敲响时,杰克说。脸色通红、睡眼蠓咙的左舷值班水兵们和航行官一起接管了午夜的甲板。“晚安,麦特兰先生。艾伦先生,我看我们大概在圣约翰角附近的水面上。我们有超过一百英寻的深度,水深在慢慢变浅。你怎么看?”
“嗯,阁下,”航行官说,“我觉得我们应该在测铅中空的地方涂上油脂,继续测量深度,直到我们碰上九十英寻的深度、碰上白色多贝壳的海底为止。”
第一遍钟,第二遍钟。然后,舵工终于把测铅拿到了灯笼下面,说道:“九十五英寻的深度,白色多贝壳的沙地,阁下。”怀着强烈的宽慰感,杰克下命令抢风驶船。“惊奇”号现在从那个邪恶的背风岸驶离了,但仍旧朝南,杰克可以下去睡个安稳觉了。
天刚亮的时候,他再次走上了甲板。天色晴朗,风力在变强,吹来阵阵怪异而不安的大风,天空和海面同样动荡不宁。混乱无序,但背风面已经看不见陆地了,一点陆地也没有了。航行官负责了午夜值班岗哨,本来应该睡觉,可他还在甲板上,他们两人一起给军舰制定了一条航线。这条航线应该可以让船绕过荷恩角,同时和陆地保持不远的距离——距离远到正好足以让他们高枕无忧,但同时又近到军舰能够得益于内陆变风的地步。现在的内陆变风是从北方和东北方吹来的,这是再有利不过的了。
在基里克和他煤黑色的助手不满的注视下,大舱的客人们吃完了杰克最后一块奶酪。这时军舰仍旧在获益于内陆变风,黑面孔上通常都燃着白色的微笑,它表露出来的不满,确实是货真价实的不满了。晚会进行得不很轻松;首先,现在船上的情况显然和欢宴不相适宜;其次,他的朋友们认识的那个乐观自信、脾气温和、多嘴多话的杰克,和身材高大、仪表堂堂、身穿华丽军服的奥布雷舰长也是非常不同的,他的脸被长年近乎绝对的权威塑造得威严十足,而他接待的两个美国人则比他年轻得多——也和他自己所想象的相距甚远。于是他们分手的时候,各自都心怀着共同的、尽管都遮掩得很好的放松感。莫维特、马丁也作陪出席了宴会。俘虏们和莫维特、马丁一起回到了下级军官室,而杰克则到后甲板上去踱步。
在后甲板上,他发现“惊奇”号保持着航线,不过从天上的情况来看,“惊奇”号的航线不可能保持太久了。航行官也在甲板上,他时不时用望远镜扫视从左舷船头到正梁的海平面;有几个人和他在一起,因为大家都在传说,要是天空保持晴朗的话,荷恩角可能就在这段时间出现。
而且传说也没有传错。在他十七码长的后甲板上,杰克正来回踱着步。为了控制舰长的所谓肥硕症,斯蒂芬坚持要杰克每天踱步三英里。还没等他走完三弗隆的距离,嘹望兵就叫喊说看到陆地了。麦特兰、霍华德,连同所有没受伤的候补生全都跑到大桅楼去看,随即,从甲板上也能看见了。作为世界的冷酷终点,它没有多少陆地,在大海的边缘上它是个高高的黑斑,它持续不断地闪烁着白光,那是海浪在它脚下撞碎,高高地溅上耸立的巨石。
更多的人走上了甲板,其中包括军医和牧师。“他们看上去多像初次出海的人啊,可怜的家伙们。”杰克温和地摇摇头,想道。他把他们叫过来,告诉他们,那确实就是荷恩角,还让他们用自己的望远镜观看。马丁绝对地兴高采烈。盯着远处危险的峭壁,看着飞沫腾起到匪夷所思的高度,马丁说:“这么说来,那些水沫,那些破碎的水花,就是太平洋了!”
“有人把它叫做大南海,”杰克说,“在四十度纬线以下,他们不把它看成真正的太平洋。可是我觉得,到处都同样地湿。”
“不管怎么说,阁下,”马丁说,“那儿是世界的另一边啊,另一个海洋,另一个半球,我多么高兴啊!”
斯蒂芬说,“大家为什么今天这么着急想要绕过它呢?”
“因为他们害怕天气会起变化。”杰克说。“这儿是西风地带,你肯定记得我们在‘列奥帕德’号上的那次航行;可要是我们能绕过荷恩角,绕过迪艾果·拉米雷兹,而且朝上多走几度,就算西风猛吹——我们还是可以改变航向驶向下风,靠近智利海岸——我们还是可以转过弯去。不过在我们绕过它之前,你看,一股西南风,甚至就连一股强西风,都可以挡住我们的路。在这个时候,我们非常害怕西南风。”
太阳沉人了紫色的云层,柔风完全停息了下来。在一种风和另一种风交替的间歇中,荷恩角的洋流抓住了军舰,把它紧紧裹挟着向东而去;而在午夜值班岗开始的时候,西南风尖啸着吹了过来。
在接下来的几天和几个星期里,尖啸声很少减弱过。有时候它会上升到狂躁的高音,威胁桅杆本身的安全而且它从来也没降低到常规时期大家觉得非常严重的水平之下,不过现在大家不久都习以为常了。
在开始的三天,杰克一直竭力保持他宝贵的西向进程,侧着穿过大风驶向六十几度纬线的海域,在那儿,甲板上、索具上、帆桁上结满了冰,冻结的飞沫把帆布变得像木板一样坚硬,缆绳也在滑轮上冻住了,人们因此而悲惨地受苦。向南,向南,一直向南,尽管有冰的危险,尽管晚上有和冰山致命相撞的危险,继续向南,希望情况会出现转变;但是等到转变出现了,情况却变得更坏,正西风增强了,朝东面翻卷而来的巨浪变得更大了,它们白色的、被风撕裂的浪峰彼此相距四分之一英里,其间是灰绿色深深的浪谷,而“惊奇”号最多可以做到的,不过是顶风停船——而且其中有整整一天,狂暴的一整天,整个海面——山峰似的海浪、浪谷和所有的一切——都成了空气和粉碎性海水的混合物,“惊奇”号只得在鹅翅形的前桅中帆下顺风疾驶,丧失了一段很长距离的进程。每个小时那样的噩梦般的顺风疾驶,都意味着,需要一整天劳累地顶风开船,才能重新挽回丧失的西向进程;而虽然“惊奇”号和它的水兵们,早已习惯了南半球高纬度巨大的海浪,早已习惯了声名卓著的南纬四十几度的海浪,习惯了更糟糕得多的南纬五十几度的海浪,他们却从没有逆浪行驶过,甚至没有尝试过逆浪行驶。海浪的尺寸非常大,迎着海浪的护卫舰,看上去更像一只小艇;虽然它有四十码长,但它还是无法横跨两个海浪,于是它的路径成了一条猛烈前后纵摇的“之”字形道路。
这猛烈的前后纵摇也差点要了马图林医生的命。他正准备到底层去——他正恋恋不舍,因为军舰上空飞着不少于七只信天翁——这时候他发现掌帆长的猫正在下一级阶梯上给自己洗脸。自从它了解到自己不会挨饿、不会受虐待、不会给扔到海里去,它就放弃了所有伶俐的、爱抚人的做派;它现在傲慢地瞪了他一眼,然后继续给自己洗脸,“这是我见过的最装腔作势的猫。”斯蒂芬恼怒地说,一边高抬起脚跨过它。猫向旁边跳去,而与此同时,“惊奇”号的船头撞上了海浪的绿色高墙,把它的牙樯指向天空,把已经失去平衡的斯蒂芬摔向前面。不幸的是,下层甲板的一扇格子板打开着,他下落了很长一段距离,落在煤堆上,这堆煤是为吊炉准备的。
身上骨头没断,不过他擦伤、摔伤、扭伤得厉害,也很受了一场惊吓;而且这件事正好发生在最不幸的时候。当时暴雪一直在从水平方向吹来,像鸟枪子弹一样猛烈,同一天晚上,在暴雪的间歇期,杰克下命令收卷前桅和大桅的中桅帆。两个值班岗的水兵们都在甲板上,他们一起在帆耳索、帆角索以及两者的帆脚索上忙碌着;而帆耳索、帆角索都断裂了,而且是几乎同时断裂的。因为帆脚索半松开着,风帆马上从针脚处崩裂开了,大桅中桅帆剧烈地摇晃起来,桅顶马上就会折断。莫维特、掌帆长、邦敦、大桅楼队长瓦里,还有瓦里手下的三个水兵,立刻爬上了桅顶,趴在结满冰的帆桁上,紧贴着帆篷把中桅帆切割了下来。瓦里站在背风的桁端上,他踩着的脚缆断了,他栽下来远远地落在船舷外面,马上就消失在可怕的海里。同时,前桅中桅帆完全撕成了碎片,而主横帆也被吹得松开了,它携带着可怕的力量,上下翻腾,左右摧毁。他们在常常是齐腰的旋流中,把帆桁降到船舷的高度,他们竭尽了全力,他们的努力程度,常人也许会觉得难以设想;接着他们又降下了前桅最下桅桁,开始把小艇固定在吊杆上,而吊杆本身也处在松脱的边缘。在整个这段时间,“惊奇”号仅靠后桅顶风停着。最终他们成功了,他们又开始缠结,编接损坏的索具,又把受伤的船伴们扛到了下面。
等船差不多修整完毕之后,杰克下到了伤病室。“金肯斯怎么样?”他问。
“我怀疑他是否能活下来。”斯蒂芬说,“整个肋骨腔都……罗杰斯可能会丢一只胳膊。那是什么?”他指了指杰克用手帕包扎的手。
“就是几个指甲扯掉了。我当时还没留意。”
从水兵们的观点看,从那天开始,情况就已经开始好转了。现在,以无休止的劳作为代价,他们又可以稍稍向西前进了,而且尽管大风仍旧稳固地保持西向,有些天他们还是可以逆风行驶,而不是转向下风了,还是可以把在这种海流和风向情况下,因为转向下风而痛心丧失的距离弥补回来了。然而从医生的角度看,事情并没有好转。水兵们的衣服总是潮湿的,水兵们自己也可怕地挨着冻,经常情绪低落,而且斯蒂芬非常担心地发现,有几个人出现了败血症的最初症状。舰上只有酸橙汁,缺乏有效得多的柠檬汁,他甚至怀疑酸橙汁质量掺假。他照料着伤病员,成功地给罗杰斯的断胳臂进行了截肢,处理了许多新出现的病例。虽然马丁、看护兵普拉特(一个温和的、不付诸行动的恋童癖患者,)和兰姆太太都在照看病人方面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希金斯则远不如他们——但他还是觉得工作很劳累。他很少见到杰克,杰克几乎要么总是在甲板上,要么就在沉睡。他惊奇地发现,自己非常怀念下级军官室极其简朴的午餐——除了不朽的阿斯帕西亚,所有的牲畜都丧身了,所有的私人储藏也都全部吃光或者毁掉了,他们现在已经沦落到只吃军舰定量供应的地步——他们吃得很快、食之无味,而且有时候厨房生不起火来,他们只好吃饼干和切成薄片的生腌牛肉。工作很劳累,还要再加上浑身的持续疼痛,加上戴安娜引起的持续消沉——预感、噩梦和预兆。最可庆幸的是,他还有古柯叶,那种高效的树叶可以让他在白天坚持下去,可以驱除他的饥饿,在晚上他还有鸦片酊,可以至少把黑暗变为他的庇护所。
他有一些时间是和荷纳太太一起度过的。刚开始的时候,她随时都得有人照看,因此陪她是必要的,后来陪护却成了习惯,部分的原因是军械官有一把可以前后摇晃的绳编坐椅,这是军舰上可以让他扭伤、挫伤的四肢和咯吱作响的躯干不感到疼痛的唯一一把椅子,另外一部分的原因是他开始喜欢上她了。妇女们具有的品质中,他喜欢的莫过于勇气了,而她有高度的勇气和韧性。在任何时候,她都没有自我,冷悯,没有抱怨,在她最疼痛的时候,也只不过是发出愤怒的、气喘吁吁的、完全不由自主的呼呼声,听上去几乎像是低声的吼叫。
她很早就已经和他推心置腹,谈到了她对侯隆的感情——他们准备一起逃走,去建一所教授数学和航海的学校——她会煮饭,操持家务,缝补衣服,就像现在她给舰上的候补生们做的那样——一开始,他以为她近乎耳语的梦呓是谵妄的声音,于是就温和地附和了她的想法,以此来安定她兴奋的头脑。但后来等他开始严厉地禁止这种不当的想法,他才发现,她早已察觉到了他对她的好感,因此他严厉的话没有产生任何效果。
而侯隆本人从一开始就显出了强烈的焦虑。他没办法公开地说出来,但候补生们却可以说,于是,每天都会有一个候补生来问斯蒂芬,荷纳太太身体怎么样了,再马上把斯蒂芬的话转达给她的情人。而尽管他羞于见到斯蒂芬,为了探询她的病情,也许还为了和斯蒂芬探讨她的情况,他还是两次报告了生病,但这样做并没有奏效。斯蒂芬用半片蓝药片和一种黑药水打发了侯隆,并且告诉他,除了说病人状况很好、很差或者死了,他不能讨论病人的情况,他的做法杜绝了侯隆倾诉的途径。
然而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随着“惊奇”号慢慢地向西,向北航行,进入比较平静的水域,随着年轻人的康复能力在迟疑的萌动之后,以显著的速度发挥起作用,事情变得越来越清楚起来了,原来侯隆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交通线。他变得高兴得多了,在他和书记员、希金斯、美国候补生合用的三角形狭窄卧舱里,有时候还能听到他唱歌,或者听到他在贺尼的吉他上弹奏。
在军舰可以扯起所有主横帆和全副中桅帆的第二天,毫无怜悯心的、善用鱼叉的军械官,把一头在海面上抬头看他的海狮杀死了。斯蒂芬取了它的肝用来治疗舰上的坏血病患者,他还留了一点去带给荷纳太太,他去的时间比通常夜晚巡视的时间要早一些。他看见他们紧紧地拥在一起,嘴对着嘴,于是他用极端愤怒的语调说:“离开房间,阁下。我说了,马上离开房间。”荷纳太太剪短的头发直竖着,脸色比她发高烧的时候还要红,像个受了惊吓的男孩。他随后对荷纳太太说:“把它吃下去,太太。马上吃下去。”他把盘子重重地放在她肚子上,走了出去。侯隆就站在门外,斯蒂芬对他说:“你要选择冒险,那是你自己的事,不过你的选择不能影响到我的病人。我不允许她的健康受到危胁。我要报告舰长。”
即便在他正说出这番话的时候,他就已经对自己义愤的腔调感到了羞愧,对其中赤裸裸的嫉妒感到了惊奇,而同时他察觉到侯隆正看着他的背后,脸色发白,表情惊惧。他转过身,看见杰克的魁梧身躯塞满着整个过道——像很多身魁力大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