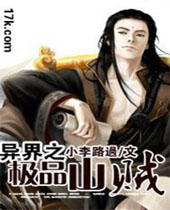怒海争锋之极地征伐-第3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旧会比它快一倍。它们是在回归线以下碰到的,东北偏北二百里格,离这儿很远。“艾斯特雷亚”号很高兴把“惊奇”号的信带到欧洲,希望它航行快乐。两艘船各自扯起降下的中桅帆,互相分开,一边叫喊着客套的告别话。在半英里外,最后能听见的西班牙话是“que no haya novedad”。①
①西班牙语:但愿没有新东西出现。
“那是什么意思?”奥布雷舰长问道。
“希望没有新东西出现。”斯蒂芬说。“新东西本质上都是坏的东西。”
有人把他们的信带往旧世界,“惊奇”人感到很高兴;他们也为那半匹帆布心存感激;他们怀着真挚的善意向“艾斯特雷亚”号道别。然而他们极其热切地期待了一晚上,在午夜值班岗的时候又因为看见它的灯光而喜不自胜,现在“艾斯特雷亚”号不能不是个反高潮,不能不是个苦涩的失望。得知“诺尔福克”号早就已经绕过了荷恩角——比他们要早得多——已经掳获了不列颠的捕鲸船,而这些捕鲸船正是他们被派来要保护的,大家还都感到了强烈的羞愧。许多“惊奇”人都有朋友亲戚从事南海捕渔业,因此他们强烈地感受到了切肤之痛,尤其是艾伦先生。他一直是个严厉的军官,当值的时候从不微笑,可他不是个蛮横的人,因为他从不辱骂水兵,也不放肆地骚扰水兵,然而他却严格,确实非常严格;现在他就更严格了。那天他负责下午值班岗,天空变得阴沉,开始下起了小雨;微风也变得方向不定,有时候甚至令人疑惑,而他严厉愤怒地吼叫着命令,让水兵们一直奔忙着,升帆,转帆,再收帆。
他和杰克进行了长时间的商讨,他们两人断定,根据“艾斯特雷亚”号提供的信息,最好的航线是驶向陆地,离回家的捕鲸船路径越近越好。这不是“惊奇”号去加拉帕戈斯群岛的直接航线,但是,航行官坚持说,他们不会损失多少时间——加拉帕戈斯群岛既宽又长——因为沿着海岸线向北的寒流,裹挟着海狮、企鹅,差不多一直延续到赤道那么远,寒流几乎是整个智利和秘鲁的长度。艾伦的道理和他在这片海域多年的经验,在杰克看来是有说服力的,现在军舰穿过忧郁的小雨,尽可能地转向东北偏东方向。
这是一段令人忧郁而心神不定的航程。他们已经摆脱了一个倒霉的人,可怜的侯隆——现在他们就是这么称呼他的——可他们又添了个更加糟糕的人,这个人必定会给他们带来厄运。候补生们可怜地深受影响——荷纳太太一直待他们很好,除此之外,他们也和成年人一样,一直对她的美貌感触颇深——杰克突然改变了他们的住处,让他们和他的秘书沃德,还有希金斯以及那个高个子美国候补生一起吃饭。沃德不愿意和他们做伴在的速度是八节,尽管他们现在都两眼通红,像老鼠一样安静,可再让他们和荷纳待在一起,是件无法容忍的事情。
军械官用酗酒的方式庆祝了自己的自由。他强迫自己的一个助手陪他喝酒,在座的还有更加情愿得多的理发师康普顿,康普顿是舰上唯一勉强可以称为他密友的人物。荷纳的食物储备很充足,他还剩有三个淡水桶的西班牙白兰地,他们一直喝到半夜值班岗的时间,那时候甲板上的水兵们恐怖地听见,荷纳用粗哑的声音在唱“早来也罢,晚来也罢,我总会在六月享受玫瑰花”。
一天又一天,“惊奇”号驶过翻腾的海面,军舰沉重地劳作着。而每天晚上,荷纳都坐下来和理发师一起喝酒,可以听到理发师用尖厉的腹语一遍遍重复自己的保留节目,紧接着是微醺的、变得喜欢倾诉的荷纳低沉、闹嚷的声调。这声调震惊了甲板上的人们,也震惊了军舰下层的人们。即便等到一个晴朗的中午,等到“惊奇”号抵达凉爽的、天蓝色的秘鲁海流,等到它转向北方,在右舷正横方向非常非常遥远地望见安第斯山脉嶙峋的、在晴空中闪耀白光的线条,舰上的情绪仍然没有变化。水兵们抑郁、沉默;他们觉得康普顿简直是疯了,竟然和军械官开怀对饮。某天晚上他们见到他满脸是血地跑上甲板,军械官在后面追着,不过他们一点也不觉得惊奇。荷纳绊了一跤摔倒了,他们把烂醉的荷纳抬起来送到下面。康普顿只是摔破了嘴,鼻子流着血,可他害怕得站都站不稳了,他对给他擦血的人说:“我就说了句她怀着孩子。”
第二天,军械官派人来说他希望见马图林医生。马图林在自己的卧舱里接待了他。军械官的动作完全平稳,但他和人没有目光的接触;他的面色很苍白,晒黑的肤色显出了赭色——一种暗淡的赭色——而斯蒂芬的印象是,他充满了一种几乎无法控制的狂怒。“我是来见你的,大夫。”他说。斯蒂芬鞠了一躬,但没有回答。“她生病的时候怀着孩子。”军械官突然说。
“听着,荷纳先生,”斯蒂芬说,“你在谈论你的妻子,而我必须告诉你,我不能和任何人讨论我的病人。”
“她怀着孩子,可你对她用了器械。”
“关于这件事,我对你没什么可说的。”
门开了。帕丁迅速地走了进来,他围拢双臂,从背后抱起了荷纳。帕丁比荷纳还要高大,而且要强壮得多。“好了,把他放下吧,帕丁。”斯蒂芬说。“荷纳先生,请坐到那把椅子上去。你的头脑不安定,你最近情绪很激动,心烦意乱,这我可以理解。你需要吃药。把它喝下去吧。”他在葡萄酒杯里倒了半杯自己的鸦片酊,递了过去,说道:“我不会假装不知道你的意思,可你必须明白,我一辈子从来都没在那种意义下使用过器械,而且以后也决不会那么做。” 他怀着真挚的善意说了这番话,或许这种善意比明显的事实本身更具有穿透力,军械官喝下了递给他的药水。
这么大的剂量,本来应该足以让十多个不习惯这种药水的人平静下来,但同一天下午,希金斯跑来见斯蒂芬,希金斯的样子与其说是惊慌,不如说是极度恐惧。“他说我对她用了器械——噢,阁下,你得保护我——我是你的助手——我是你的下手——你得保护我。他尊敬你,他一点也不尊敬我。”这是真话。希金斯的饶舌重复得过多了,他的贪婪也变得过于赤裸了,他愚蠢到竟然去欺压看护兵,而看护兵却是下层甲板水兵中颇有名望的医学先知,看护兵揭露了希金斯的很多丑事,私下里还给别人看了他陈腐的蠖螋和破旧的锹螂。况且说到底,斯蒂芬给普莱斯做的开颅手术,已经把希金斯在牙齿方面可能拥有的一丁点成就差不多抹光了。
“你最好躲着他,等他平静下来再说。”斯蒂芬说。“你可以呆在伤病室里,给伤病员们念念书。我会叫帕丁陪你坐上一两天的。你得和军械官礼貌地说话,也许送他一件小礼物。你有点轻率,损害了他的善意,你得想办法跟他和解。”
“噢,阁下,我会给他半个畿尼的——一个畿尼——我会给他两个畿尼的,我发誓——除了睡觉,我不会离开伤病室的,你不用担心,阁下,睡觉的时候我四面都是吊床,而且大个子美国候补生就睡在门边。”
然而星期五还是出事了。那是个乌云密布的凄惨日子,斯蒂芬和马丁正在解剖一只鹈鹕。军舰正沿着肥腻的洋流航行,企鹅、海豚和各种各样的海豹、海狮、海熊常常在其中出没,洋流中同时还有数量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大群鲲鱼一类的小鱼,天上则飞着大量以它们为食的鸟类。海军陆战队的霍华德射下了很多动物,这只鹈鹕就是其中之一。马丁说,“他们说的‘约拿的提升’是什么意思?”
斯蒂芬还没来得及回答,霍华德就走下来告诉他们,有一头奇怪的、巨大的东西,游到了射程之内,它看上去很像一头海象。他开了枪,不过只射中了它旁边的幼崽,因为在关键时刻,一阵水雾飘到了他和猎物之间。要是他们见到那东西就好了;它非常奇妙,就像个人一样,只不过比人要大,它的颜色可以说是灰色。他真希望他们见到了那东西。
“霍华德先生,我知道你的用意是好的,”斯蒂芬说,“可是让我恳求你不要过度射杀动物,不要超过我们能收集,解剖的限度,也不要超过大家能吃掉的限度。”
“噢,大夫,你向来不是个喜欢打猎的人。”霍华德大笑着说。“嗨,要是你喜欢打猎的话,在这片水域里你可以整天不停地开枪;现在一群鹭鸶正在飞过去,我左右开弓,玩得正开心呢。我得马上回去了;我叫了两个人给我上膛。”
“约拿的提升,你是说?”斯蒂芬说,“大概这是他们的行话,是说—个大家不喜欢的人,或者一个倒霉的人,被推到海里去了。”
“噢,肯定不会吧。”马丁说,他不清楚最近的动态,“我听他们在这么说希金斯先生。”
“真的吗?”斯蒂芬说。“求你拉着皮,等我回来。”
希金斯不在伤病室里,也不在他的卧舱,而且斯蒂芬寻找他的时候,留意到一些人在交换意味深长的目光。他把看护兵叫到一边,说道,“听着,杰米·普拉特,你是什么时间最后见到他的?”
“喔,阁下,”杰米说,“他不敢到厕所去,你知道,他要么用瓶子,要么用罐子。可昨天晚上他肚子咕噜噜要拉稀,就到船头去了,那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我再也没见过他。我以为他可能和你在一起,要么在他卧舱里,要么在缆绳舱里。我听说他在那儿有个躲的地方,因为他非常害怕某个先生,可以这么说。”
“要真是躲在下层的话,全体集合的时候他肯定会回自己岗位的。”
鼓声响了起来,甲板上的那些隔板全都消失了,护卫舰可以从船头望到船尾,它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而所有的水兵都跑到了各自的岗位上。莫维特迅速巡视了一遍,准备对舰长说,“所有水兵都在岗位上,处于戒备状态,阁下,请。”他看见掌帆长在船首楼上,船匠和助手们在抽水机旁和翼舱里,军械官和他手下的军士、助手们在弹药库里各自的岗位上。不过,等他走到阴暗的下层,看见斯蒂芬、马丁和看护兵都站着准备好照顾伤兵,斯蒂芬却说:“阁下,我必须报告,我的助手希金斯先生缺岗。”
没有进行大炮演习就结束了全体集合。鼓手们敲起了解散鼓,杰克命令彻底搜查下层平台和储备舱。希金斯有可能在缆绳舱里,躲在大圈的缆索中生了病,或者有可能从某个升降口失足掉了下去。在迅速降临的暮色中——低低的云雾已经开始飘过高处的索具——人们点起了灯笼,开始了这一定要走的必要过场。可他们的心思不在这儿。当然他们的心思不在这儿,因为他们明确地知道有人给了希金斯一个约拿的提升,再说这也不是什么重大损失。在哀鸣开始的时候,他们全都匆匆地回到了甲板上,挤作一团地站着。
这哀鸣是种音量巨大的、悠缓的、绝望悲哀的哞——哞——哞,有时候音调会变得高起来,变成尖叫,就连船上最老的水兵,也从没听过海上传来这样的声音,而且这声音围绕着军舰,离两边的舷侧都很靠近,有时候可以分辨出一个形体,可从来也看不清楚。不管怎么说,也没几个人敢看。
“那会是个什么东西呢?”杰克问。
“我说不准,”斯蒂芬说,“可能就是那个东西,它的幼崽挨了一枪。也许那个幼崽受伤了,也可能现在死了。”
声音变得更响了,响得几乎令人难以忍受,随后又在垂死的呜咽中停了下来。“莫维特先生,”杰克用极其不安的口气说,“船已经彻底搜查过了吗?”
“我不能完全肯定,阁下。”莫维特说,他在哀鸣声中把声音提高,而哀鸣现在转到了左舷方向,“我马上去问问。”他问的所有问题,得到的答复都是一样的:是的,每个地方都仔细检查过了;不,阁下,再下去查一遍也没有用。对他说这些话的人,都是负责的委任军官们和军士们,有时候他们是在对他当面撒谎。不过他清楚,而且他们也清楚,不可能再让水兵们到军舰上比较偏远、比较黑暗、比较僻静的地方再搜索一遍了。
“上帝是我的生命,”杰克叫道,他看见沙漏已经流空了,而即使在激烈的海战中,即使军舰的船底凿穿,沉到了海下,这个半小时的沙漏瓶也一直是宗教般按时翻转的,“上帝是我的生命,你到底在想什么呢?翻转沙漏,敲钟。”
当值的海军陆战队员翻转了沙漏,不情愿地走向船首。八遍迟疑的钟声,四处响彻着号叫。
“布置值班岗哨。”杰克说,“朱达斯神甫啊,你们都站在这儿干什么?莫维特先生,今晚熄灯之后,住舱甲板上允许挂灯笼。纠察长,留心这件事。”
他停下来想看看值班水兵是否确实集合起来了。有一会儿工夫他觉得可能连这都做不到了,这是因为,虽然他经常见到水兵们惊慌不安,心神不定,但他从没见过他们这样害怕,也没见过他们这样垂头丧气。不过大部分军官都在甲板上,而迟钝的、完全没有想象力的亚当斯先生,还急切地和斯蒂芬、马丁讨论着瓶装淡啤酒的储藏问题,他的在场,帮助麦特兰先生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一等到点名结束,杰克就走进了大舱,双手背在身后,沿着横跨船身的方向来回踱起步来;同时,可怕的大声哀鸣一直围绕着军舰。
“传话请大夫来。”他终于说。斯蒂芬进来之后,他说:“我听说马丁问起过你约拿的提升。我知道大家在议论些什么,我也一直在考虑。这种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请告诉我,因为大家都认为军械官犯下了大罪,你是否可以正式判定他是疯子,必须把他拘禁起来。”
“我不能这样做。许多人干过大家说他干的那种事,可还是被当成精神正常的人。我既不能根据假设,也不能根据非常强烈的怀疑,甚至不能根据合乎法律的证据,就正式判定他是疯子。我必须尽可能地检查他的心志,必须了解他干这件事的时候是否合乎理性。从不可靠的、独立完成的检查,也会产生知识的微弱亮光,我至少必须凭借这亮光去了解真相。”
“检查?”杰克说,“很好。”他摇了摇铃说,“传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