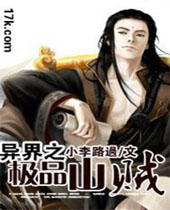怒海争锋之极地征伐-第3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可以把你的消色差望远镜……”斯蒂芬止住了自己,停顿了一下,又说:“你非常好心,可我自己也有一架。我不想再麻烦你了。”
他感到极端地愤怒:他的解决办法——相对于三角形两条非常长的边,取其短边——在他自己看来无可置疑地合乎情理。令他感到更加愤怒的是,现在舰上几乎每个人都对他格外友善、特别关心,不仅他的老朋友们,比如邦敦和基里克,以及享受特殊待遇的乔·普赖斯(他简直把这个给他开颅的人当成了自己的私产,而且和只丢了一条胳臂的罗杰斯处在永久的敌对状态中),就连帕丁,还有新近加人的“保卫者”号的水兵们,甚至连候补生队伍里的小孩子们,都对他关怀有加。因为觉得自己比大多数人都更能保持volto sciolto, pensieri stretti,①一直感到自豪。他可以发誓,自己的苦恼完全无法察觉,可现在就连大字不识的戴柏油帆布帽的水兵们都安慰起他来了。
①意大利语:展开的面孔,封闭的思想。
怀着充满愠怒的满足感,他观察到,尽管海潮变更,事实上“惊奇”号在这两段水路航行得还是很慢,这是因为,柔风有两次变得对航行不利了。他们缓慢地驶过两片绝妙的岸滩,一条小艇本来是可以在那儿送他们上岸,再把他们接回军舰的,第一片岸滩就在捕鲸船黑色残骸所处的暗礁往前的第一个小海湾。他很清楚,他和马丁本来就算四肢着地爬过岛屿,也会有多余的时间。“只要一半的时间。”他嘟囔着,极端沮丧地敲打着栏杆。
他注视着昏暗的、乌云笼罩的加拉帕戈斯群岛在船后消失,随后就早早上床睡觉了。他的一连串祈祷词的最后一段,本来并不是为像他这样充满怨恨的头脑而准备的。然后他服用了两盎司的鸦片酊,躺在自己的小床上,拿起了博修斯的《论哲学的安慰》。
但即便如此,在午夜两点帕丁把他叫醒的时候,他还是非常恼怒。帕丁用英语和爱尔兰语,非常缓慢,极其困难地告诉他,布莱克尼先生吞下了一个四磅的葡萄弹。
“这种事情是完全不可能的。”斯蒂芬说,“那个可恶的小畜生在撒谎——炫耀——充能人——想引人注意。等我给他一剂药,让他吃点苦头——他就会懊恼的,相比之下蒙斯特的悲哀都算不了什么。”
不过等他看见那个小畜生之后,他了解到所谓的葡萄弹,原来只是游艇四磅大炮所用的一颗小炮弹,九颗小炮弹才组成一发。小野兽脸色苍白,惊慌失措,连连为自己辩解,人们已经把他安置在了半甲板的灯笼旁边。他马上叫人抓住他的脚倒提着,自己跑去拿来灌胃唧筒,朝他的体内灌进了大量温和的掺朗姆酒的盐水。在痛苦的干呕声中,他听到了铁球掉进盆里的当啷声,他高兴地想到,他不仅治好了可能致命的消化道堵塞,而且也戒除了病人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对酒精饮料的爱好。
虽然如此,虽然这次他在肉体上和道德上都大获全胜,但第二天他的情绪仍旧不佳。亚当斯说起舰长今天会出席下级军官室的午餐——而且午餐会特别精致,简直就是市长大人的筵席,可斯蒂芬只是说:“噢,真的吗?”他的声调里找不出一丝的高兴。“我知道那家伙以前是怎么在港口滞留的。”他从背风面的跳板上看着杰克,对自己说。现在“惊奇”号在广阔的南海平稳地航行着,从海洋的一边到不可想象的另一边都是纯粹的蓝色。“我知道这家伙以前是怎么在港口滞留的,只要事情和女人有关——还有奈尔逊,还有很多舰长、很多将官,只要事情和通奸有关——到那种时候,就把所有的顾虑都抛在脑后了,哪怕是对皇家军舰一丝一毫的顾虑。不,不,他们的顾虑只留给自然哲学,或者随便什么有用的发现。他的灵魂都给了魔鬼,这条不诚实的、伪善的狗,不过他可能没有察觉到自己的虚伪——pravum est cor ominiume①——心首先是背谬的,而且还捉摸不定。谁会知道心是什么呢?”
①首要的一点,心是背谬反常的。
可虽然斯蒂芬性情阴郁,报复心很强,他从小所受的教育,却让他非常注重待客之道。舰长是下级军官室的客人,舰上的军医是不可以心怀固执的怨恨,沉默地坐在那儿的。用了相当大的自制力,斯蒂芬说了四句礼貌的话,过了适当的间隔,他又深深地鞠了一躬,说道:“阁下,和你干一杯。”
“我必须最衷心地祝贺你,大夫。祝贺你保全了年轻的布莱克尼。”杰克回敬了他的鞠躬,说道,“要不然我真不知道怎么去面对我的老船伴,去告诉他说,就为了一颗葡萄弹,我们让他的儿子阵亡了。我的意思是说,这种情况下的葡萄弹,而不是法国人的或者美国人的炮弹。”
“他怎么会吞下那样的东西?”马丁问道。
“我当候补生的时候,谁要是说话太多,我们会往他嘴里塞上一个。”杰克说。“我们把它叫作棒头糖。大概事情就是这么发生的。”
“我可以给你一片狐鲣吗,阁下?”霍华德从餐桌的中部说。
“请吧。这种鱼是一流的,狐鲣,一流。我可以整天不停地吃。”
“我今天早上抓了七条,阁下。我是坐在后桅链台上,在尾波旁边下的钩。我送了一条到伤病室,一条送给候补生们,三条给了我的海军陆战队,留下最好的给我们自己。”
“一流,一流。”杰克再次说。确实,这是第一流的午餐:最好的绿海龟、晚上飞到船上来的鲜美的飞鱿鱼,还有各种各样的鱼,还有海豚馅饼,最精彩的是水鸭做成的一道菜。从味道上说,加拉帕戈斯群岛的水鸭和克里斯蒂安岛的水鸭不分上下。霍华德的中士以前是个偷猎者,水鸭是他网上来的。斯蒂芬不无恼怒地注意到,随着吃喝的进行,他的礼仪也变得越来越不做作了,他刻意的彬彬有礼的表情越来越接近于自发的微笑,他已经险些在放松自己了。
……
看那破旧褴褛的风帆,
迎着蠕动的无形的风,
把顶着滔天巨浪的大船,
拉过沟壑纵横的海洋。
玻璃酒杯重新添满的时候,莫维特在片刻的安静中说——他和马丁讨论诗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就是我说的那种东西。”
“这是你写的吗,莫维特?”杰克问道。
“不是,阁下。”莫维特说。“那是——那是另一个家伙写的。”
“蠕动的无形的风。”麦特兰重复说。“我听说猪可以看得见风。”
“等一等,先生们。”霍华德叫道,他举起一只手,满脸通红,用闪光的眼睛环视着大家。“你们得原谅我,可是我很少临时想得起好的笑话。大概这次出航以来还没有过,不过在普赖特河附近,有次就差了那么一点。所以,要是你允许的话,阁下,”——他向杰克鞠了一躬——“有一个科尔克湾的老太婆,她住在一个小木棚里,只有一间屋子;她买了一头猪——一头猪,呃,这是笑话的关键,不然这个笑话就不会这么妥帖了——因为它只能和她住在同一间屋子里,你们听明白了吗?那头猪只能和她住在同一间屋子里,所以大家就问,‘那臭味怎么办呢?’她说,‘噢,哎呀,上帝啊,它只好慢慢去习惯了,’ ——你懂吗,她还以为……”
霍华德的解释淹没在狂笑的大风里,站在杰克椅子后面的基里克笑得最欢。杰克自己也说:“它只好慢慢去习惯了。”他仰起头大笑起来,脸色深红,蓝眼睛比往常更加明亮了。“哎呀呀,哎呀呀。”他终于说道,他用手绢擦了擦眼睛,又说,“在这个眼泪的深谷里,时不时大笑一场对人很有好处。”
他们安静下来之后,军需官越过他的邻座,盯着第一副官说:“你刚才念的是诗吗?在猪的笑话之前。”
“是啊。”莫维特说。
“它不押韵。”亚当斯说。“我自己又念叨了一遍,发现它不压韵。要是娄万在的话,他会把你的诗人教训一顿的。他的诗总是押韵。我还记得他写的一首,就像是昨天的事: 航船倾斜着,龙骨咯吱咯吱地尖叫, 在异常的抖晃中,水兵们摇摇欲倒。” “我看诗的种类几乎就像缆索的种类一样多。”航行官评论道。
“确实如此。”斯蒂芬说,“你还记得那个阿麦德·史迈斯吗?他是斯坦厚普先生的东方秘书,我们去坎朋时见过他。他跟我说起过一种奇怪的马来诗歌,这种诗歌的名称我记不起来了,可我还记得一个例子:森林旁边长着一棵菩提树, 在渔人的岸滩上鱼网散乱; 我坐在你的腿上,千真万确, 但是你不要以为, 你因此可以对我动手动脚。”
“用马来语念它押韵吗?”在一阵安静的停顿之后,军需官问道。 “押韵的。”斯蒂芬说,“第一句和第三句……” 布丁的到来把他的话打断了,那是一个异常豪华的布丁,把它端上餐桌的水兵神态自豪,大家都鼓起掌来。 “什么,这是什么?”杰克叫道。 “我们料到你会惊喜的,阁下。”莫维特说。“这是一个浮岛,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个漂浮的群岛。”
“这就是加拉帕戈斯群岛啊。”杰克说。“这儿是阿伯马尔岛,这儿是纳尔伯罗岛,这儿是洽罕岛和胡德岛……我不知道舰上还有会做这种东西的人,我敢发誓,这是一件杰作,配得上一艘旗舰。” “是一个捕鲸人做的,阁下。他当水手之前,是但泽的糕点师傅。” “我加上了经线和纬线,”航行官说,“是用棉花糖做的;还有赤道也是,可我把赤道加粗了,还用葡萄酒着了色。” “加拉帕戈斯群岛,”杰克说,“完全吻合,就连雷东渡巨石和考里的迷岛也在,方位也都安排得很准确。不容易,想想我们从来也没有踏上过哪怕一个岛屿……我们的职业有时候是个要求很高的职业……”
“上帝之声的严厉女儿!噢,职责!”莫维特说。但杰克注视着在军舰的起伏中摇晃的群岛,没有听见他的话,杰克继续说,“可是我告诉你们,先生们,一旦完成了任务,要是我们还原路返回,我们要在詹姆斯岛上艾伦先生的小港里停泊几天,每个人都可以尽情地漫游。”
“你要一些加拉帕戈斯吗,阁下,不然它要漂走了?”莫维特说。
“要破坏这样一件艺术品,我有点犹豫,”杰克说,“可是,除非我们不吃布丁了”——带着心照不宣的表情,他把勺子放在糕点厨师的赤道上——“我看我必须越过赤道。”
赤道,赤道,每天沿着赤道,或者稍稍偏南,他们向西航行着。他们几乎马上就远离了企鹅、海狮,远离了所有的内陆鸟和几乎所有的鱼;他们也离开了忧伤的氛围、寒冷的海水、低垂的乌云;现在他们航行在天穹下一个不断更新着的深蓝色圆盘上,而淡蓝色的天穹,间或被非常高的卷云点缀着。然而他们航行得一点也不快。尽管“惊奇”号展开了辉煌的晴天轻帆——上上下下的补助帆、甚至所有的最上帆和第三层帆,连同第三层帆上的三角帆——可在两次观测之间,它航行的距离很少超过一百英里。几乎每天下午都有两三个小时,柔风要打瞌睡,或者甚至完全睡着,让风帆的众多金字塔处在凄凉的松弛状态,而同时广阔的死寂铺满了海面,只被偶尔会经过的鲸鱼和抹香鲸的队列所打断。鲸鱼们彼此间隔很远地排成一队,数目超过两三百头,它们朝秘鲁方向游去。每天晚上,在安排值班岗哨时,“惊奇”号还把其他风帆降下来,只留下那些中桅帆。虽说白天像羔羊一样无辜,晚上说不定还会有突然的暴风。
这是海军里大部分人都不熟悉的水域,拜伦、瓦里斯和库克的航线要么比这靠南,要么比这靠北。这样缓慢的爬行本来会让杰克着急,不过他已经从航行官那儿了解到,在太阳开始从回归线回移的时期,这儿一直就是这样的。况且对“诺尔福克”号来说,情况也是一样,说不定还更糟。艾伦和捕鲸主炮手交谈了多次。捕鲸主炮手是个名叫霍格的中年人,他三次到过马尔盖萨斯群岛;两次到过三明治群岛,他的第一手和第二手经验,对舰上的所有人都是极大的宽慰。他们尽快地航行着,但并不像看见追逐目标时那样,像紧急的日子里那样打湿风帆。因为他们知道,“诺尔福克”号会以更加迟缓的步调行进,而它到达马尔盖萨斯群岛之后,还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在岛屿之间游弋,去寻找在那儿捕鱼的不列颠捕鲸船。一刻也不能浪费,确实如此,但并非每一刻都必须快马加鞭。
军舰再一次以令人惊奇的速度,回复到一种完全正规的、自足的生存状态中。很快,这又重新成了自然的生活方式,“惊奇”人隔膜地回顾起他们在荷恩角以南遥远而酷寒的日子,甚至连他们沿着智利和秘鲁海岸的令人忧烦的航行,都恍若隔世了。
每天早上,太阳总是不偏不倚地正好从护卫舰的尾波里升起,照耀在刚刚清洗过的甲板上,但不久甲板就被凉棚隐藏了起来。这是因为,虽然这儿不像几内亚湾那么炎热,并没有热到沥青从木板缝里冒出气泡,柏油从高处滴下来的程度,比起记忆中红海臭名昭著的酷热就差得更远,但气温还是有华氏八十几度,因此遮阳是大有必要的。除非被邀请到舰长的大舱去,每个人都只穿帆布衣服,而即使在舰长的大舱,候补生们也被免除了厚厚的开司米背心。
然而对回复到正常的深海航行,候补生们也许是舰上惟独感到不太满意的一群人了,因为现在每件事都那么讲究,那么有条有理,那么服从布里斯托规矩。虽说除了在南纬五六十度最艰苦的那段日子,拉丁语和希腊语从来也没有撂荒过,现在两门课程却不仅恢复了正常,而且加倍地紧张了起来。而既然奥布雷有了时间,可以领他们游历导航术的迷宫,晚上他还让他们学习很多星星的名字、赤纬、赤经,找出它们和各行星以及月亮之间的角距离。他和莫维特也有了时间,可以着手提高他们的道德水准了;道德在海军的环境下意味着,很早就从舒适的吊床上起身,在钟声敲响之前很早就接替岗哨,决不把手放在口袋里,不倚靠在栏杆或者大口径短炮的滑动炮架上,在缩帆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