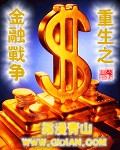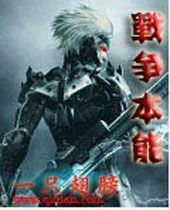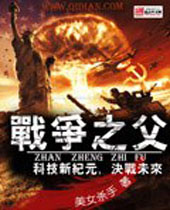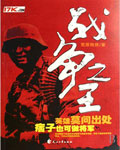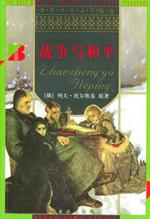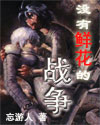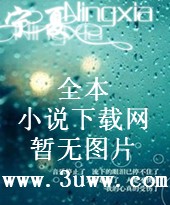中越战争纪实-第2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人可以排雷,但仅仅是在雷场的大平面上开出几条线来,那叫通道。
蚂蚁们可以把地雷蛀透,战区的蚂蚁能在水泥板上蛀窝呢,老鼠们可以在地雷上嗑洞,老鼠需要磨牙。但被蚂蚁、老鼠蛀坏的地雷有几个呢,地雷毕竟不是油饼。
1916年5月3日,英、德海军在日德兰半岛附近的海域展开了一场激战。战斗结束后,英舰〃鲁普斯〃号发射的一条鱼雷仍在海上横冲直撞。后来,有人在世界的其它海域也见过它,直到1972年后才不见它的踪影。
看来是需要时间,悠久的时间。时间就是历史。积淀已经留给了历史,历史会使地雷失效消逝,也会使地雷和恐龙蛋一起永久存留,并会使地雷变得象出土文物一样珍贵。
当我们在某部一连一排采访时,他们正在搬家,阵地上猫耳洞内的波纹钢全拆下来。
既要搬走,那所有猫耳洞都要炸掉,炸不掉的天然洞,石缝,就都布上地雷,整个阵地上都有地雷来封死,从里到外。地雷一箱箱运来,连那战地舞厅也堆了那么多箱的地雷。
这战地舞厅是战士们背水和水泥修的,上面编织袋被复层有二十厘米厚,舞厅内布置得很美。
明天一早这个舞厅将不复存在,它将被炸成平地,然后在上面布雷。标准只有一个:让敌人无法到这里来,也无法在这里排雷。
从明天起一连这里也不再是舞厅,而是一个再不能人有来的雷的原野。
战士们在达里举行最后一次舞会。
大家尽情地跳。音乐是欢快的,从此这里再也听不到欢快的音乐。
跳累了,就坐在一边的地雷箱上歇一会儿,接着跳。以后再不会有人到这里来跳舞了。
排长不想跳,班长郭庆喜也不想跳。〃你说,以后还会有人到这里来吗?〃
〃来不了啦。〃
〃真可惜,这儿风景多好,打完仗,应该开个旅游区。〃
〃坐直升飞机,不落下来,在顶上盘旋。〃
〃后方好多人候到这儿看看呢。〃
〃不打仗,就没有这么多人想来了。〃
〃我就想来。〃
〃来了,在那儿立脚?都是雷了。〃
〃不打仗的时候,这雷也没法整了吗?〃
〃没法。〃
〃以后科学就发展了呢?〃
〃也许。〃
第二天,人们听到那里沉闷的爆炸声,舞厅消失了,从此,那里只剩下了雷,留给大地也留给历史的雷。
雷躺在地下,不会永远呈静态,不甘留在一个地方,如果说雷成为地球的一种细胞,那么无数的溪水,河流,无数的塌方,滑坡,则是这种细胞转移的肌肉、血管、淋巴。
某部侦察排执行任务过一片流少地带,道路是排过雷的,谁知流沙的滑动又带来了地雷,把一个见习学员的腿炸了。
在某团部有一处接水的地方,人们常去,不料就从山上滚下来一颗雷,就滚到了这接水处。
某团三连新兵陈维标到厕所解手,正蹲着,从山上滚下一颗雷,在身边炸了,吓得他提裤子就往洞里钻。别人听到地雷响,以为他触雷了,说了一声〃不好〃也往外来救他,见他提着个裤子,脸吓得没点血色。他的体会:地雷这玩意,你不踩它,它也会来找你。
某部机关前面有一条小河,河里常有地雷冲下来,层层水波常会雷推到岸边。这里的侦察连在河边清理卫生,一次就从淤泥中清出三颗雷。
那次发大水,水把一个存放地雷的弹药库冲走了,还有那设在水道石缝中的猫耳洞,整箱子的雷被冲散,(当然也有不少罐头),于是山下的那条河就成了雷河。那雷不仅能顺流而下,还会逆流而上。
河里的雷群顺着水流冲得很远,几里之外还有撞响雷时见到的水柱,再往前就不知道了,河从哪里流出国界,雷也就从那里走向了世界。
敌人冒着生命危险偷偷过来埋下的那些地雷,也将从这里物归原主。
有一条山泉汇成的小河,平时水很小,所经之处,常有十几米到几十米的落差,形成多处瀑布。
最有气势的是在某公路边,那瀑布从石壁上倒挂下来,下面就是一座石桥,水珠总是把石桥溅得很湿。
到了雨季,这瀑布就变得很有气势,很远就听到了哗哗的水声,瀑幅一下宽到了十几米以致几十米。
那瀑布中以常会席卷着地雷滚落下来,在崖底发出清脆的炸裂声,只是瀑布水声不断,使这地雷的炸声显得不那么震耳。
这崖下的桥很重要,一直有岗哨。也流传着不少惊险的故事。说敌人特工为了炸这桥,化装成老百姓,赶着牛过桥,牛背上的柴草里装着炸药,到了桥上,那赶牛的便走开了,守桥战士立刻鸣枪,牛惊了,奔跑起来,刚跑过桥,就炸了,牛炸得粉身碎骨,桥没事。
雨季到了,瀑布变得凶猛起来,溅到桥上的水在流淌。
溪水携着泥沙到这里跌落。
突然有一天,那石桥处轰轰的响起了爆炸声,地下与空间都在传着这巨大而沉闷的声响,有人说那是天上的雷鸣,也有人大喊一声〃不好!〃再到石桥上去,才发现那石桥竟然被炸坏了一大块,碎石飞出很过远,连栏杆都不知飞到哪里去了。人们能估计出这需要多少梯恩梯炸药才会炸出这个效果。
人们看出来了,那天兵天将便是洪水瀑布,它们携带着人类赠与的无数地雷,横冲直撞。
满山遍野的地雷滚动了,汇入那暴涨的小河,那一道道的雨裂沟中露出了深埋的地雷,圆圆的,象鹅卵石那样经过千百万年大自然的磨砺才成为适于滚动的卵状,地雷天生就是卵状的,适应滚动的。象是服从天命的一群的士兵,一声令下,便到那低凹的翻滚的河流中来集合,顺着激流,排成多路纵队,雄纠纠地向前开赴。有的站队了,淤积了,一股激流,一个旋窝便又把它们卷起,加入那开进的雷大军。
那水无可阻挡,那雷也无可阻挡。
水流到哪儿,雷就滚到哪儿。
这流动的雷的大军终于来到了这悬崖边上,它们跌下去了,起先还是连续爆响,终于那么多雷一起跌落,轰隆,轰隆,那爆炸声压倒了瀑布发出的声音,看不到哨烟,看不出溅起的泥土,但那雷的大军一起爆炸的力量,竟将那石桥炸伤了。
还有那无数没有爆炸的雷,在水中翻滚,随着泥沙一起向前冲去了,冲向深沟,冲向前面的开阔地,也冲向河床。在这里,地雷犹如地球表层的癌细胞,在随着河流的血管扩散,再扩散。
上一页 目 录 下一页
第十二章
52。八百个蜜月加起来不满三百个足月
看见了,那是他的家。那儿,是她的家,也看见了。她在干吗?三排长入神地看着车窗外头。他看不见他们的家。他们还没有家。当兵的成了家也依然没家没业。兵车向南飞驶着。二排长想着他那新婚半月的妻子,担心着她那瘦弱的身子,一米六六的她毛重才九十斤,风一吹象要倒。他同时为自己的弱肉强食而内疚。她的家也看不见了。她在干吗?最后那一晚上,真委屈她了,真不好意思。他们谈了四年多,可结婚太仓促了。一说打仗,都凑开了热闹。此一去生死未卜,干吗非先找上一个不可呢?他觉得还是不该结婚的,可还是结了。部队那一阵到处都是结婚的,甭说招待所,连菜地连猪食棚连库房连作坊,所有的房子都住满了。新婚的和老婚的,领证和的没领证的,都往一块住。他给更新的结婚的战士让了房子,动员她回去,她哭了,说什么也不走。他们的蜜月才半个月,这一别又是〃君今往死地〃,他也没法劝了。真委屈她了,住到了连队的大会议室,还没炉子。到晚上,四班副又成了新郎,没地方找房子了,也在会议室凑合吧。对角上一个角一对。最后那一晚上,象集体宿舍,真不好意思。四班副那边又是新婚第一宿。有什么办法,灯一灭,动静小着点儿吧。办完事,渐渐觉得冷了。换得再紧捂得再严也还是冷。睡不着。就是不冷本来也睡不着。睡不着又不能说悄悄话。听听那边,他们也没睡着。不知道忍了多半天,他发话了:〃四班副。〃〃到!〃这一声四个人都乐了。〃冷吧?〃〃真冷。〃〃睡不着?〃〃睡不着。〃〃外边月亮挺亮。〃〃是挺亮。〃可真冷。〃〃是挺冷。〃〃一冷又显着黑了。〃〃黑点儿好。〃〃还是亮好。〃好什么,一亮咱们就全曝光啦。〃〃干脆起来聊会儿天吧。〃〃聊吧。〃〃哎,等会儿开灯,我们这口子还没穿好呢。〃灯开了,大会议室,对角上,一个角一对,穿着衣服又披着被子,四个聊起天来。
团里的集体婚礼上,新娘代表发言最来劲,她说,军人就是最可爱的人,说理解信任,说一千道一万都没用,现在马上结婚才是最实际的行动。全场都给她喝彩。
那个团的集体婚礼,新娘家代表是唐山东省姑娘,念着念着理解支持的讲稿,忽然冒出一句,地震没砸死,这回又上前线,呜呜地哭开了,一下子没人说话了,新娘子们挨个抹泪。
那个连的炊事班长才有意思呢,他八三年和原来对象订的婚,一说打仗女方吹了,结果他的家乡又出了个见义勇为的姑娘,先来信自报家门,接着就到部队来了。本来姑娘就是想打抱不平,安慰看看这老炊,可指导员故意拿话激人家,说现在可不能结婚,一结就连累你了。姑娘一听,说结就结,好让他放心上前线。第三天就在连队举行了婚礼。听说那姑娘叫沙志红。
说着说着,两对新人又来了情绪。排长的她天亮就要走,;四班副那一对还是新婚之夜。又闭了灯,双轻手轻脚地。这叫什么事吧。一打仗真什么也不顾了。二排长叹了口气。真委屈她了,那最后一晚上。兵车还在向南飞驶着。
一位团政委说,为了让大家安心上前线,我们为十六对新人组织了集体婚礼,团里各级主官都参加,拍录相,发纪念品,把声势搞得大大的,战士们很感动,说一辈子也忘不了。我们的老兵多,都二十二、二十三了,再打两年仗,都成了困难户。二十四岁以上的还有一百零九个没对象呢。我们想办法吧,有苗头的就抓住。有的姑娘就是到部队来看看对象。一看这场面这气氛,咱们也结。团里搞完,营里连里统统搞,一共组织了六十多对。我们就是要通过这些来告诉人们,尽管是打仗了,也还是结婚的多,吹灯的少,理解的多,不理解的少,就是要告诉大家,你们仍然是最可爱的人。
一道参战命令,使集团军近八百多官兵成了新郎。
八百对新婚夫妻的蜜月有长有短,长的不到一个月,短的十天八天一个星期。侦察参谋齐华林结婚第三天就被电报召回部队,开进经过西安时,妻子和岳父、岳母都到车站送行。在站台上,她转着泪说她害怕,总梦见唐山地震。齐参谋是地震孤儿,一家六品人,父母弟弟和两个妹妹那次全没了,就剩他一个。临开车,老丈母娘说,唉,我们娘俩一个命,老头子就是我们结婚第三天上的朝鲜战场。工兵连指导员张建国晚上八点钟赶回河南老家,骑自行车带着未婚妻到县政府敲开秘书的门办了手续,晚九点入新房,第二天早晨七点登上返回部队的车,结束了为期十小小时的蜜月。
八百个蜜月加起来,不满三百个足月。
参战部队有两个突击:突击结婚的多,未婚妻突击吹灯的多,集团军有了八百新郎,同时也有了两千多名〃吹灯兵〃。
在战区,到处都可以听到这样的故事,各级政工干部似乎尤其注重这一点,对之都有精确的统计数字,然后再向你谈几个曲折的或者感人或者令人愤慨的事例。临上前线突击结婚,说明我们战争的的正义性质和群众基础,说明后方人民的理解的支持,说明八十年代战士最可爱;而众多的吹灯兵在前线出生入死忘我战斗,则说明当代军人负重报国,说明新一代士兵的高尚情操,说明他们更可爱。
19号阵地25个兵,平均年龄22岁,没有一个结婚的,自称〃光棍阵地〃。光棍阵地上原先还有五六个有对象的,一说打仗,尤其是一上阵地,就一个接一个的吹灯,最后只剩下了李广才。光棍们都把他的她看成是全阵地的唯一希望,而李广才自己,一方面很自豪,同时又多少觉得有点对不起大家。对象是他的中学同学,并且在第二汽车制造厂上班。部队临出发她要来看他,他没让她来。她来信说上前线才是真正的男子汉,我在后方支援你。上阵地后,李广才给她写信,没说是在全团最前出最危险的阵地上,交防的友军在这个阵地上坚守期间,平均一天伤亡一个,这些当然不能告诉她,不能让她更提心吊胆;。但阵地情况李广才写信告诉了同学,也终于传到了她的耳朵里。李广才从一上阵地就盼信,盼了两个月,她的第一封信终于来了。信中说你们是了可爱人的,有更多的好姑娘在等着你,咱们分手了你别有包袱。这信不仅对李广才,对全体光棍都如同一记闷棍。光棍阵地悲哀了:咱19号算是没戏了。光棍阵地愤怒了:妈的回去哥们儿替你找她算帐。都吹了,光棍阵地这回是名副其实在铁杆光棍了。没有了后顾之忧,老越来吧,来了光棍们就猛干,总想过过瘾。不过李广才和她还通着信,她告诉他,她春节结婚了,是厂里的,他于是向她祝贺。此举虽然招来光棍们的一致谴责,李广才却说,我们毕竟爱过一场。
最使前线官兵痛苦的事情莫过于吹灯。这些战场上的男人们最恨的就是负心姑娘。即使敌人似乎也不曾使他们那么痛苦,即使敌人似乎也不曾让他们那么愤怒。
吹灯,指的是中止恋爱关系,而且通常是一方还热着,那边已经绝情了。只要有谈恋爱地方,就会有吹灯现象。在参战部队,吹灯的更多更集中些而已。但吹灯一词,无疑是个极有中国特色的字眼,它所包含的社会心理内容,它所体现的文化伦理背景,都是中国式的。
吹灯本身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恋爱关系不象结婚那样可以明确地以证为准,再者恋爱过程极易出现反复,一句吹灯话一封吹灯信,也许是分离的起点,也许不过是个小小的波折或大大的玩笑。多少多少个吹灯兵这种统计数字肯定会有许多折扣在,当然也有确定了的,比如欠灯信同时就告诉过去式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