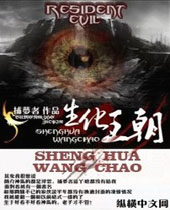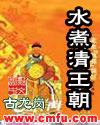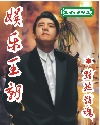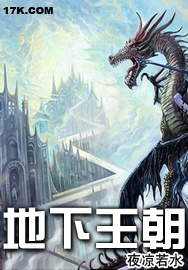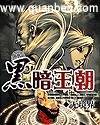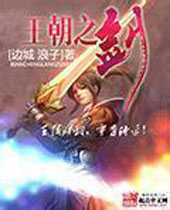十大王朝的最后时刻:帝国不语对枯棋-第1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唐穆宗则是个典型的享乐型皇帝,在他三十岁时就把一生的时光都透支完了。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他短暂的一生都在寻求长生不老之道。
唐敬宗也是个享乐型皇帝,他是娱乐至死的范例,十八岁时死于打猎回来的一个深夜,弄死他的是一群整天围着他转的宦官。
唐文宗好像深刻地意识到了大唐的危机感,发誓要跟他的前两任享乐型皇帝划清界线,他一生着力于藩镇、朋党、宦官之事,用心不可谓不深,到头来却一无所成——唐王朝到了他那个时代,已然是烂泥扶不上墙了。
同样对国事孜孜以求的还有号称小太宗的唐宣宗。他有一个座右铭,叫“至乱未尝不任不肖,至治未尝不任忠贤”,还把《贞观政要》写在屏风上,“每正色拱手而读之”。客观地说,在晚唐的衮衮诸君中,唐宣宗用力最巨,收效也最大,但只可惜,这是一个王朝最后的回光返照,因为在他死后仅半年,浙东就爆发了裘甫起义。这次起义成了唐末那场著名大起义的先声。
唐王朝到了唐懿宗时代,一切已是尽人事,听天命。唐懿宗晚年最用心做的一件事就是恭迎佛骨。这位看上去有些杯弓蛇影的皇帝打心眼里希望佛祖降临人间,来拯救这个快走到三百年的大王朝。
但是一切的一切都来不及了,因为那场致命的农民运动正在呼之欲出,正在以不可遏止的激情喷薄在这个苍老得快失去记忆的王朝上空。
第102节:黄巢怀才不遇
黄巢怀才不遇
黄巢已经怀才不遇好多年了。
曾经,这个山东汉子是想报效朝廷的——他几次三番参加科举考试,可朝廷没看上他。
在唐王朝,像黄巢这样试图以科举博功名的有志青年何止千万,但朝廷能看上眼的只有一小撮。
黄巢注定和绝大多数落榜的有志青年一样,从哪里来回哪里去,该干嘛干嘛。
他回到了山东曹州冤句老家,干起了贩卖私盐的活——黄氏家族从事这种违法活动已经好多年了,他爷爷的爷爷当年就靠这个谋生。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人生苦旅中,黄巢的命运设计不可能有什么偏差或奇迹发生。
如果他的后代没有足够的智商和运气,毫无疑问,黄氏家族子子孙孙的生活只是对其祖辈生活的简单克隆。一旦被官府抓获的话,他们可能活得更惨。
有志青年兼私盐贩子黄巢的内心突然有了一个冲动。他想改变自己的命运设计,如果成功了,他的子子孙孙的生活将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将不再是私盐贩子,而是国之栋梁,甚至有可能成为国家领导人。
当然,如果失败的话,黄巢将要接受命运的残酷惩罚,这是一个人的冲动直面无可奈何的时代时所必须承担的代价。别无选择。黄巢别无选择。
他终于造反了。
黄巢造反的故事在很多年后的今天依然被津津乐道。
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黄巢成功了。他让唐僖宗像当年的唐玄宗一样惶惶如丧家之犬放弃长安出逃巴蜀。他带领他的部队浩浩荡荡地开进长安,豪迈地在这个古老的都城宫廷里宣布:旧时代已经过去,新时代即将来临。黄巢还亲自为他的新时代命名为大齐,并改元金统。
但是仅仅四个月后,被赶出长安的唐王朝用它最后的力量对大齐政权进行了反扑。黄巢的成功成了昙花一现,他最后在离他家乡不远的地方拔剑自杀——这个人终于没能彻底改变他自己和他子子孙孙的命运。
但是,黄巢却改变了唐王朝的命运。对本来就已摇摇欲坠的唐王朝来说,黄巢施加到它身上的生命冲动无疑是致命的。因为仅仅二十五年之后,历史上最著名的王朝之一——大唐王朝就彻底死翘翘了。
第103节:玄宗之后无大唐
只是对于黄巢来说,这一切已经无关紧要了。
玄宗之后无大唐
在玄宗之后,唐王朝的皇帝很少活得有尊严的。
宦官当权、藩镇割据、民间起事,玄宗之后的一百多年是皇家尊严扫地的一百多年。
唐玄宗和唐僖宗虽说做了背井离乡的皇帝,但好歹还是皇帝。
唐昭宗做的简直就不是皇帝了。
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仗着平定黄巢有功,明目张胆地要扩大地盘,并且向云州发起进攻。
唐昭宗大怒,宣布免去李克用河东节度使的职务。宰相张睿也大怒,发誓要宰了李克用这个狗娘养的。
但很可惜,磨刀霍霍向克用的结果是李克用把刀架在了唐王朝的脖子上——唐王朝对李克用的兴师讨伐以失败告终。唐昭宗第一次尝到了他作为一个末世皇帝的屈辱:在李克用的强硬要求下,宰相张睿被贬为外官;并且他宣布恢复李克用河东节度使的职务。
第二个让唐昭宗尝到作为一个末世皇帝屈辱的人是凤翔节度使李茂贞。这个人居功自傲,一点都不把唐昭宗放在眼里。在唐昭宗作出有限的反抗之后,李茂贞竟带着他的凤翔军向长安扑杀过来。无可奈何之下,唐昭宗让宰相杜让成为替死鬼,并加封李茂贞为山南西道节度使。李茂贞这才带着他的凤翔军骂骂咧咧地离去。
但没过多久,李茂贞又联合其他节度使再次杀到长安,这一回的替死鬼不仅有宰相韦昭度,甚至还有唐昭宗本人。李茂贞等准备废了他改立吉王李保为帝。皇家尊严扫地的唐昭宗竟然想以毒攻毒,他乞求李克用救救自己,救救他这个风雨飘摇的皇帝。
李克用也终于来了。
在这样的乱世,一切都是利益的考量。李克用来是正常的,不来是不正常的。
但是在这样的乱世,没有谁是唐昭宗的保护神。在接下来进行的权宦与节度使的角力当中,唐昭宗变成了利益双方角力的砝码——他沦为了他们手中的一个棋子,在输赢胜负之间被一遍遍地过手。直到最后,他成了朱温手中的傀儡皇帝——大唐这个王朝走到这般田地,一切都已是板上钉钉了。
唐昭宗最后死在洛阳,死状极为狼狈。他为了躲避刺杀,半夜时分穿着单衣满大殿地绕柱逃避。刺杀他的人是朱温派来的。朱温认为,这个王朝的气数该尽了,一个属于他的时代该开始了。他任命自己为梁太祖,并且开始一脸威仪地坐在龙椅上,雄视天下。
而遥远的长安,终究化为一片废墟,历史不由分说地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大唐,一个伟大的时代,至此——
寿终正寝。
第104节:不改革是不行了(1)
北宋:
那一场无人喝彩的改革
不改革是不行了
趴在历史的门缝边缘,看一个王朝的花开花谢、盛极而衰,最明白的看法是从它的开场看起。
其实,北宋这个王朝的开场是非同寻常的。
就像京剧舞台上的亮相,赵匡胤一上来走的就不是常规的路子。他半推半就地让那件黄袍披在自己身上,咿咿呀呀开唱一段霸王戏,一个王朝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开张了。
好在赵匡胤的全局控制能力比较强。他带着赵式的非典型性思维,带着陈桥那些有功之臣的理解与不理解,急中生智地演绎了杯酒释兵权,强行“排除”了一个帝国臆想中的危机。这样精彩的桥段,看客是不得不齐声叫好的。
当然看客始终还是捏着一把汗。因为真实的危机依旧存在。西夏、契丹还有南方的那些小国,在随后的五十多年里,它们一直像定时炸弹一样,时刻挂在北宋的头部、腰间以及其他敏感部位,令这个王朝到底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只是这些,演员赵匡胤都已经无暇顾及了。作为一个开场的头角,赵匡胤可以说不落俗套地完成了他的表演。这就够了。至于他的子子孙孙们能不能将戏接着演下去,并且演好它,这要看他们的演技如何。他赵匡胤是不想管也管不着了。
没想到接下来出场的是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以及他的皇子皇孙们。他们依次出场,开始了中规中矩的表演。但是他们的表演大多乏善可陈,看得看客们昏昏欲睡,直到公元1068年,十九岁的宋神宗坐到了这个位置上。
第105节:不改革是不行了(2)
宋神宗时代的北宋已经是内忧外患了,但是十九岁的宋神宗却想有所作为。
因为十九岁是激情洋溢的年龄。
也是天地任我行的年龄。
年轻的宋神宗充满豪气地问年长的宰相富弼:国家怎样才能富强?边患何时可以尽除?富弼却向他叹气:皇上刚刚即位,应该布德行惠,这个国家二十年之内最好不要打仗。因为打不赢也打不起啊。
宋神宗刚开始不明白,但很快他就明白什么叫“打不赢”和“打不起”了。因为国家军队里到处都是注水兵,所以“打不赢”。那什么叫“注水兵”呢?“注水兵”说起来由来已久,北宋一向执行“荒年募兵”政策:荒年时饥民激增,为了不让这些饥民造反,政府决定花钱买平安,把他们都收编为军队,但他们光吃粮不打仗,便形成了“注水兵”。神宗时的国家军队多达一百五十万人,却基本上没有什么战斗力,稍有战斗力的都派出去布防西夏、契丹还有南方那些小国的进攻了,剩下的就只能靠国家养着;而“打不起”是因为国库里没钱了。国库里的钱主要是两大用途,一是养兵,二是养官。“养兵”上文已述,这里说说养官。北宋的官员队伍比较庞大。真宗时有一万多人,到仁宗时就达两万五千人,最后到神宗这儿就突破三万了。虽然政府几次喊着要精减干部队伍,可每次精减过后,人数不减反增。庞大的官员队伍使北宋的财政负担不堪其累,再加上特权阶层合理避税,国库要不空虚那是不可能的。
宋神宗真切地感受到,历史走到了一个拐点上,不改革是不行了。
只有坚持改革,北宋才有出路,如果闭着眼睛再继续将局面往下拖,内忧外患一旦激变,这个先天不足的王朝很容易就这么死翘翘。
但是改革就能救国吗?北宋的改革说起来也不是自神宗始。若干年前就有范仲淹改革了。但范仲淹是个谨小慎微的人,他的体制内太极拳根本就掀不起什么波澜,很快地,他就收手了。仁宗时代的包拯则以三司使总领的身份厉行改革,他在调查了全国范围内土地兼并情况之后,提出要重新丈量土地的口号,目的是让大地主大权贵们如实交税。但是包拯的口号没有被落实,这个喜欢使铡刀的铁面高官痛苦地发现,很多人对他的改革举措阳奉阴违。大地主大权贵们团结起来跟他干,而仁宗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结果包拯的改革无疾而终——他的铡刀再锋利,也铡不了一个国家的软弱和彷徨。
第106节:不改革是不行了(3)
由于改革总是雷声大雨点小,总是以激情始以党争终,从而成为了官场生态新陈代谢的促进剂,于是北宋王朝的改革在神宗时代就成了一个人人避谈的关键词。只有神宗自己还对它充满极大的热情。
这个时候,王安石开始声名鹊起。
王安石是改革派的理论大师,以大谈改革为荣,以墨守成规为耻。
最重要的,他有白眼向天的性格。一向生活在理想和逻辑世界当中,追求完美,不通人情世故,也不屑于人情世故。
这样的性格,神宗喜欢——因为一个过于讲究人情世故的人,是不能做改革者的。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神宗的性格和王安石的有点像,喜欢充满激情地做一件看起来很美的事。
所以,神宗有意向要让王安石来主持改革大计。神宗为稳妥计,问宰相韩琦,王安石当宰相怎么样?神宗问韩琦话的时候后者正在打点行李。这个三朝元老在以前的N次改革当中当了很多次替罪羊,这一次,他一听神宗又要改革,头都大了,死活要告老还乡。神宗留不住,只得准他辞职。但没让他还乡,而是安排他做相州节度使。毕竟是老干部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对他一撸到底不合适。韩琦停止了动作,抬起他饱经沧桑的双眼,一字一句说了以下这句话:王安石为翰林学士有余,居宰辅地位则不足。
若干年后的事实证明,韩琦那饱经沧桑的双眼没有看走眼,王安石为人处世的性格更多时候是适合做一个改革理论家而不是实干家,但当时的神宗哪能看透这一层。他只以为韩琦这么说是酸葡萄心理在起作用,不能理性、冷静地评价他的后继者——神宗确实想对王安石委以重任。于是,他又找到老宰相曾公亮,要他说说对王安石的看法。曾公亮说:安石真辅相才,心不欺罔。
神宗这下高兴了,看来大宋王朝还是有心明眼亮之人,有有容乃大之人。他在心里暗暗下决定,曾公亮可以留下来,和王安石一起主持改革。志同才能道合。曾公亮和王安石,应该是志同道合之人。
第107节: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四面楚歌(1)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四面楚歌
在文人扎堆的北宋,王安石的名声一向淹没在司马光、欧阳修、苏洵甚至苏轼等人中间,更别提年长于他的范仲淹了。
但是公元1069年,王安石就像一颗大慧星,拖着长而明亮的大尾巴呼啸而来,搞得北宋政界、文坛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这一年也是熙宁二年,王安石四十九岁。在经过近一年时间的考察和考虑之后,神宗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主持改革大计。
但是神宗万万没有想到,即便在他的委任状下达之后,反对王安石的声音依旧此起彼伏。
首先出来反对的是当年以弹劾文彦博一举出名的非暴力不合作者唐介。唐介说王安石“虽好学却泥古不化,议论迂阔而不切实际”,这样的人出来改革,天下要为之大乱。唐介此时的身份也是参知政事,和王安石同级。这两个人如果不和,改革注定要胎死腹中。想到这一层,神宗的头都大了。为了力保王安石,神宗决定对唐介所说的任何话都如风过耳。唐介见说不动皇上,就跑去找曾公亮。曾公亮刚开始无动于衷,但不久之后他就被说动了。几个月后,曾公亮和王安石说再见——他要告老还乡。曾公亮走之前对神宗说,我钦佩王安石的为人,但我反对他激进的改革,所以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