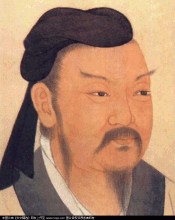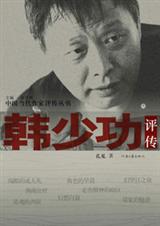刘裕评传-第2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么,后秦割地这件看起来很荒谬的事,为何会发生呢?因为此事的年代已经很古老,当事人姚兴又没有留下回忆录,要确切知道他究竟是怎么想的,已经是件几乎不可能办到的事,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对当时局势与姚兴个性的分析,做出我们的推测。
首先,在下先将查找到的几种常见的解释列举如下,供朋友们分析对比:
第一种解释,姚兴自己说的,他在学雷锋,具体内容已见上述;
第二种解释,姚兴此时进取之心已失,诚心诚意愿与东晋实现睦邻友好关系,为此不惜作出重大让步,用今天的话说,这叫“以土地换和平”;
第三种解释,姚兴畏惧刘裕的威名,不敢和刘裕开战,同时又顾忌到北魏和西北诸凉国的威胁,只好学习曾文正公,“打落牙和血吞”,忍一步海阔天空。
然后,让在下来分析一下这几种解释。关于第一种解释,我们就不说了,供相信“世界充满爱”的朋友们选择。不过估计多数朋友还是和在下一样,认为世界还没有发展成共产主义,还不可能“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姚兴是一个政治家而不是慈善家,所以他第一项解释的真实合理性不会太大。
那么第二项解释呢,姚兴是否诚心与晋朝交好?以在下看,恐怕未必,他的诚意也是打了折扣的。最明显的证据有两条:一、是收留桓谦等晋朝特级通缉犯,不但不予遣返,反而严加保护,并在后来为桓家人东山再起提供了不少便利。二、是接受谯纵的称臣,并在后来多次出兵帮助谯蜀抵抗晋军,这就像老美一边声明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一边又派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一样。
再看第三项解释,此时的姚兴是否害怕刘裕?以在下的观点看,如果让刘裕与姚兴在大致相当的条件下打一仗,那姚兴几乎是输定了。但这毕竟是在下的观点,不是当时人的看法,而姚兴是不会以在下的看法作为决策依据的。刘裕此时在晋朝,虽已是无可匹敌的名将,但尚未与北方各国打过仗,不可能有太大的国际声誉。从后来刘裕北伐南燕,慕容超敢于选择放晋军过大岘的下策,以及姚兴在后秦的战略势态大大恶化时,为救援南燕,仍敢对晋军以战争相要挟来看,认为他现在就会因为害怕刘裕而不惜大放血,恐怕是不够客观的。
而且,将帅的指挥才能虽然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在古代甚至可能是主要因素,越靠近现代,因技术落差的拉大,将帅在战争中的重要性不断降低),但毕竟不是绝对因素,还有众多的外部因素也会对战争结局产生影响。
而从外部环境来看,此时的姚兴较之刘裕仍有优势。柴壁之战后,北魏与后秦的关系逐渐好转,已由后秦的现实威胁转为潜在威胁;后来让姚兴挥之不去的梦魇——刘勃勃(即后来的赫连勃勃),此时还在后秦做他的安远将军;至于陇西诸凉,此时也都还在后秦面前恭顺地摇着尾巴,后秦所处国际环境目前还不坏。相比之下,刘裕领导下的晋朝建康政府,处境要糟得多。在外不但巴蜀与岭南丧失,后秦、北魏和南燕也都在不时骚扰着晋朝的北方边界;在内,大乱之后,百业凋零,在领导层内部,刘裕与刘毅和司马皇族的矛盾又渐渐明显化。内忧外患并作,可谓危急存亡之秋也。总之,姚兴不该怕刘裕。
姚兴割地下
可能有朋友要问了:既然一二三项都让你否定了,那你认为姚兴犯的是哪门子迷糊?那么在下就对此事进行一番自己的推测。因为是推测,仅供朋友们参考。
推测之前,我们可以先确定一点:土地是好东西,它可以脱离国家存在,而国家不能脱离土地存在,它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的强弱。本朝太祖曰:“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尽折腰!”古代那些名君雄主们,从秦皇汉武,到一代天骄,从亚历山大,到奥古斯都,征战不休的最大原动力,正是为了这玩意儿。
和土地密切相关的国家另一基础资源,是人口。在古代自然经济的条件下,人口的多少与国力的对应关系甚至超过国土的大小。因为在这两项基础资源中,国土是死的,人是活的,国土大的优势,正在于它能够容纳更多的人口,国家的财富最终是要靠人生产出来的,国家的武装力量也要从民众中征发。在一定的经济文化条件下,拥有更多的人口往往也就意味着拥有更多的财富和更强大的武力(注:以上推论进入近现代后不再适用),所以古代的统治者们无不把地广人众视作国家富强的象征。
然而,凡事都没有绝对。国家的领土并不总是越大越好,人口自然也不总是越多越好。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人终究是有独立思想的生物,并不是没有思想的工具,由于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等冲突的存在,一个国家拥有的人口中总会有一定数量的“负人口”。所谓“负人口”,是指这样的一部份人群:他们对现有的国家政权缺少认同感或缺乏忠诚度,他们的存在不会对国家产生助力,相反具有对国家的破坏力,国家还得花相当的人力物力甚至军队来防备他们,所以他们对国力的影响是负数。正人口和负人口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政治的清明与否、灾荒或是丰收、文化的冲突与交流、乃至于民族融和或种族清洗等,都会对正负人口的转化产生重大影响。例如明朝末年,人口数超过一亿,比周边任何国家都要多得多,这本是强国的象征,但由于明末苛重的税费加上频繁的天灾,将大量民众变成负人口:流民遍地,处处揭竿而起,他们对明政府的打击甚至大于外敌满清。
土地也是同理。如果在某个地区,它的居民大部份是负人口,或它的位置处在强大外敌威胁之下,易攻难守,使得国家为保卫这块土地付出的成本大于得到的收益,那么这块土地就变成国家的“负领土”。同人口一样,正负领土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但这需要巨大的投入,也不一定担保成功。如二战后,英法等原殖民大国之所以肯从它们的大部份殖民地撤出,就是因为那些殖民地已经变成它们的负领土。
在引入了负人口和负领土的概念之后,我们再来看姚兴的作法。姚兴所割十二郡的完整版本在下一直找不到,就知道的其中四郡来看,全部地处今天的河南省南部,距离后秦的政治中心长安较远。而且这些地方在十六国时代,多数时候是晋朝领土,其民众并不太习惯异族的统治,对后秦的忠诚度估计很低,换句话说:这十二郡是后秦的负领土。
虽然是负领土,但若遇上如后来北魏拓跋焘那样的君主,也绝对不可能退让,因为负领土是可以转化成正领土的,纵然不能转化,也可以作为保卫正领土的屏障。但姚兴自柴壁之败后,显然进取之心已失,其国家战略转向全面收缩:放弃国力难以承受的边远地区,集中力量保护后秦核心区域,以减轻国家负担。
要证明这一点并不困难,因为这并不是姚兴唯一一次主动割地。就在第二年六月,南凉主秃发傉檀向后秦进贡了三千匹马和三万只羊,姚兴便主动将后秦占有的陇西第一重镇姑臧(今甘肃武威,前凉、后凉均建都于此,南凉得到姑臧后,也迁都于此)割让给南凉。我们固然可以用事后诸葛亮的观点,认为姚兴不敌刘裕,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后秦会不敌南凉。姚兴割姑臧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姑臧城孤悬于外,几乎处于南凉和北凉的合围之中,一旦有变,守之甚难。
不过,姚兴的做法虽有一定道理,他却疏忽了一条原则:在生存竞争激烈的乱世中,你退一尺,则人进一丈!靠消极退让是不可能赢得长治久安的。这次外交博弈的结果,晋朝兵不血刃,就收复了十二郡土地,让刚上台不久的刘裕威望大增,大大加强了他的执政地位,今后不管是对外北伐,还是对内整合,都增加了不小的筹码。从这个角度上说,不管姚兴割地的动机是否纯正,他都可算刘裕的恩公之一,对刘裕一生的功业,助力着实不小。
不过刘裕的为人我们是清楚的:政治利益高于一切,只要成为他前进的拦路虎,刘寄奴绝不会在乎你是否对他有恩!厚道的姚兴白白地助人为乐,最终也未能给子孙换来平安。以后的史实证明:与刘裕作邻居,实在是姚家的大不幸,后秦虽然用大放血的方法躲过了初一,但终究没能躲过十五。姚家即将迎来的,不仅是亡国,还有灭门!
穆之献策上
义熙三年(公元407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建康的政坛发生一次重大变故,刘裕的政治盟友,司徒、录尚书事兼扬州刺史武冈侯王谧逝世。如果放在今天,起码也得在CCTV向全国人民发表讣告: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久经考验的有产阶级战士,著名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王谧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XX年XX月XX日XX时XX分逝世,享年四十七岁。王谧同志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战斗的一生……然后全国暂停娱乐节目,下半旗致哀等等(这自然不会妨碍刘毅等人偷着乐)。
但要弄清楚这件事对晋朝政局的冲击有多大,我们最好先弄清楚王谧的官究竟有多大?他在中央政府的位置究竟有多重要?
这其实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说它简单,是因为王谧的职务史书上记载的清清楚楚,说它复杂,是因为这些职务所代表的实际职权并不是固定的。
两晋南北朝,是中国的政治架构由三公九卿制向三省六部制变化的过渡阶段,人事制度最欠缺的就是规范化,乱七八糟的各种官职和将军号很能让人眼花缭乱。对王谧最重要的三个职务大致可以这样解释:司徒,是名誉宰相;录尚书事,是实质宰相;扬州刺史,扬州省长兼首都军区司令。
因为很难用现今的职务作类比,在下估且用大家比较熟悉的晚清官职说明:王谧的官大致相当于XX阁大学士、入值军机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就是晚清声名赫赫的重臣李鸿章,也没做到这么大的官(李鸿章为大学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一生未入军机处)!
不过在这里,我们又得引入另一条常识:历史上,职位与职权经常是脱钩的。如果你以官职作为证据,认为王谧在晋末的位置比李鸿章在晚清更重要,那就大错特错了。王谧本身虽有名望,但并无实力,他和刘裕的关系如同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那曲《歌唱祖国》:王谧像林妙可一样站在前台表演动作口形,但真正发出声音的,是坐镇京口的刘寄奴和他的谋士刘穆之。两相配合,使得建康新政府既好看,又好听。
但现在,这种两面光的政策执行不下去了。王谧的死,对刘裕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他此后再找不到这么合适的士族代言人,王谧留下的空缺如果让别的士族名士来顶替,刘裕将很可能丧失对中央的控制,因为现在晋朝的实力派人物并不只有刘裕一人!
穆之献策下
另外这些实力派人物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左将军兼豫州刺史、南平郡公刘毅。面对突然到来的变化,这位**怀大志的刘希乐在竭力压制住内心喜悦同时,早已料定:这个机会,走过路过,不容错过!
虽是良机,对它的使用也是需要很高政治技巧的,一定要拿捏到位,不能刺激到刘裕的神经,以免弄巧成拙。经过精心的盘算,刘毅向朝廷提出两套方案:一、由琅琊王司马德文担任司徒(反正司徒已经退化为荣誉衔,让皇族担任无碍),由中领军谢混接替王谧其他的职务;二、仍是司马德文任司徒,谢混录尚书,扬州刺史则授予刘裕,不过刘裕可以坐镇京口遥领,好发挥强项,为国家捍卫北疆,不用入京,扬州刺史的对内职责由孟昶代理。提出两套方案后,刘毅等人也显得非常谦逊,不敢擅自决定,派尚书右丞皮沈携带方案,前往京口请刘裕选择。
从表面上看,两套方案都可谓合情合理,谢混论门第,论声望都最合适接替王谧,而且两条建议似乎都没刘毅自己什么事,他摆出的是一付一心为公的高风亮节。但在实际上,不管刘裕选择方案一还是方案二,刘毅都是包赚不赔的:刘裕的势力都将被悄悄地从中央挤出去,换上他的盟友。
不过,刘毅的计划尽管很高明,他还是疏忽了一件事:这个世界上的聪明人,并不只有他刘毅一个。
义熙四年(公元408年)正月,皮沈到达京口,他首先见到的人,是刘裕的记室录事参军刘穆之。皮沈向刘穆之传达了廷议的结果,刘穆之听罢,假装要上厕所,请皮沈稍待。一到厕所,刘穆之悄悄写下一纸便条:“皮沈来了,他说的话千万不可以同意!”,然后遣人送给刘裕。过了一会儿,刘裕出来接见皮沈,不谈正事,尽打哈哈,一番你好我好天气好的客套之后,就打发皮尚书去馆驿休息。然后再召刘穆之前来询问商议此事:“你说皮沈的话不能听,是什么意思?”
刘穆之先向刘裕分析了此时的政局,预测时势的变化:“晋朝失政,非止一天,再加上桓玄篡夺,天命已移。以公今天的功勋、声望、地位,怎么还可能谦让处下,只做一个守边将领?刘毅、孟昶这些人,与你都是布衣起事,共建大义,同为谋求富贵。只是举事之时有先后,为求成功故推你为首,但在心中他们始终视你为同僚而不是上司,并不会对你心服口服,效忠于你。既然本非君臣,力量权势又相当,将来怎么可能不反目成仇,相互吞噬?(所以不可不早做准备)”把政治温情默默的面纱一把扯下,露出**裸的利益,而且一语中的,刘穆之确是个明白人。
接着,刘穆之提出对现实的问题的处理意见:“扬州是国家的根本重地,不可以假手于人,原先推让王谧,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如今如果再让出去,又没有第二个王谧可用,一旦在中央失去权柄,就将处处受制于人。以朝廷上下对你猜疑和畏惧,各种各样的诽谤和谣言必然交相而至,将来的灾祸难以估量!怎么可以不深思熟虑?只是他们已经抢先拿出了朝议结果,如果一定说要自己来干,不但不好措词,也得罪了全体朝臣,不是好办法。所以公不妨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