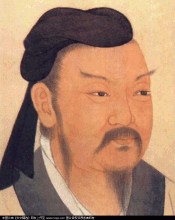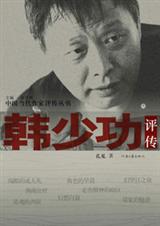��ԣ����-��47����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ɽ�ܵ����˵ľ۾������´�ҽ���Ĵ��ջ��Ϊ���굱��һ����������Ժ������������������꿤�����࣬�����ڳ���ǰ�����������˾����֮��Ԯ��˾����֮���ɽ��������ʾ��������ַ��֡�
���������������岿�䣬��������Ծ���Ӻ���ݵĽ���Ҳȫ��չ����������յ���ԣ������֮����������վ����ԣ��һ�ߣ�����Ϯ����һ��նɱ˾����֮������Ԯ���������塣��ɱ������֮����������û��Ѹ�ٱ��ϻṥ���꣬����ͣ�ڵ���ϴ��ɱ�Ӹ��������岿�䣬�ȳ����ַ��ƣ���������˽�����ʱ�䡣
����ڣ��ս��ʱ����ԣ��פ����ͷ��������������ڳ����ϰ���б�Ա����Ľ��꣩���ȴ���Ů���Ľݱ��������ǰ����ʦ����û�뵽�������û�е�����������ȴ��Ů����ɹѸ�����Ϣ�����Լ��������������֮����ôս���ˣ�ʹ�ĺͻں�����ԣŭ���ɶ����㲻�ٵ����귽��ľ��ӵ�������¶�ʮ���գ���������ǿ�ɳ����������������˾����֮��һ��ս��
����е�ǰ��˾����֮Ҳ��ȫ�����Ҷ�Ͷ�����ⳡ�༪�ٵĺ��ģ����Լ�����ս���㽫���ݱ�Ȩ��������˾����˼����ͬ³���Ӻ��Ԯ�������������������ֿ�������Ӻ��������ռ���˵������ڳ������������˷�����أ��ȴ�����ԣ���ַ�����
��������һ���ij��������ذ������ͱڣ�����ʮ�����ѣ���ԣ����ļ���ǿ������ʧ�����ۼ��з��������֣�ս���ϵ���ԣ����Խ��Խ��⣬�ڱ�ŭ�У���ԣ��һ����ս����ʧȥ�����ǣ���Ҳ���������Էֱ��ػأ������������ף�Ҫ����һ����һ�����ȣ��ʾ�ǿ�й�����
���������µ��˶�����������ڵ���ԣ�Ѿ������Ǹ������һ��ǧ��С���٣�Ҳ�����Ǹ��������ų���������лʸ������������ˡ���ԣ�����Ѿ���ʮ�����ˣ����Ը��ڵ�ʱ���ǵ�ƽ�������������Ѳ�������Ľý�������Ҫ���ǣ���������Զ�ȵ�����أ���ս������һ���ų�����һ����˾���ɵ�Ӱ���Ǿ�����ͬ�ġ����������ҵĽ����Ƿ�Ȱ�裬����ԣԽ����ŭ��˭ҲȰ��ס��
���������ʱ��һλüĿ���㡢������ŵ�������ͻȻ�Ӻ��汼����������ס��ԣ���������봬����ԣ��ŭ�л�ͷһ���������������̫ξ������л�ޡ�
��л�ޣ�����������л�����ֶ��ԭ�������������µ��ν������б��ξ���������ɱ��������ȻҲ���Ž�ɢ����ԣ��Ϊ���dz��ĺû��ᣬ�Ը�����֮˵�����㿴�����Ƹ���Ļ�ţ���ʲô�ܸɵ��˿������ҵĸ�������������֮������ԣ�Ƽ���л�ޡ�������λ��ù�����岻̫һ����л����ȻҲ�Ƕ�����ʿ���ӵܣ��������϶���ԣ�سɴ��£������������棬û�о���л��İ��ӡ�л�����Ƕ�ı������ǿ�ɣ����������ϰ�����IJ���������ԣ��ע�⣬�õ���Ρ���������������ʱ��������ֹ��ԥ���ݣ�����Ҳ�dz���ɫ���Թ������ƣ�����ԣ������ָ������������ƽ��������ԣ�����ء�
�����¿����������DZ�֤��л����Ȼ��λ˧�磬��������ԣ֮��Ĺ�ϵ����û�а������ϱ����ijɷݡ���Ϊһ�������ˣ�л����������쵼�ڼ���֮��˵����ʱ������Ҫ�ľ���һ����ʵ����������̨�ס��δ���ѧ�ߺ���ʡ�����㡶����ͨ����ʱ�����̲�ס����˵��л�����Ƕ���ץסʱ�����ó���ʱ�ͳ��ְ�����֮��л������ԣ�������ݵ����ݣ���Ц���ٳ���ʵ�ǽ��ҡ�
���������ڣ���ŭ�е���ԣ��ֱû���ɽ��������������ֱָл�ޣ����˵������ɱ���㣡��л�����ش𣺡����¿���û����л�ޣ�������û��������ֻҪ����ֹ�����գ���л�����к�ϧ������������ôһ����һ������ԣ������������ƽ����
ƽ������Ӻ����
��ʱ��������֯�ǰ������Ľ��죬����������ս�Ľ��佫�����O����ԣ�����´�����������������������O�������ĵ��Σ����ɵ���¶��ɫ�����ֵط���ô������ԣԶԶ�������O�ٳ�û�ж�������ѹ��ȥһ��Ļ�����ð���������������ң����Ѻ��O����ץ������ն�ף���
�����O��������������һ����������Ů������̫ξ�������Ƿ��ˣ���æ�����Դ����ˣ��˵�������������������ˣ���ʱ���ܽ��������������
�����ڸо������Ӻ����ǹ����쬵���Ϣ�����Oֻ��ƴ���ˣ���һ������Ϊ�˽��������˶�����������ѡ��һ����Ϊ��Ҫ������ؾ�û̫ע��ĵط����õ�����ʯ��϶���ڳ�һ�����������ɽ�ָ��dz�ӣ�����ʿ��һ����������������������ͱڣ���ߵ�ʿ��Ҳѧ���������ӣ��������±ڣ�ͻȻ�������ؾ����벻���IJ��档���ϰ����ַ����������ɣ�����չ��������������ʢ��³�����������ײ���ɳ���Ͻ����O�Ķ��֣���ѹ�ò������ˡ�
����ԣ����ս�������������Ӷ������������������ԣ��������ʹ�£���Щ������ʿ�����һ���ս������������Ѫ�ĸо����ָ������ǻ���֮ʦ�����䱾ɫ������Щ��ս��������ҹ����£�˾����˼��³��ָ�ӵľ���Ӻ������ȫ���Ƕ��֣�����ô�ܿ��䣬�����ɾ���
�����ֵ���ԣָ�Ӿ��ӳ�����������پ����˽��ꡣ��˾����֮������ӵ�С����ߡ��ؼ������ܴ��ˣ��ٴ�ƽ�����£���Я������³��֮������˾����˼һ��������������³����ʯ�ǣ���������飩����һ������
�����˲���ǰ�IJ�ʹ��ѵ����ԣ���û��˾����֮�������´�Ϣ�Ļ��ᣬ������ֱ���·����һ�������к�����֮�뽫���������ʾ���½·������������ʯ�ǵ�³�죨����֮����ԣ��ĸ���ڵĵܵܣ���ԣ�������壬Ϊ��Т˳���ӣ�������ƽӹ����ͨ����������ԣ������λ�÷��ڰ�ս����������֮�ϣ���Я�Լ��˵���ͼ�������֣�������ѵ���������ٵ������һͨ��������ˮ���Ӻ�ˮ���ϣ�����������
���������ӵ���֮�£�³��һ����أ�һ��������������ȡ�˾����֮��³��֮���˲��ҳ��ɣ�������ʰ����֮�������ʾ���Ԯʯ�ǡ������˻�δ���³���Ѿ��������ӻ��ܣ�ʯ��ʧ�ء�˾����֮��³��֮����ֻ�û��³��İܱ������������������������ǽ�Ҫ����֮ʱ��������ˮ��Ҳ���Ƚ�������³��֮�����²ξ���Ӧ֮�����������꣬�رճ��ţ�����³��֮������ǡ�˾����֮��˾����˼��³��֮��³�컹�к���֮����ֻ������������Ͷ�����أ������һ·�ϣ�һֱ�����ر߽�Ҳû���ϣ��ؾ�����ʱ�����뱱κ����֧Ԯ˾����֮�ľ��Ӷ�����·�ϣ���֪˾����֮�Ѱܣ�Ҳ���Ի�ʦ��
�����衡��
��ʤ���ˣ�����Ӻ����ƽ���ˡ����ݴ�ʷ��ְλ��ʱ���Լ����Σ�Ӻ�ݴ�ʷһְ�����常����֮��������Ȩʵ����������������δ�й������뼯Ȩ����ȻȨ����û����˾�������ӵ����У�����ԣ��սǰϣ����ɵ���ҪĿ���Ѿ��ﵽ���������ijɹ���ȴ���������о���Щ���Ŀ��֣�Ϊ�����ʤ�����������Ĵ���̫��ʹ�ˣ��������������Ҫ�������ϵģ�������λ�ȥ���Ů�����˵���ʧ���Ŀ�⣿
����ԣ���ǵ������Ů�����������ӣ���ʱ��������ʮ�꣬��һ�ε��ϸ��ף����ݻ�ֻ�Ǿ��ڽ�ͷһ������Ь��С������ע�����������ϳƣ����˵����ڽ�̫Ԫ���꣨��Ԫ383�꣩��Ҳ������ˮ֮ս��������һ�꣬����䴫˵����Ϊ����������������÷���Ļ���ת����������˵����ԭʼ��������û�в鵽�������ο�����
������갰����ǿ��﹦��갿���Ů��������ְ�������븸������ͬ�����������ʵ���ŵ����ԡ�ֻҪ�������̵ļҾ����Ͳ��������ŵ����Ե���˼���Ǿ���˵갼Һ�����һ����Ҳ���ƾ��ȣ������ʱ����ԣ��ֻ�ܺ�����࣬һͬ���Ѷ��ա������ϣ�갰��ͽ��ռ������鲼һ���첹��һ�����ɰ����£�����ԣ�ʹ����������������ͼ������ȥ���ޣ������е�С������������֮���˵ĵط�������ٱ��ؾ��ڷ�������������ǿ���ڵ�СǮ��������������ͷ��ƶ������һ�������ȥ��ֱ����һ�죬������һ��ƽӹ����ԣ�DZ���ˣ�Ͷ�����á�
�������ּ����½�����������˵ܣ�����Ͷ���������ļ������ڰ��죬��ĸ������һ��������������������ϣ������䵭���¹�ѧϰ�첹���ߡ���Щ��ĸ��һͬ�غ��ڼ������������������£�������������ӻ��йظ�����Ϣ�������������ģ�Ҳ���Ǹ�����Ϣ����Ϊ˭֪������һ����Ϣ��������ج�ģ�����������̫��ĹѸ�����ʹ�����ı�Ӱ��Ҳ��֤��δ�ϵ�ĸ��ͷ�����ռ��߰���˿��
��������Щɥʧ����ͬ�磬���˵������˵ģ���Ϊ���ĸ�������ԣ�����������ĵȴ�������ĸ������ӭ���˸��׳���ͷ�ص����ӣ�갰��׳���ԥ�¿������ˣ������˵�Ҳ��һ�������۵�ƶ����Ů��һԾ��Ϊ������Ľ�Ĺ��С�㡣��������ĸŮ������˵�����������Ǹ��˵ģ����²�����ͻȻ���ٵĸ����ٻ�����Ϊ���Ǹ���֮��Ҳһֱ�����ż��ӵ�����ϰ�ߣ��������ڿ����������еؼ����ɷ��ף�������Ϊ���������£����������ضɹ�һ��������֮ҹ�����������˵�ƽ�����������Ҹ���
�����衡��
갰����Ѿ�������ǰ���ţ������������࣬���������Ҹ��ģ����Ȼ�����ԣ����˭��֪�������ֿ������ƺ��Ѿ�Զȥ�����ѣ������䵽Ů����ͷ�ϣ������ԣ���ǹIJ�����Ů����֪ج�ĵ����������ǰ����������������֮��ʬ���ĸ���ʿ���������J��Ҳ�����Ǹ�����ȭ���������Ķ��J��
�����ȷ�Ǹ�����£������Ͳ����ԴǵĶ��J�����һ�����ص�����֮Ů���й�����֮��ս���������촦֮��IJ��¸����������ݣ�ֻ�����˵���һ�䣬������ǿ��һ�䣬���˵�ֻ������̾Ϣ�������������������������Ŀ�ʹ�����ڲ����С���
������֮��һ�������İ��迪ʼ�ڽ���������һ���������������˵���һ�̵İ�̾�����������������衷�����ĵ����߲��꣬��֪���������˵ܱ��ˣ�����ͨƪ�Ծ������ӿ��ǣ�ĬĬ��˵���ͷ�Զ��ʱ�������밧�ˣ�
����������ȥ�����������档������â�ߣ������������
����������ʱ��ٯ���������Ը��ʯ�ȷ磬��������á�
���Ż�ȥ����������ֱ���֡�ֻ����ɳ���������£�
����˵��ԣ����������������ĸ�������������Ӱ�쵽���ӵ�ʿ����Ҳ�������Լ�������ʼ�ı��������������˰��պ��������ɵ�Ҫ����ǰ��������Σ�
����������ȥ��ǰ����ƽ�����Ŵ��߸ǣ������﹦����
��������ǧ��Ͻ����������������䣬�����ѵá�
���˺��������������������������ȥ��ֱ���Ƴ���Ϊ�������д���¡��������衷����ȡ����
���������˵ܣ����ܾ�����ԣ�����ټ������ع�������һ�ĸ�����������֮�������������ӣ���տ֮���촾֮�������Ը�Ҳ��÷dz���������û���˼�������Ц����ֻҪһ�����⣬��ᱯ��������������ޡ���ԣ�Դ�Ҳû�а취����Ϊ�ںܴ�̶��ϣ����е��������Ĵ��������Բ���Ů����ʷ����˵����ԣ������С��������Ǵ������µ���տ֮�����˰ٰ���۰���ʱʱ�������ߡ������СС��ϸ�ڣ����ǿ����ģ���һλ����Ů���ľ��ꡣ
��������ˣ�������ǽ�Խ��Խ����ط��֣���ԣ������ʷ�е�����������һ�����μң���һ������ͳ˧����ͬʱ����һ�����ף�һ������Ů���ݴȰ������簮�ĸ��ף�������һ���ݣ������������꽥�������Ͼ�����ռ��������Խ��Խ����Ķ�Ů������������ʴ����ԣ�Ǻ�����Ӣ�������������그�µIJ��ٴ����У����ǻ�����������仯������Ӱ�ӡ�
Ӣ����ʧ��ͬ����
�������������ʱ�䣬��ʹ�ĵĸ��϶�������ԣ�������ڳ��������ʮ����ĺ��ػʵ�Ҧ�˾ͱ���ԣʹ��öࡣ��Ϊ��ԣ��Ů�����ٻ�����ѳְ�������Ķ����ǣ�����æ������к���
����ΪǼ���յ��������Ϯ������Ҧ�ϼ���ķ�ֳ������ͦǿ�ģ�����Ҧ�˵�үүҦ���پ��ж��Ӷ����ʮ������ֻ�����ݱȽ�ƽӹ����ʷ�������ء�����֪����ֻ�����еĵ�����Ҧ�塢�ڶ�ʮ����Ҧ�ɣ��Լ���֪���е�Ҧ����Ҧ����Ҧ˶�¡�������ô˵������Ҫ��ʮ����ʱ����ѡ�Ž��Ѱ�����ô��ͥ����ô�����Ҧ��һ������������
����һ��Ҧ���ֵ�������Ҫ������Ī����Ҧ�ɣ�����������պݶ����Ƶļ��ۣ��ڶԴ��Լ�����ʱ����ȫ��һ���������ģ���ֵܡ�����Ҧ����ǰ�ؾ��������サսʧ��������ս����**��������Ҧ�ɽ��Լ������ø��ֳ���Ҧ�����������������ң����Լ���ô���ѣ���Ҧ�ɻش𣺡�ֻҪ�ֳ��ܹ�ƽ�����£���ЩС��������˺�Ҧ�ɣ������Ǻεȵĸε����հ���
��������Ϊ���������Žụ����Ҧ�ϼ��Ų�������Ȼ����֮������ץס�����������ˣ����������ء��ں��ؿ�������ս�����У�Ҧ���ֵ��Ƕ����и�ͬ��������ͬ��������һ���룬����һ��ʹ��Ҧ����Ϊ��������Ҧ����Ҧ˶�µȶ������н�������ʷ���ϴ�û���������ֵܼ����κβ��͵ļ�¼��
����ϧ��Ҧ�ҵĺ����ӵ���Ӧ�˸����������Ĺ�������ص۹��ĵ��������壬Ҳ����Ҧ�˵Ķ�������һ��ʱ��Ҧ���������ֵ��Ѱ���ͳ�����ڱ���Ⱥ��N���ӵ������Ժ��ˡ�
���������²鵽�ļ��أ�Ҧ��������ʮ�������ӣ��ֱ���Ҧ����Ҧܲ��Ҧ����Ҧ����Ҧ����Ҧ�ȡ�Ҧ�֡�Ҧ�ʡ�Ҧ�ӡ�Ҧԣ��Ҧ������Ҧ����������Ҧ������Ҧ����������С���������ο�Ҧ������үү�Ĺ�Լ�¼������Ҳ����Ҧ�˵�ȫ�������ˡ��ɼ���
��Ȼ��������Ӷร������˵�ò�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