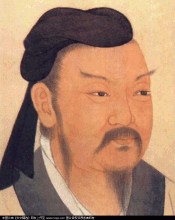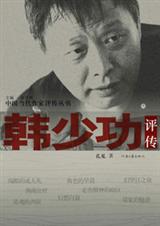��ԣ����-��5����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û�뵽���ǣ�����һλӵ�ж�������άȨ��ʶ��ǿ�Ĵ�ʷ���������������ӵ��ļ��������������Ȼ��˾��������ô�����壬�����α�Ҫ����������ϵ��������ǣ����Ļ���ͥͶ���˲����������Աߵ����϶��Լ��Ρ�¡�����꣨��Ԫ398�꣩���£��������Ķ�����Ϊʹȥ����������˵��˵��������˾����֮�ֵܣ�רȨΪ�������������������ھͿ�ʼ�ٽ賯͢��Ȩ������������ԥ�ݣ����ָ�����ֵ�˭�ء����������ڵ���ı��û��������죬����Ӧ���������㡣����Ϊ��������������Ҫ�ڵط������������������������Ȼ��Ҫ�DZ���ͬ־���������������Ŀ��������ͬ����������ȥ֪ͨ���ٿ��ͻ�����������Ҳ��ʾͬ�⣬����������Ϊ������Լ��һͬ�������ƾ��ǡ�����Ϊ���ٿ��������Ļ����ڴ��ݹ������ּ�ģ����ʹ�������ܶ϶��Ƿ�ȷϵ���ٿ��ֱʣ�����ȥ�����ٿ�ʧ�ڳٵ���Ҳû�����������ɵ��֣��������������������ٿ������������
�������ľ���������´���������ʱ��ʵ����������֮�ķ��ԣ����������dz�͢�Ĺ��ˣ�����������ӵ��常������һ���ˡ����һ����������������û�е��ォ����ǰ���û�Ϊ�˽���ɱ���������谮�����������Խ������������ϣ��Ѿ������ˣ����������µ�������Ȼ����˵ʮ��ǡ������Ҳ�㲻��ʲô�������������������ĵأ��ڽ���������ʲô��ʧ������֮ʦ���ݡ�����•������ʮ���꡷�أ���������������������ļױ����������Ϊ����������������ʿ��**����㽫����������������Ϊ������֮ʦ������֮�ס������һ���ٵط������������������ϱ�ָ�������˾����֮�ֵܵ����У�����͢���������ַ���
������֮���Բ���������Ϊ����ʮ���ֳ�������ɿ���������֮��һ������֮�ij����������µĺ��ţ����Լ�̫ԭ���ϵĸߵ�û���ȣ�������һﳤ���ֲ�˧���Ϻ�ɫ�Ĵ����ӻ����������������ﻧ�����Լ���ȥѲ�ӣ��紺�����Ա�վ���Ჱ���ɣ�������ͷһ����������֪��������̸����ʱ�еĸ�������һ�ϲ�ͨ���ɼ������ٵļ�����Ҫ����������֮ȫ��Υ���ˣ�Ҫ���ǿ���ȷ�м������������ܴ��̣��ɳ�ӥȮ��������ĸɲ���������ôҲ��������ôһ���ˡ����Լ������Ľܳ��˲ģ��������ԣ����˻²�Ϊ���࣬��־�����Գң�����˼����˵�����ҵ��������������Ժ�������Ǿ����˷ѹ��ҵ��˲���Դ�������õ�������ϴ���ָ�ֻ���ô����Ҫ���������ģ����Ǻܵ��ۣ�
����˵˾��������˵�����꣬�dz����ţ�æ���˼���ȥȰ������ת�⣬���Դʰ��������������ij���Ů������������֮�䣬��ͬ���⣬��һ�������кȹ��ƣ�һ����»������ѵ����ԣ��˴˼�������ܣ���������������ѣ�������Ԯ���ѵ����������������������ѹ���裿��Ȼ�������������һ������Ȩ���գ��϶����㵱����������С�ˣ���������������Σ�ֻ�½������������ѱ���������˵�ٻ������ˡ���
��������˵������������Ҫ�����뾩�μ��ȵۣ�Т��ۣ�����������������ƿ�ʩ������Ҫ���Դ��С��ҵ��ҷ�������������ʾ��ִᄅʦ�������Ų��ҷ������ҡ�ȥ����±䷢��ʱ����Ҳ��������һֱ���������������̷�����������û�жԲ�����ĵط������������أ���Ϊ������������ɱ�������������������������Դ��Լ��ˣ�����˭��Ϊ������Ч���������ɲ���ѧ����������ȫ��һ�ٶ����������ȥ��ɱ����
��˾�����ӽӵ����ź�֪������������أ���ʽ����ȫ�����ϡ�˾��Ԫ�ԶԸ���˵����������ϴ�����Ϣ���ݵĺý���ˣ��������ٳ������ǵ����⣬��ô���ǵ�Ŀ���������ֻ��˾����֮�ֵ�Ϊֹ��̫�ף���˾�����ӣ��Ĵ��������ǰ�ˣ���˾�������Ѿ��ŵ�������������֪����Ǻã�����ȫ����������ȫ������˾��Ԫ��ȥ������������һͷ����������ƴ�����������������ͷ�ڹ�Ľ�ɫ��
�����ݴ�ʷ������������������������ٿ�����Ϊ�ϴγٵ��������е���ⲻȥ���ټ���������ط��֣�����ԭ���ܺ��۸�����������ж��dz����������µף����ʷ���Ͽ��������Ϊ�ȷ棬����Ϊ������ˮʦ��ǧ�س������£��Լ��ʾ�����������������������ӵ��ĵڶ�����ս���������³���ǰ��ͻ���Կڣ������Ž���������ˮ�볤�������������β��õĽ��ݴ�ʷ�����������˾�����Ӱ������������Ǹ�ʲô�ģ���Ȼ������������æ���Ƕ��ӣ�����û��������˸����ţ�����˾�����������˵�ˮƽ������������ֻ��Ҳ���������漶�ģ���
��������
�����¶��գ���͢��˾��Ԫ��Ϊ���ֶ�����ͳһָ��������������������Ϊ������·����·���������������ҽ���л��ָ�ӣ�������������·��˾����ָ֮�ӣ��ַ�ԥ�ݴ�ʷ��������ʮ�գ�˾����֮��ţ侣��յ�Ϳ�ز�ʯ�������������ֻ�����ӣ�Ͷ������˳�����µĻ�����˾����֮�漴������Ϊԥ�ݴ�ʷ��ʮ���գ����µ�����ڡ����������ϵ�˾����֮��ս�ڰ�ʯ���ճ��ض��ϣ���˾����֮��ܶ��ӣ��ܵ�˾����֮���ʵ�ˮ��ȫ����û��������뻸����ʤ�ƽ����Ὥ���պ��ض��ϳ��������������ˣ��ӱ����Ͽ��������������ǿ��ľ��ݾ��뾩�ھ��Ķ����л�֮�У�����ս�������������᧿�Σ��Ҫ�����Σ�������Ƿ����漣��
����������������Ŀ���뿪ս�����ع�ͷ�����¿�һ��˾��Ԫ�ԵIJ��𣬿ɷ����������Ǻܺ����ġ���������˾����֮���ǵ��ӵ������ˣ��ȽϿɿ��������Ҳ���ˣ����ߵ�����������ȴ���ڲ����������ȥ���������복طһ��һ�ͣ����Ƶ������������Դ�������һλ��������ָ����������սʱ���������𣿵�˾��Ԫ���ƺ��Դ˲������ģ���Ϊ��������ע�ĵط�����������������������֮��
��˾��Ԫ�Դ������������ʱ�̣����ǿ����˴˿��������ǿ�������������ˣ����ӵ����Ƶ���������Ϊ�κ������������ٿ�����������Ϊ����������ʲô�۲Ŵ��ԡ�����˵�����ɣ���������û�б����������ľ��ú�����֮�������ͽ����������кοɾ壿���ʱ������֮���DZ���������꣬�߷�������֮Ҳ�͵��ڲ߷��˱�������������������֮��������һ����
��������������������֮һ��������֮���Լ���λ��ͷ��˾��Ҳ���IJ������ġ�����֮�Ĺ�λ���ǿ�Ϊ�������°�ս��ѫ�����ģ�����ÿһ����Ǩ������Ӧ��һ����Ѫ������������ɱ����ʷ���������Ǵ�������ڻ���˭��ս�����Աȵ���������֮������ijЩ�˵ĸ߸����ϣ�ֻ����Ϊ�����ϰ֣������ϰֵ��ϰ��������쵼��ֻ����Ϊ�������������������˲ݵ��廨��ͷ��ֻ����Ϊ���дƻƣ����ڿ����̸��
�������������˻��������ԣ�һ�����£���ֻ���Լ�����СС�������������֮�����ģ��Դ˼�Ϊ��ƽ���������ʱ������һ�������ѣ���Ϊ�����ɽ�����®��̫�صĸ������������������ش�����˾��Ԫ�Ե����ţ�Ȱ����������������͢��ֻҪ�³ɣ��ͽ��������ڵ�ְλ��������֮������һ����С���ջ���֪�ڶ����۹�����ʷ�ϣ�������û��һ����ʿ��������˵��ι�������һ���ķ⽮���������ڴ���˶����۹��߲������ƶȵ���Ϊ����������������֮���ɵ���Ȼ�Ķ����������������������£�������Ҳ��ʾ��ͬ�����������������ܱ�������������������˳��
�����ϴ��±������IJξ����֮̽������������æ�����������档������Ȼ����������֮���������������Ը��Դ�Ĺ���ϰ��ʹȻ����������������֮���������ŵ�������Ϊ���֮������֮ƽ����ì�ܣ�����������λ�βξ�˵�Ļ�������������Ҫ�����أ������������֮���ѵ�����֮�б���ָ�ӱ�������
����������������������֮�����������Գ������Ϊ�˸�ο����֮�������ص������д�����ϯ�䣬�����������˵��棬������֮Ϊ���֣�����ʿ����ǿ��������˵����ȷʵ��Ҫ�������������ͬʱ�����˺�˾��Ԫ����ͬ����ŵ����������°�ɣ���һ�볯����������Ʊ���������֪��������������������ܷ�������֮Ϊ������������������Ȼ�Ѿ����ˣ���������֮�������Ƿ�����������������˾��Ԫ�Եľ����Ѿ�����ı䡣
�������㵽�����ߣ�����Ц���������ҵķ��ա��ҵ����У������и������ޣ��������ȵ���
�����պ�����֮��������վ����ر����������䣬ɱ���������ĸ�������ӣ���ǰ�����Ͷ����͢��ͬʱ�ɶ�����������Ů������֮��ʦ���ڣ�������������ʱһ����֪���������ڳ����ı�����������������ͻȻɱ���������IJ��������������������˻ؾ��ڣ����dz��Ѿ�������֮��ռ�ˣ�ֻ�ö���һ������������
����Ϊ�����ϵ�������ʱ����������û�вο������幤��ѧ����ƣ���ʱ����˵����ʶȱȳ����������˲�Զ�ˣ��ټ�������ƽ���������ţ�������������˵����ӵ����������յ����أ�ʱ��**��������ĥ��Ƥ��Ѫ����ʹ��ʵ�ڲ���������Ǹij�С������Ͷ������������ڳ�������ץ�������������ն�ס�������Ȼû����£����䲻������ʿ��Ȼ����еģ�����ǰ���Ժ������ݲ��ȵ������Լ����뷢����˧��ֵ��������Լ�ն��˵�����������Լ���Ϳ�������˲����ŵ��ˣ���ý����������³��������ҵı��ģ��������ڹ��ҵģ���Ը����֮������ǣ�֪���й�����������һ���ˣ��ұ�֪���ˣ����º�û�����ļҲ���������ƣ�ֻ��һЩ�鼮���ѡ�
���ܵ���˵����������Ʒ�����㻵��������ı���Ҳ����ij��ڹ��ģ�����������̫ƽӹ��˵�����۸��ֵͣ�������á����������ijɹ���Ȩ������Ҳ�����˾������ǿ���Ķ�ȥ��
��ͷͬ��
������֮������������ɱ��ʹս�ַ����˾������ת��ԭ������������·���Ѿ����˽������£�־�ڱصã��ɾ���һգ�۵Ĺ���ԭ��ǿ��Ķ�·�Ѿ���ɵо��������Ҳ����ף�������仯�찡����˧���ٿ����Ǹ���С���µ��ˣ��ⲻ��˵�ˣ���������ںͻ����������������۵�����Ҳ����ס�ˣ�����֮�������������ǺöԸ���ô�����˲����ٽ��ƣ���ʦ���ޣ������е�ɳ�ޣ���
���������һ�����ٿ�������λ���֣�
���������־��������µ����ӡ���˵����ĸ��������һ�κ�����������ҹ���������£�����ͻȻ����һ����ʯ���������Ա�װˮ��ͭ����ս�һ������һöֱ�����������ӣ���Ө����ʮ��Ư�������ϼ���ʮ��ϲ�����Ͱ���һ��������ȥ�������¼���ˮƽ�����û�°�ö��������¶��𣿾������ϻ�ò��ͷ��ˣ������ж��ĺ�����������ֱ����������ӣ�����Ȼ�ȶ������С������ӡ���֮ʱ�й����ң����ֵ�С���鱦����֮��һ��������������˵���·dz�ϲ�����С���ӣ�����������Ϊ���ӣ���Ϯ�Ͽ�������������ʱ��һ�ξ��ݵ������Ա���ݱ壬�������Ż�����ͷ����˵������Щ�˶����㸸���ϲ��¡�����Ϊ���µ�ɥ�ڸոս����������������飬ʧ��ʹ�ޣ��������棬������ˣ�Ҳ�����µľɲ�������������̵�ӡ��������ֶ��Ҳ�ܳ谮�����������ѵĶ��ӣ���ָ���Լ�����λ������˵�����ȵ��鱦������Ҫ�������λ����������
����û�Ȼ������꣬����Ͳ����ˣ�û�ܶ��ֳ�ŵ�������ڶ������еĵ�λ����Ϊ����������ѳ�͢�۸��ù�Ǻ������˾��������Ȩ�ѻ���Ҳ�����ص������ѹ�Ķ�����������ò���棬�������ʣ����������������ġ�����֮����Ȳ�������Ŷ��գ��������ŵڸ߹�һֱδ�����ã�ֱ����ʮ���꣬�ŵ��˸�̫��ϴ����̫��ϴ����������̫�����ǵ�������ϴ���ǡ��ȡ���ͨ���֣���ʾ��̫�ӵ���ǰ���ۣ���̫�ӵ��̴ӣ�һ���ȱ�����ʯ��С�١������ְ���Ϊ����̫�أ�����ڻ����ij���������˵�������Ǹ�̫С�Ĺ١���˻������úܵ��ݣ�̾Ի������Ϊ���ݲ�����Ϊ������������KΪ�������ɴ�ͳ��˹��ҵ����㣬���ٻؾ��ݡ���Ϊ���µ�����ҵ���������ھ������������������鲼�����Ի�������ûʲô�ٷ�ְ���ھ��ݵ�ʵ��Ӱ���������ڴ�ʷ���ٿ�֮�ϡ�
������ڣ���ũ�����ˣ�����̫ξ����ĺ����������ʼ�����ߴ��������£������Ӻ��ϵĹŵ��ʿ�塣���������������Ƶġ�ȫ��ʿ�����а��㣬��ô��ҵ��ŵ����ڽ������������������Ϻͳ¿�л��֮�ϣ���ϧ�����Ϊ����̫������������α������������ʿ�嶼������ҵ��ʣ��ʲ���ȱ����ô�࣬���Ƕ�����������������������Ļ����ǰ���𣿵������ʵ�Ŷ�ȥ����˳��������Ҳ��˵�ˣ������������̫����з�ˣ������ں��������ɰ���Ҳ������Ұ����Ž�Ĵ�þ��棬�����أ����ܳ��棡�������ҵ�һ����������ֻ�ܴ���������˵��Ժ��У��ϲ��������ĺ�ͷ�ļ��������������ˣ���������Ϊ������ں��ţ�
���Դ�����ڸе���Ϊ�߿��������¹��ң�������ս������������㣬�ܵ���˼ƽ����ǿ��ֱ�֮��������ÿһ�θе����������ŵİ���ʱ���������гݣ���Ϊ��ǰ���Ķ�����Ϊ���һ�������鹣�����������ˮ֮ս���ı������������Ž�ս������Ȼû���ñ����Ͽ���ҵ��ŵڣ���Ҳ�úܶ�����Ϊ�������ͬ־�����DZȽ���ս���ġ�
���ɴ˿ɼ����������˱˴˲����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