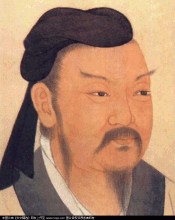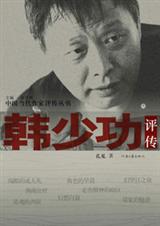刘裕评传-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多人认为:杨佺期同志,还是比较能战斗的。
由此可见,这两个人彼此并不团结,但他们也有共同点:都对现状极为不满,想要找机会往上爬,官位都在殷仲堪之下,能力都在殷仲堪之上。殷仲堪则一面利用杨佺期来牵制桓玄,另一面又用桓玄牵制杨佺期,勉强维持仲裁人的位置。
有了王恭的先例,这一点也很快被人看出来了。桓冲的儿子桓修正在朝中担任左卫将军,向司马道子献计说:“西路的叛军可以不征而定。殷仲堪、桓玄等人之所以敢兴兵东下,完全是仰仗着王恭的北府军,现在王恭已经失败,他们的惊慌沮丧自然不用说了,这个时候如果以重利诱惑桓玄和杨佺期,仅靠他们两人就可以摆平殷仲堪。”
于是,朝廷下诏,发布了一系列人事任免令:一、任命桓玄为江州刺史,代替已当了俘虏的王愉;二、任命杨佺期为雍州刺史,原雍州刺史郗恢调回中央任尚书;三、任命桓修为荆州刺史,由刘牢之派军一千,护送他上任;四、原荆州刺史殷仲堪降为广州刺史。(今天广东比湖北富多了,但在东晋时恰恰相反。而且当时的广州刺史是刁逵,就是当初把欠债的刘裕抓起来吊打的那位大债主,此次的人事命令中却没有说殷仲堪如到任,刁逵怎么安排?可见司马道子父子其实压根没打算让殷仲堪就任。)
殷仲堪得到诏书后,又惊又怒,催促桓玄、杨佺期二人赶快进兵。但桓、杨二人本来就是为了出人头地才出来玩命的,并不是什么昌明党久经考验的忠诚党员,此时都生了二心,殷仲堪的命令已经指挥不动他们了。殷刺史发现势头不对,也不通知桓、杨二人一声,就带着自己的直属部队撤走。殷仲堪一边撤,一边还放出风声警告驻扎在蔡洲的桓玄、杨佺期部众,让他们尽快解散回荆州,如果不回来,自己回到江陵就要杀他们的家属!桓玄、杨佺期的军队顿时人心浮动,两人大惊,也只好狼狈西撤,追赶殷仲堪,直到寻阳才把他给追上。此时,三个人都重新冷静下来:大家已经是一条线上的蚂蚱了!
一千多年后,清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十一月,大名鼎鼎的平西王吴三桂在云南反清,接着,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三月,靖南王耿精忠反于福建,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二月,平南王世子尚之信幽禁老父尚可喜,反于广东,这就是清初著名的“三藩之乱”。当时清帝玄烨为了孤立三藩之首的吴三桂,就采用了与司马道子父子类似的手法:停撤靖南、平南两藩,宣布除吴三桂外,包括耿精忠、尚之信在内的其他人只要反正,全部给予赦免。这一招很成功,耿精忠和尚之信后来都投降了清朝,有“圣祖仁皇帝”亲口许的诺,这回该没事了吧?谁知等吴军一失势,清廷就杀了尚之信全家(尚可喜先已病死)!等清军攻克昆明,耿精忠和几个心腹便在北京享受了凌迟这种高规格死刑,其余子孙部下皆斩!
这个典故,殷仲堪等三人虽然不知道,但这个道理,三人是明白的:现在万万不可以自相残杀!于是,尽管三人之间已无信任可言,但还是达成了合作协议,互送子弟为人质,结成三方同盟,并推桓玄为盟主(王恭一死,殷仲堪也不能当头了)。盟约签订以后,三人发表了《寻阳联合公报》,公报的主要内容如下:一、替王恭鸣冤,要求严厉惩办刘牢之和司马尚之;二、上疏强调殷仲堪无罪,不该被降职;三、部份接受中央的人事命令,即桓玄任江州刺史、杨佺期任雍州刺史这两项。
虽然战局已经逆转,但司马元显觉得此时兴兵西讨也没有必胜的把握,而且就算成功,除掉已经削弱的昌明党,却养大一个刘牢之,恐怕也不是什么好事。于是,朝廷与三方同盟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互做了一些让步,三方同盟放弃第一条要求,而朝廷也不再降殷仲堪的官,双方终于达成了停火协议,第二次“昌道内战”结束。
在这次内战进行期间,还发生了一件目前看起来似乎无关紧要的小插曲:有一位名叫孙泰的宗教界人士当时正在新安(今安徽歙县)当太守,以为国赴难、讨伐王恭的名义,并利用他是五斗米道教主的有利条件,聚集起私兵数千,欲图大事。司马元显怕他尾大不掉,派人将孙泰和他的六个儿子诱杀,只有一个侄儿侥幸逃脱,率一百多名铁杆教徒逃入海岛,发誓报仇!这个侄儿的名字,叫作孙恩。
元显扩军上
成功战胜了昌明党的东西夹攻之后,十七岁的司马元显洋洋自得,身边很快聚起了一帮马屁高手,对着他一个劲地摇尾巴,把他捧成古今少有的超天才少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英明统帅。司马元显也自认为舍我其谁,干脆乘老爹司马道子在府内醉生梦死的机会,让晋安帝下诏,免去他的司徒、扬州刺史的职务,由自己接替,正式取代了老爹,成为道子党的第二代党首。司马道子好容易酒醒,才发现自己已经不用去上班了(虽然他早就没上班了),勃然大怒,但也无可奈何。
从某些角度来说,司马元显与朱由检颇有几分相似:两个人都在年纪轻轻的时候突然骤掌大权,而且在掌权之后不久都成功地做成了一件大事(司马元显摆平了王恭,朱由检摆平了魏忠贤),这使得两个人的自信心都超过了他们的实际能力,以为天下大事,不过尔尔,开始雄心勃勃、雷厉风行地胡来。
作为道子党的后起之秀,司马元显认为:这次危机虽然借刘牢之之手杀掉王恭而得以化解,但他也不相信刘牢之对朝廷会有什么忠心,藩镇强过中央的危机根源并没有改变,要摆脱地方武力对中央的威胁,当务之急是要大力加强中央直辖武装力量的建设,如果拿不到别人的枪杆子,就得自己打造一把枪杆子。这个想法并不算错,但为了实现这个重大的战略目标,他采取的具体对策是让三吴一带的“免奴为客”者“自愿”到建康充当军户,增加中央政府控制的军户数量。因为是“自愿”,所以号称“乐属”。所谓免奴为客者,是指曾为奴隶,得到部份解放,上升为半自耕农的人,他们虽然已有一定人身自由,但仍依附于原主。之所以选择三吴,是因为此时东晋虽然不小,但强藩林立,中央号令真正有效的地方,除掉国都建康,也就剩下三吴之地了。
这道命令一下,司马元显捅了一个大大的马蜂窝,遭到三吴民众上下一致的反对,他这么做得不旦没能建立一支强大的新军,反而引发了东南的大乱,也使笼罩在他身上的“神童”光茫丧失贻尽,露出了镀金的本色。
当地地主的反对很正常,夺走他们的依附民,就如同直接割他们的肉。那免奴为客者为何也不愿意呢?难道他们不喜欢自由?要弄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最好先回顾一下古代的士兵究竟是用怎样的方法从老百姓中挑选出来的。
中国古代的兵制,经历了非常复杂和漫长的演变过程,如果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那就是在征兵、世兵、募兵三大基本制度之间,做着反反复复,来来回回的肯定与否定。
西汉实行的征兵,与今天有几分类似,是“普遍义务兵役制”,凡年满二十三岁的成年男子,都要服两年的兵役。这两年兵役也有区分的,第一年担任郡国的地方部队,这一年任务除了客串警察,维持地方治安外,还相当于干一年的实习兵,象今天的大学一样,实习军校也是分专业的,有材官(步兵)、骑士(骑兵)、楼船士(水兵)三种,每年到秋天的时候,进行毕业考试,称作“都试”。第二年从地方毕业,转为中央军,或卫戍京师,或驻守边境。不过这个顺序并不是固定的,假如遇上大规模战争,国家也会临时大批征召士兵,不受两年服役期的限制。显然,这一套制度要能够有效实行,中央政府必须强而有力,统有完善的地方各级政府,国家能够有效的掌握户口。
后来王莽篡位,光武中兴,天下经过十多年的混战后重归一统,东汉王朝建立。因为在王莽当政期间,有不少地方武官利用秋天“都试”的机会起兵(如西汉居摄二年,即公元7年,东郡太守翟义与郡都尉刘宁等借地方兵集中都试之机起兵反莽),必须防患于未然。与此同时,由于经历了战乱,国家的经济状况不容乐观,也需要休养生息,在以上两个因素的推动下,光武帝刘秀对原来的兵制进行了调整,其目标:大力压缩地方部队,只保留中央军,强干弱枝。建武六年(公元30年),撤销了各地的武装部,“诏罢郡国都尉,并职太守”,建武七年(公元31年),又取消了地方的实习兵,“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既然没了考生,考试自然就变得不必要了,因此“都试”也就跟着一起取消,地方武官挟兵造反的可能性在相当一个历史时期内被消除了。
没有地方部队,地方的社会秩序如何维持,发生骚乱怎么办?刘秀采取的方案是,对豪强地主发展自己的私人武装采取默许和纵容的态度,让他们来顶替地方军。今天西方各国政府,倘若感到钱不够花,想要削减政府开支时,最常用的一招就是将国有企业私有化,而刘秀也正是这样干的。大概在光武帝看来,豪强地主与东汉帝国政府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由他们从自己的依附农民中组织部曲私兵,不但可以代替地方部队,为国家省一大笔钱,而且因为他们每支的规模都很小,毛毛虫掀不起大浪,也比原来的地方部队安全。
但从长远来看,刘秀的改制给将来造成了很多不利影响。一方面,因为取消了实习期,中央军士兵未经培训就上岗,职业技能没法不下降。这一点在刘秀时代还看不出来,因为那时的汉军将士都是追随光武打天下的百战劲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军的虚弱将越来越明显;另一方面,豪强地主的私人武装因不受服役期的限制,其经验技能的积累往往胜过正规军,又由于在冷兵器时代,武器的作战效能和价格的落差都是比较小的,导致政府军的装备通常也不优于私人武装,官兵对私兵的优势逐渐丧失,为即将到来的军阀割据奠定了物质基础。
元显扩军下
到了东汉末年,在“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声中,东汉中央政府的威信与军力一起扫地,中央军的无能让私人武装获得了急剧发展的机会,例如我们熟悉的曹**、刘备、孙坚等人的初始军力都是私人组建的,非国家的编制军队。当这些私人武装升级为军阀集团后,尽管他们往往已拥有了合法的官爵职位,控制着大片的州郡土地,但已无法按照原有的征兵制度为自己征募兵员了。这是因为天下分崩,兵连祸结,导致人口锐减不说,剩余的百姓也往往不入坞堡,便成流民,都不在原来的地方了,原先合法的基层政府机构,什么乡镇村社居委会之类的,全都消失无踪,你想这兵还怎么征?
我们假想一下,比如说某一天,兖州牧要征兵,他先去市政府调查户籍资料,查得XX村还有XX名男丁今年该服役了,好,发份通知下去,让他们赶快来报到。
什么,通知发给谁?这么笨啊,不会发给乡官吗?
什么,那疙瘩没乡官?发给亭长吧。
那疙瘩没亭长?那发给里正吧。
那疙瘩也没里正?这…这…(头风犯了,晕倒中…)
算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大不了下一次基层,为征兵处的干部做做表率。可当苏醒过来的曹州牧亲自到XX村一看,得,从村头到村尾,站着喘气的一个没见着,躺着不喘气的倒是有不少。曹领导郁闷到了家,心中慨叹,几句传颂千古的诗句脱口而出:“…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上边这一段是虾扯蛋,不用当真,不过在下怀疑,曹公难过的主要原因是这种局面害得他征兵征税太困难,因为这种惨状的形成,他自己也“功不可没”)
但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吧,何况还是孟德公这样的聪明人。资源不足,就要加强对现有资源的利用效率。一项重大改革,世兵制的一种,军户制便就这样应运而生了。军户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原先私兵的放大与规范化。当年豪强地主们在组建私兵的时候,不可能象政府那样去按户籍抽丁,都是从亲戚、家仆、依附佃户中招人手,彼此之间一般有较亲密的关系,比较容易上下一心。士兵是由依附民、家仆等组成,往往全家都附属于兵主,他们一般不容易叛降或逃亡。对于乱世军阀来说,这些优点都是非常可贵的,而且有战斗经验的老兵,是军阀们的宝贵财富,也不容流失。于是,以曹**为代表的军阀先进分子,便纷纷执行了“兵农分离”政策,将士兵及其家属的户籍专门提出来,组成军户,实行军事化的集中管理,一切行动听指挥,解除了他们的徭役和赋税负担,专职当兵。平民一旦加入军户,除非有最高领导的特批,永远不能脱籍,任职终身,父死子继。
出于保持军户战斗力的考虑,军阀们对军户的个人问题都非常关心,总会想方设法给他们找个老婆成个家,这样做有三大好处:一、体现领导对军户士兵的关怀,有助于提升士气;二、让军户生下小军户,保持军户的人数稳定,也就是保证了稳定的兵源;三、军户士兵有了妻儿,领导手中也就有了人质,可以防止士兵叛逃,反正你跑得了和尚也跑不了庙。从另一方面看,当时的平民加入军户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战乱时代,军队作为有严密组织的武装集团,其生存下去的机率远高于没有自卫能力的自耕农,衣食可以维持温饱,还可以有个家,虽然不得自由,但对于灾难深重的乱世民来说,这些条件已经够优越的了。
要在乱世称雄,光“足兵”是不够的,还得“足食”,屯田政策因此出台。战乱时代,自耕农为了躲避战祸而大量逃亡成为流民,使得大片良田化为荒地无人耕种,而大批流民却无地可耕。以曹**为代表的一些军阀开始将控制的荒地改建成大型的国有农场,吸引流民前来耕种。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