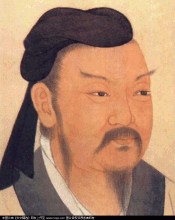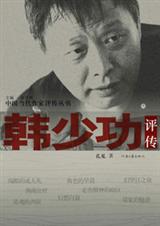刘裕评传-第6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过,与很多文章留给人们的印象不尽相同,驻防关中的晋军尽管经历了这次伤筋动骨的严重内纠,但其防御体系仍未完全崩溃。临危受命的傅弘之率晋军反击,在池阳(今陕西泾阳)大败夏国皇太子赫连璝所率两万夏军,然后乘胜追击至寡妇渡(今甘肃庆阳县北),再次大败夏军,粉碎了夏军的长安的进犯。
这两次胜利,让王买德吹嘘的,要在十天之内擒获刘义真的大话,变成了一个破碎的肥皂泡。习惯于欺软怕硬的赫连勃勃闻听败报,感到晋军仍不可小视,便没立即前来为儿子找回场子,而是又率领他的大军缩回了安定。这说明,即使只是刘裕手下像傅弘之这样的二流将领,只要在局势没有彻底失控的情况下,也能给赫连勃勃制造足够多的障碍。赫连勃勃的能力,其实被很多文章高估了。
关中之崩 三
能被后世的文章高估,自然是因为赫连勃勃这位老兄的吉人天相,好运相随,总能在碰到麻烦时遇贵人相助,比如当年在亡命之时得遇没弈于,潦倒之日得遇姚兴。所以用不了几个月,赫连勃勃命中遇上的又一位“贵人”,就要出手相助了,他对赫连勃勃夺取关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绝对高于王买德。
这位“贵人”其实已经出过场了,他的大名叫作刘义真,就是刘裕的次子,那位名义上的关中最高领导。
刘裕是个慈爱的父亲,但慈爱的父亲并不见得就是称职的父亲。可能是由于自己的童年缺少父爱,再加上诸子都生于他四十岁以后,全属于老来得子,故刘裕对他的儿子们宠爱有加,多放纵而少磨练。
此时已身居桂阳县公的这位刘义真小朋友,又是其中比较得宠的一位。他自幼便长得仪容俊秀,伶俐乖巧,非常可人疼,虽然年幼无功,却已经有一大串说出来吓人的显赫官衔,用近世的标准来算,他的职务大致包括五个省军区司令、两个省长、以及西北区军政长官、西北少数民族问题专员等等,已远远高出了刘裕手下战功最显赫的将军。
权力是否一定会带来腐败还有得一说,但权力肯定会带来马屁精。只要有腥味,就不愁没苍蝇。一些善于钻营的同志很快发现,这位官职多得一口气说不完的刘二衙内,是个出手很大方的人,只逗他一乐,就能拿到不少赏赐,真正的低风险高收益。形势明显了:哄刘裕的孩子,是个比跟着刘裕征战更加有前途的朝阳产业。很快,有志于这一行当的从业者们,便带着贪婪的欲望和谄媚的笑容,聚满了刘义真的左右。
可惜,美好的愿望在实现之前,往往还要经历挫折。挫折来自关中的实际负责人,刘义真名义上的下属,安西长史王修。
当初刘裕离开长安时,曾亲自牵着刘义真的手,将他递给王修,那情形,与当年刘备白帝托孤颇有几分相似。受此礼遇,王修深感刘裕的知遇之恩,因此他在治理关中之余,也把为人师长,校正小长官的过失,当成了自己不容推脱的责任。所以,他对于刘义真乱花钱,随意赏赐手下的行为,屡次加以制止,从而严重侵犯了刘义真左右群小的利益。
投资是为了回报,对于利欲熏心的马屁精一族更是如此。大家放弃尊严,低声下气地装弱智,来哄一个并非自己儿子的小孩子开心,容易么?努力如果不能转化成收益,那还有什么意思?是可忍,墪不可忍?于是群小决定共同努力,搬倒王修这块绊脚石。至于覆巢之下,还会不会有完卵这个问题,已超出群小们的理解范围了。
他们一起偷偷向刘义真进言说:“当初沈田子之所以杀王镇恶,是因为王镇恶要造反,而王修杀害沈田子的原因,是他和王镇恶一样,也想造反!”
刘义真年纪还小,虽然看起来挺聪明伶俐,但也不是什么神童,还没有判断复杂事物的能力。在他看来,自己身边这些玩伴,当然比一脸正经的王长史可亲多了,不信他们,还能信谁?
于是,在夏军败回安定九个月之后,刘义真突然命自己的亲信刘讫动手,诛杀了王修。王修死后,关中人心大乱,再无人能控制局势,新附军民纷纷叛逃,或各自为政,都不再听从长安的号令。刘义真惊慌失措,又做出了符合一个十二岁正常孩子智商与胆略的决定:放弃长安以外的所有据点,将全部兵力缩回来保卫自己。
晋军在关中的局势,至此彻底崩盘,败局已定,再无挽救的可能。
得知关中晋军的一系列自杀行为后,大喜过望的夏主赫连勃勃再次从率军安定出发,不费吹灰之力便进驻长安西北的咸阳,关中与外界的联系终于被切断,长安的晋军真正落入了夏军的罗网之中。赫连勃勃原先靠王买德的谋略没做到的事,刘义真帮他做到了。
关中之崩 四
长安的噩耗,也惊动了数千里外的彭城,刘裕恐怕万没想到自己的精心安排,竟演变成如此糟糕的结果。随着关中传来的坏消息接踵而至,尤其是王镇恶、王修相继被杀事件,让他进取北方的计划完全破产,他现在只能考虑赶快把坏事的儿子接回来,连固守关中都不再指望了。
王修被杀的当月,刘裕急命辅国将军蒯恩前往长安,接刘义真回来,又命诸将中较有行政才能的朱龄石为都督关中诸军事、右将军、雍州刺史,代替刘义真镇守关中;朱龄石之弟朱超石至洛阳以西,安抚民众,同时接应朱龄石。朱龄石临行前,刘裕吩咐说:“你到长安之后,让义真马上轻装速发,起码得过了函谷关,才能放慢脚步。根据那里的实际情况,你也可随机应变,如果关中确实已经守不住,那你就和义真一起回来。”
十一月,朱龄石到达长安(显然,夏军到此时也没能真正封死潼关道与武关道),传达刘裕的命令,乐坏了刘义真和他左右那班小人:终于可以离开这个危险的鬼地方,不用再面对那些匈奴野蛮人的刀枪,整天担惊受怕了!
不过再仔细一琢磨,刘公的命令也有美中不足的地方:轻装速发,那最近这些日子在这里得到的财物,岂不是大部份都带不走了?怎么办?子曰: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于是,王修死后已经没人敢管的小孩刘义真,在左右群小的怂恿下,将坏事干到了底。他不但没有轻装离开,反而乘着离开前放纵左右,对长安城中百姓,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洗劫!一年多前,这支曾让很多百姓寄予厚望的王师,现在完全堕落成了一群土匪、强盗。他们闯入一条条街巷,砸开每家每户的住宅,抢走所有值钱的财物,还有被他们看上的当地百姓的妻女。
等到所有的车辆都塞满了抢来的财物和美女,刘义真终于出发了。一个已经恨透了这群暴徒的当地官员悄悄潜出长安,投奔夏国,向赫连勃勃报告了刘义真的行踪。于是赫连勃勃立即命太子赫连璝率三万大军追击刘义真。
看着刘二衙内如此胡来,心急如焚的将军傅弘之只好搬出刘裕的权威,警告他说:“刘公吩咐我们要轻装急行,您却带着这么多辎重车辆,每天前进不过十里。行动如此缓慢,一旦让匈奴人的追兵赶上,我们如何应战?现在赶快放弃这些东西,骑快马疾驰,还有机会躲过灾难。”
虽然在这个世界上,刘裕是此时唯一还能管住这个孩子的人,但这种权威一旦放到几千里之外,效用也就大打折扣了,于是刘义真不听,继续带着珠宝美女,坚定地向着前方的万丈深渊,缓缓前进。
没过多久,赫连璝的追兵赶到,傅弘之和蒯恩两员猛将只好担任断后,且战且退,掩护刘义真逃走。一连几天,交战不断,晋军虽有损失,但仍能坚持,终于行至青泥(刘裕的原意是让他们从潼关道回来,刘义真改走武关道的原因可能是出城后发现潼关已失)。在这个一年多前沈田子的扬威之地,晋军遭到夏军埋兵王买德部与追兵赫连璝部的前后夹击,最终全军覆没。
两员忠勇的将军,傅弘之和蒯恩在奋力拼杀之后,力尽被擒,而后傅弘之宁死不降,并大骂赫连勃勃,被勃勃剥光衣服,裸身于雪地之中,活活冻死,蒯恩也不屈被杀;安西司马毛修之本已突围,他登上一处高岗寻找失散的刘义真,结果让叛变的部下击伤,献给了赫连勃勃,之后投降了夏国。为数众多的晋军死难将士则被赫连勃勃砍下人头,堆成“京观”,用来宣扬夏军的武功!
而那个最该死的人,酿成这次惨剧的小祸首刘义真,却逃脱了。他因为人小个子小,战乱中躲进了一片茂密的草丛,没有被夏军发现。曾为南燕降将的鲜卑人段宏,这时担任刘义真幕下中兵参军,他在大军溃散后单人独马,寻找这位小长官。段宏一边找一边呼唤,终于在草丛里将这个孩子找到,然后背着他,共骑一马,逃回南方。得保性命的刘义真对段宏感慨说:“这次的事确实是我缺少算计,不过大丈夫不经历这样的挫折,怎能知道人生的艰难!”(说说而已,从刘义真后来的表现看,见不到他有多大进步。)
关中之崩 五
第二次青泥之战结束了,但晋军的悲剧却还没有结束。接管长安的朱龄石也没有完全遵从刘裕的嘱托,随刘义真一同返回,也许他认为局势还没到无可挽回的地步,还想在关中搏一把。
不过现实很快粉碎了他的判断。已被晋军暴行激怒的长安市民,乘着刘义真与晋军主力撤出长安的机会,发动了大规模的暴动,并和城外的夏军取得了联系。兵微将寡的朱龄石部顿时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无法招架,只得放火焚烧长安宫殿后,突围向潼关方向逃走,被收复刚刚一年零三个月的长安城再次从汉人政权手中失陷。
但此时潼关守军因为被抽走,已夏军赫连昌部袭占,朱龄石发现东出潼关无望后,移军向北,奔往曹公垒(地处潼关以北,隔黄河与蒲坂相望,是当年曹**讨伐马超时修筑的军营),与守将龙骧将军王敬先会合,已至蒲坂的朱超石得知,也强渡黄河与兄长会师。虽然会师,晋军兵力仍较薄弱,而且已失当地民心,进退维谷。
在另一方,夏国大将赫连昌得到了父皇勃勃派来的大批援军,很快将曹公垒团团围住,并切断垒中的水源,晋军大困。
眼看失败在即,朱龄石对朱超石说:“我们兄弟如果一起战死,该让父母如何伤心,你还是悄悄突围走。只要你能活着回到故乡,我死也瞑目了!”朱超石含泪回答:“人生于世间,那有不死的!我怎么可以在危难的时候,抛下兄长,独自逃生!”
不久,曹公垒被夏军攻破,朱龄石、朱超石、王敬先、以及刘穆之的侄儿右军参军刘钦之等全部被俘,随后都被杀害。
曹公垒的陷落,标志着关中战役的结束,潼关以西,秦岭以北,再无晋军存在。后秦的原国土,以潼关为界,基本被晋、夏两国瓜分(有些网文称刘裕在此次战争损失二十万大军或一无所得的说法并不正确)。但相较而言,南朝所得的不多,而付出的不少,是刘裕掌权以来干得最大一笔亏本生意,尤其是大批名将丧身西北,这是个几乎无法弥补的损失,由此直到南北朝终结,南方再没出现过刘裕北伐时这样豪华有将帅阵容。
在数千里外的彭城,刚刚得到青泥大败,刘义真生死未卜的消息时,刘裕勃然震怒,就像当初听说女婿徐逵之战死时的情形一样,不顾一切地下达动员令,要再次出兵北征。
谢晦也再一次给刘裕的冲动踩了刹车,提醒说:“如今士卒疲惫,各项准备也不充分,最好等时机成熟再战。”
奉常(祭祀官员)郑鲜之,则更加明确地分析了再次出征所要面临的各种实际困难:“现在夏虏已占地利,他们如果亲听说是刘公亲自北征,必然以全力把守潼关,以如今已经削弱的兵力,要想一举打破赫连勃勃扼守的潼关,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殿下不攻潼关,只到洛阳,又何必亲征?夏虏虽然得志于关中,但畏惧您的威名,一定不敢越过潼关往东,即使你不去,现有的地方也不会再有危险。您亲征如果无果而终,反而会折损威名,让敌人生出觊觎之心,增加北疆的麻烦。何况我们后方并不稳定,大军出征,隐患重重,也不允许长期曝师于外。当初讨伐司马休之,就有盗匪袭击京郊的盐亭;去年伐秦,又发生徐道期作乱,广州失陷的事。今年江南各地水旱灾频发,很多地方都发生了抗税抗差的民众骚乱,士庶均翘首盼望殿下回朝,不愿再打仗,如果又听到北征的消息,难保不发生变乱!”
刘裕很清楚,郑鲜之说的话都是实情,真要北征,决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要不然去年他也不会在刘穆之死后就急忙回来。正好,段宏保护着刘义真也回来了,冲动过去的刘裕只能登上彭城的城楼,远望着西北方向痛哭一番,三次北征的计划随之放弃。
也正如郑鲜之所料,赫连勃勃得到关中已经很满足,并无染指河南的打算,晋(以及后来的刘宋)、夏两国达到新的暂时平衡,此后两国没再发生大的冲突。
北伐之谜 上
假如我能够穿越千年时空,在义熙十四年的隆冬,走上彭城的城楼,看见那位矗立于寒风中眺望西北,痛哭失声的身影,我将不得不从内心发出一声悲凉的长叹:刘裕老了!
关中失败的惨痛,正如城下那冰冷的泗河水,浇灭了这位精力已逐渐衰竭的五十五岁老汉,那曾经如火焰般熊熊燃烧的进取心。从此以后,刘裕还活着,还将由宋公变成宋王,再变成宋武帝,但那个气吞万里如虎的英雄,已离我们远去……
这次刘裕一生中唯一的重大失败,也给后人留下了两个永远争论不休的话题:一、刘裕发起第二次北伐的主要动机何在?二、假如刘穆之不死,刘裕有统一中国的机会吗?
自从崔浩将刘裕比作晋室的曹**开始,到如今涉及此段历史的多数文章,对第一个问题的答案都大同小异:刘裕为了篡位需要提升威望,所以借北伐立威,并无统一天下的雄心。不过,说得人多就代表正确吗?这个答案果然是无懈可击吗?如果我们把眼界放宽一点儿,不要只睁着刘裕一个人的事,用相似的历史作一下对比,那么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