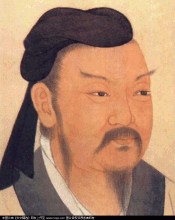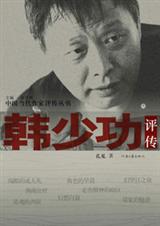刘裕评传-第6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裕一个人的事,用相似的历史作一下对比,那么就可以发现,这种说法其实漏洞很大。
刘裕要取司马家而代之是肯定的,但这和北伐没有必然联系,北伐成功对他建立新朝只是一个有利条件,绝非必要条件。假如刘裕的目的仅仅是一个皇位,那他完全用不着发动这次战争。
在北伐后秦之前,刘裕已经对内平定桓玄与孙恩、卢循之乱,相当于两挽东晋这座危楼于既倒,对外则攻灭了南燕和谯蜀两国,并曾用外交手段就收复十三郡领土。这样的武勋实际上已超过了当年代魏的司马氏祖孙(即使把篡位前司马氏四代老板的战绩加起来,对内也没有可与刘裕相提并论的功勋,平定淮南三叛性质上仅与刘裕摆平刘毅和司马休之差不多,而对外也只灭掉了一个蜀汉)。
再看看刘裕之后,无论是南朝的萧道成、萧衍、陈霸先,或是北朝的高欢、宇文泰、杨坚,论武功均不能望伐秦前的刘裕项背。(尤其是杨坚,这位隋文帝在篡位前根本就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功绩,甚至还不如桓玄,但这并没有妨碍他成为这一群篡位皇帝中的最成功者。从杨坚的成功,我们可以这样作相反的推想:假如桓玄称帝之后的表现不是那样差,也没有倒大霉遇上刘裕这个煞星的话,楚朝完全可能成为一个正统朝代,堂而皇之地写入二十四史。)
如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推论:既然这么多道行不如他的篡位同行们,都可以顺顺当当地改朝换代,凭什么武功已经凌驾于众人之上的刘裕就还得再灭一个后秦?
另外从刘裕回师后的具体行止,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二。刘裕东归后,他的常驻地仍是指挥北伐的战时大本营彭城,而并非国都建康。他也没有在其北伐成功,声望最高的义熙十四年称帝,而是又等了两年,那时晋军已在关中失利,刘裕的声望已然受损。这些事实也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刘裕回来后并没马上把改朝换代当成第一要务;二、他要称帝,其实已不需要更大威望的支持。总之,刘裕回来肯定是要篡位的,但他并不是为了篡位而回来,就像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并不是为了吃饭一样。
至于说刘裕不想一统天下,就像说某位穷人白手起家,打拼半辈子创立一家公司,目的只是为了当老板,并不想赚钱一样,你信吗?对已经是国家实际元首的刘裕而言,假如能够完成统一,那么最大的受益人,正是刘裕及其子孙,故而仅从利益的角度来说,他也比那些“渴望统一的广大人民群众”更有扫平列国的动力。
虽然在商战中,每一个神智正常的公司经营者(少数别有用心的诈骗犯除外),都是希望盈利的,但并不妨碍年年都有很多家公司亏损以至破产。这道理也很简单,因为能不能盈利,并不是由公司老板个人的想法甚至能力所决定的,要受到里里外外很多种因素的制约,经营天下者,业务自然更加复杂,但原理与此类似。那么假设上天格外眷顾,让刘裕始终能后顾无忧,放手于北征,他能开创一个统一的王朝吗?
对于这个问题,北魏崔浩也作出了著名的回答:不能。他提出的理由有两条,一是刘裕不能“行荆扬之化于三秦之地”,无法巩固他占领的地区;二是由于兵种、地形、气候等方面的差异,晋军在华北作战将是以短击长,所以刘裕“不能发吴越之兵与官军(北魏军)争夺河北”。
这两条理由有道理吗?都有。但果然无懈可击吗?恐怕不见得。别的不说,就以崔浩服务的北魏帝国为例:当年拓跋珪称王于牛川时,它只是塞外一个落后的以游牧经济为主的国家,与中原在经济、文化和制度上的差异,较之江东与关中,恐怕只大不小,后来击败后燕,便成功入主发达富庶的河北之地,并且站稳了脚跟,这一成功,难道靠的是“行塞北之教化于燕赵之地”?
当然,对于复杂的历史事件不能简单类比,要研究拓跋珪做到的事刘裕能不能做到,我们不妨仔细审看一下现存的资料,利用一些疑点进行推测,看看刘裕本来打算怎么做?
刘裕对关中人事安排的一大疑点是:他明明不信任王镇恶,手下也并非没有其他将才,为何还将关中防务这样的重任交给此人?最常见的解释,是说王镇恶在灭秦之战中功劳最大,所以这次任命属于论功行赏。
但这种解释,显然会在另一个重要人物身上碰钉子,这便是那位论行政职务还在王镇恶之上的安西长史王修(按两汉至魏晋的习惯,长史为掾属之长,而且后来王镇恶被杀后,王修未经刘裕批准,就能任命毛修之接任安西司马之职,也可见一斑)。
令人吃惊的是:这个地位如此重要的王长史,却在《晋书》、《宋书》、《南史》等史籍中都没有传记,我只能确定,他并非出自瑯琊王氏和太原王氏这两大政治豪门,而且就在下所看到的史料而言,在他被任命为安西长史之前,这个人就没在史书中露过脸。这就奇怪了,这么一个要名气没名气,要功绩没功绩,要后台没后台的“三无”人员,怎么就能平地一声雷,跃居众多名将谋臣之上?
好在史书在他头次出场时提供了一点线索:“(刘裕)以太尉咨议参军京兆(人)王修为长史”, 京兆,就是晋朝时长安所在的郡名。现在看出来了吧,王修和王镇恶之所以让刘裕选中的共同点在哪儿?提示一下:并非都姓王。
北伐之谜 下
值得推敲的另一大疑点是:刘裕为何只给王镇恶、沈田子等人留下一万精兵?不管以哪个标准衡量,要守卫关中故土,一万人太少了。需知关中周边,强敌林立,即使不考虑东北面的北魏与西北面的西秦、北凉等潜在敌国,只要出长安北行不过二百里外,就有赫连勃勃的夏国军队。
参考夏国以前的战争经历,赫连勃勃能够动员的兵力肯定不少于五万,而且多是些机动性极强的凶悍铁骑,如果中途不受阻拦,跑快点的话,他们只用一天时间就可以冲到长安城下观光!难道刘裕对自己的儿子和百战而得的战果就如此漫不经心吗?
另外一条记载,从侧面解答了这个问题。
在王镇恶被杀前,关中晋军内部出现他要杀尽南人,自立为王的流言。尽管这肯定是一条谣言,但一条谣言要能流传开来,它应该具备最起码的潜在可能性,否则骗不了这么多身经百战的老兵。
这条谣言揭示了问题是,怎么杀?且不说王镇恶的武艺是出了名的差劲,就算他是东方不败或者独孤求败投胎,也很难相信他能自己动手,杀掉一万精兵。因此,在此时王镇恶手下的军队中,一定有不属于那一万北府老兵的新军存在,考虑到流言的内容和关中防务的需要,新军的数量上限无法确定,但下限应不少于一万人。
至此,综合这些零散的蛛丝马迹,也许我们已经逐渐走近历史的真相了:
一、就像二十多年前,已故的“总设计师”认识到不能以大陆之教化施于港澳,从而出现了今天的“港人治港”与“澳人治澳”一样,刘裕出台的政策,是以关中人治关中。因此,他才会提拔了功绩、名声都不显赫的关中人王修,而不用有世家背景的谢晦、王弘等人,或与自己相识已久,关系更亲密的南方旧人如张邵、孔靖等。换句话说,刘裕并不打算“行荆扬之化于三秦之地”;
二、刘裕要进一步北伐,完成一统,打下华北以至塞北,仅凭现有军队,难度是很大的。因此,刘裕实际上已在北方人中着手编组新军,负责人就是在北方民众中拥有巨大号召力的王猛的孙子——安西司马王镇恶。假如不发生后来的一系列变故,刘裕仍是有经营北方打算的,那时他用于征战北方的军队,将不仅仅是“吴越之兵”;
三、结合上两条,崔浩预测正确的是结果,而非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从不少迹象来看,崔浩作为一个汉人,可能仍存在对南方政权的认同,他的话不一定完全代表其真实看法)。假如不发生刘穆之逝世和关中变乱的事,那么阻止刘裕统一最大障碍,可能是时间。此时夏和北魏都非国势混乱的将亡之国,刘裕并不具备明朝初年那样速定北方的条件,只有采取稳扎稳打的方针,逐个消灭。但要达成这一目标,起码先得把关中由占领区变成领土和后方基地,同时组建一支有战斗力的新军,特别是骑兵部队,这些事都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而从刘裕离开关中之时,距离他寿终正寝之日,已经只有三年半了!总之,如果一切顺利,刘裕统一天下的可能性虽然存在,但非常微小,估计超不过一成;
四、在刘裕手下,既有北方人望,又有大将之才者,唯王镇恶一人。这使得刘裕只要还存有进取北方的念头,他对王镇恶就很难做到“疑人不用”。但在权术硬币的另一面,一个既有能力又有人望,而且不太听话的下属,又是让每个专制君主(刘裕早已是事实君主)夜不能寐的病根所在,再考虑到自身崛起的经历,要让刘裕对王镇恶做到“用人不疑”,也是不可能的!正是这一两难处境,将刘裕在关中的人事安排,逼上了一条危险的钢丝,并且最终因为一步失误,全盘皆输!
五、刘裕计划失败的关键,是王镇恶与王修的被杀。王镇恶被杀,使组建新军的努力告吹;王修被杀,使稳固关中的设想破产。而且这两人,原先都是关中汉人心目中的骄傲,也是刘裕赢得关中人心的关键。然而,仅仅在不到一年间,这两个人就相继被害了,而且还是被与刘裕一样的南方人杀害的,这一事实极大的打击了关中人对南方政权的认同感,而彼此的不信任又加剧了双方的矛盾,于是北方人大批叛逃,南方人大肆抢劫。晋军与关中百姓的关系,终于由王镇恶入潼关时的鱼水交融,演变成朱龄石出长安时的水火不容!其中的教训,实在值得后人深思。
至此,刘裕原先的一切宏伟设想,皆成泡影,他再无统一中国的可能。他还能做的大事,只剩下了一件……
革晋鼎 上
义熙十四年(公元418年)六月,刘裕接受他推让了快两年的“九锡”和宋公爵位,向从权臣到皇帝的大道上迈出实质性的一大步。
不久,不知是刘裕或是他的某个心腹,从哪里看到了一条“昌明(晋孝武帝)之后有二帝”的谶文,这引起刘裕高度重视:假如这条谶文很灵验,那刘裕要篡位就不能从现在在位的安帝司马德宗,这个昌明之后的第一帝身上下手,否则晋朝还会有“第二帝”来复辟,只能等下一位晋朝皇帝。但三十七岁的司马德宗虽然傻,身体除大脑以外的其他部份却还很健康,要等他自然死亡,那还不知是猴年马月的事,刘裕可已经年近花甲了。没办法,刘裕只好舍弃了司马德宗这枚性价比很高的橡皮图章,为晋朝再创造一位皇帝。
这年十二月十七日,刘裕派入宫中,随侍晋安帝左右的中书侍郎王韶之,乘平常照顾安帝起居的皇弟,琅琊王司马德文患病外出的机会,将晋安帝勒死于东堂。作为中国历史上,智商绝对是倒数第一的皇帝,白痴天子司马德宗的一生无疑是不幸的,口不能言,不辩寒暑,浑浑噩噩地出生,又浑浑噩噩地死去,从未享受过人生的乐趣。
不过反过来细细思量,身处晋末的混乱时代,他的愚鲁又未尝不是他的大幸:假如他智力正常,像他的弟弟司马德文,在那种时代也不可能中兴皇权,恐怕因为权臣们不放心,只会死得更早。而他,不管经历怎样的天翻地覆与兴衰荣辱,生命和地位如何岌岌可危,也从没感觉到天位的沉重和朝不保夕的恐惧。仅就个人心理体验到的幸福指数来说,他比弟弟幸福多了。
这个白痴纯度达24K的“幸福”傻子当然留不下儿子,刘裕随后宣称尊奉大行皇帝遗诏,拥他的弟弟琅琊王司马德文继皇帝位,改明年为元熙元年,大赦天下。司马德文后来被称作晋恭帝,逊顺事上曰恭,作为皇帝却要“逊顺事上”,他会有一个怎样的未来,光从这个谥号也可以看出来了。
司马德文一登基,就证明了他确实是“恭帝”。元熙元年(公元419年)正月三日,兄长司马德宗尸骨未寒,司马德文就下诏晋封宋公刘裕为宋王。刘裕扭扭捏捏地又推辞到七月份,才接受了宋王的封爵,将自己的驻地由彭城南迁至寿阳。
虽然刘裕改朝换的进程就像切香肠,每次只向前挪动一小步,但走到这里,距离皇位也实在找不出什么中间站了,只差抬脚迈最后一步了。
可话又说回来,不管怎么说,篡位如同臭豆腐,是一件吃起来虽然香,但闻起来让人不舒服的事。要迈出最后这一步,最好能由别人提出倡议,避免直接弄脏自己刚洗白的鞋子。
于是到第二年年初,宋王刘裕在自己驻地寿阳的宋国王府举行了一次宴会,宴请宋国主要官员。当酒宴渐入**,气氛非常融恰之际,刘裕突然发话,给他的这些部下们出了一道很难理解的智力题:“当年桓玄篡夺帝位,颠覆国家,是我首倡大义,起兵重兴晋室。而后,我南征北讨,平定四方,建立功业,于是得蒙皇上下赐九锡,可谓荣光无限。但我如今年已老迈,地位又太过崇高,世间万事,都忌讳过于满盈,否则不能长久。我现在只想将王爵奉还皇上,回京城养老,以安晚年。”这段莫名其妙的话,让在坐的多数官员也听得莫名其妙,只是本着油多不坏菜的原则,一个劲地给刘裕歌功颂德。
说实在的,在下作为一个读史的后人,虽然很清楚刘裕此时想要干什么,但还是看不出他这段话,与他想暗示的意思之间,究竟有何联系?
好在刘裕的手下可不都是在下这样的笨蛋,从来不乏聪明人,比如晋朝名臣傅咸的孙子傅亮。当天色渐暗,酒终人散之际,这位担任宋国中书令的傅大人走出王府归家,行至半途,傅亮突然心念一动,猛然间领会了宋王想要表答的意思。于是他马上掉头,又赶回宋王府。
不一会儿,傅亮见到了宋王刘裕,两个人继续打哑谜。
傅亮说:“我得回一趟京城。”
刘裕问:“要多少人护送?”
傅亮答:“数十人就够了。”
言罢,告辞。在不明就